This blog will be suspended until next year due to some technical problems. In particular, the computer at home is out of order. Actually this is the only major reason. Ur yea, there is a minor one. I am now on my hometown soil and this is Christmas time. Blogging may not be an appropriate way to enjoy the hol. (Coz it's not a foreign land. OR it is a foreign land.)
Anyway,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folks.
Friday, December 22, 2006
THE TIMES,英國一份歷史悠久的報紙。林行止認為﹐這份報紙的中文譯名應該是《倫敦時報》。不過﹐很多香港人﹐包括陶傑在內﹐都喜歡叫它做《泰晤士報》。那是音譯與義譯的分別。只是﹐由於「泰晤士」三個字早做了那條貫穿倫敦的河流的中文名字﹐為免混淆THAMES和TIMES﹐我以為﹐林行止先生的說法比較可取。
一份報紙成功與否﹐最重要的還要看它有什麼讀者。也許﹐你會以為那是雞與雞蛋的問題。但我始終認為﹐有什麼樣的讀者﹐方有什麼樣的報紙。因為為了迎合市場﹐報紙裡面的文筆﹐都會跟著讀者走。
要知道一份報紙的讀者是什麼人﹐當然要翻閱讀者來函。《倫敦時報》的LETTERS TO THE EDITOR出名高水準。都是簡短而雋永。每年年終﹐最好的數百篇都會給輯錄成書。以前﹐還在香港的時候﹐也買過兩本。的確是學寫「啖啖肉」英文的最佳讀物。
早前﹐有一篇講溫室效應。讀者寫道﹕
Sir, We must take global warming seriously. It is December 9 and I have just been bitten by a mosquito. It was not alone.
寥寥二十字﹐便把一切說得很明白。陶傑說﹐寫文章要多一個字嫌太多﹐少一個字則嫌太少。不能有多餘的脂肪﹐要「啖啖肉」。
看見MOSQUITO這個字﹐想起了個多星期前﹐跟老朋友通過的一趟電話。那天﹐我們談到THE MOSQUITOES - 我們的樂隊。
實在不記得是誰起的名字。當然﹐也記不起名字的來由。或者﹐是從THE BEATLES來的靈感罷﹖始終﹐我們是一隊以甲蟲樂隊為藍本的組合。我們臺上的表演﹐都是以披頭四的作品為主。
亦想不起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只記得﹐一切都從那年的SINGING CONTEST開始。我們選了WHEN I'M SIXTY-FOUR參賽。
跟很多出色樂隊一樣﹐我們的起頭也很不順利。除了一眾友好支持外﹐並沒有得到其他人的賞識。每年的音樂比賽﹐就只能入到複賽﹐都跟決賽無緣。直到中學的第七年。
那一年﹐我們如常揀了披頭四的歌。是ALL MY LOVING。
我們知道﹐那是最後一年。於是﹐每當空堂的時候﹐我們都會聚在一起練習。也有錄音﹐希望找到裡面的毛病。經過多翻改善後﹐我竟然覺得我們唱得跟THE BEATLES有丁點相似。(我不敢說有太多﹐因為那是對這一個音樂傳奇太過不敬。)當然﹐也不只是我們自己覺得出色。因為我們以首名的成積打入決賽。
環顧所有對手﹐我們相信﹐只要唱回複賽時的水準﹐冠軍是十拿九穩。不過﹐既然是最後一年參加SINGING CONTEST,我們希望多享受些臺上的時間。於是﹐我們竟然選了五﹑六首我們都甚喜歡的披頭四作品﹐串了起來做一個MEDLEY。只是﹐因為時間緊迫﹐加上考試日子漸近﹐練習得實在不多﹐我們再一次使支持者失望而回。不過﹐老實說﹐我倒很享受在臺上擺動MIC-STAND。
可是﹐自預科畢業前的那次公開演出後﹐大家便各有各忙﹐再沒有走在一起夾歌的時間。有得也只是卡拉OK。更想不到的是﹐到了現在﹐竟然難上加難。因為我們都各散東西﹐各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一個在中美洲﹐一個在歐洲﹐兩個在亞洲。幾時還有再會的時間﹖
朋友﹐你們還記掛著蚊子樂隊嗎﹖
原來﹐要給蚊叮﹐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註﹕技術問題﹐TOFFEELAND將暫停刊登一天。
一份報紙成功與否﹐最重要的還要看它有什麼讀者。也許﹐你會以為那是雞與雞蛋的問題。但我始終認為﹐有什麼樣的讀者﹐方有什麼樣的報紙。因為為了迎合市場﹐報紙裡面的文筆﹐都會跟著讀者走。
要知道一份報紙的讀者是什麼人﹐當然要翻閱讀者來函。《倫敦時報》的LETTERS TO THE EDITOR出名高水準。都是簡短而雋永。每年年終﹐最好的數百篇都會給輯錄成書。以前﹐還在香港的時候﹐也買過兩本。的確是學寫「啖啖肉」英文的最佳讀物。
早前﹐有一篇講溫室效應。讀者寫道﹕
Sir, We must take global warming seriously. It is December 9 and I have just been bitten by a mosquito. It was not alone.
寥寥二十字﹐便把一切說得很明白。陶傑說﹐寫文章要多一個字嫌太多﹐少一個字則嫌太少。不能有多餘的脂肪﹐要「啖啖肉」。
看見MOSQUITO這個字﹐想起了個多星期前﹐跟老朋友通過的一趟電話。那天﹐我們談到THE MOSQUITOES - 我們的樂隊。
實在不記得是誰起的名字。當然﹐也記不起名字的來由。或者﹐是從THE BEATLES來的靈感罷﹖始終﹐我們是一隊以甲蟲樂隊為藍本的組合。我們臺上的表演﹐都是以披頭四的作品為主。
亦想不起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只記得﹐一切都從那年的SINGING CONTEST開始。我們選了WHEN I'M SIXTY-FOUR參賽。
跟很多出色樂隊一樣﹐我們的起頭也很不順利。除了一眾友好支持外﹐並沒有得到其他人的賞識。每年的音樂比賽﹐就只能入到複賽﹐都跟決賽無緣。直到中學的第七年。
那一年﹐我們如常揀了披頭四的歌。是ALL MY LOVING。
我們知道﹐那是最後一年。於是﹐每當空堂的時候﹐我們都會聚在一起練習。也有錄音﹐希望找到裡面的毛病。經過多翻改善後﹐我竟然覺得我們唱得跟THE BEATLES有丁點相似。(我不敢說有太多﹐因為那是對這一個音樂傳奇太過不敬。)當然﹐也不只是我們自己覺得出色。因為我們以首名的成積打入決賽。
環顧所有對手﹐我們相信﹐只要唱回複賽時的水準﹐冠軍是十拿九穩。不過﹐既然是最後一年參加SINGING CONTEST,我們希望多享受些臺上的時間。於是﹐我們竟然選了五﹑六首我們都甚喜歡的披頭四作品﹐串了起來做一個MEDLEY。只是﹐因為時間緊迫﹐加上考試日子漸近﹐練習得實在不多﹐我們再一次使支持者失望而回。不過﹐老實說﹐我倒很享受在臺上擺動MIC-STAND。
可是﹐自預科畢業前的那次公開演出後﹐大家便各有各忙﹐再沒有走在一起夾歌的時間。有得也只是卡拉OK。更想不到的是﹐到了現在﹐竟然難上加難。因為我們都各散東西﹐各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一個在中美洲﹐一個在歐洲﹐兩個在亞洲。幾時還有再會的時間﹖
朋友﹐你們還記掛著蚊子樂隊嗎﹖
原來﹐要給蚊叮﹐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註﹕技術問題﹐TOFFEELAND將暫停刊登一天。
Thursday, December 21, 2006
說來慚愧﹐自中學開始﹐便學習過不下五種文字﹐只是沒有太大閱讀困難的﹐便只有中文和英文。於是﹐對於其他世界的作品﹐我都只能讀翻譯本。
只是﹐在紅色中文的污染下﹐我們的世界﹐已經再沒有梁實秋和余光中﹐已經再沒有人能夠好好用中文翻譯。
其實﹐當身邊週圍都是西化中文的時候﹐又怎可能還有人可以把其他地方的作品﹐用真正的中文寫一遍。從來﹐我都以為﹐翻譯也是一種創作。那是一種別人文化與自己文化的結集。中文翻譯,便是用中國人的話去講外國人的故事。無奈﹐現在做中文翻譯的人﹐都只會把THE RED FAT CAT說成「那隻紅色肥貓」。
所以﹐要讀屠格涅夫﹑要讀杜斯妥耶夫斯基﹑要讀佐拉﹐我唯有讀英文。
不過﹐在英語的世界﹐對於那些世界名著﹐又實在有太多翻譯本。面對著這麼多選擇﹐我始終只相信企鵝。我想﹐這又是中了陶傑的毒。
企鵝出版社創建於1935年。
有天﹐創辦人ALLEN LANE到DEVON探望完偵探小說女王AGATHA CHRISTIE後﹐正準備返回倫敦。他希望在火車上讀點新潮的書。可是﹐在EXETER火車站的書店找來找去﹐都尋不到一本合意。因為不是雜誌﹐便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品。有見及此﹐突然靈機一觸﹐ALLEN LANE決定以廉宜的價錢向群眾提供高水準的新潮讀物。從此﹐便成為了英國讀物普及的一大功臣。每年﹐出版社都買出三百萬本書。
最早面世的企鵝版書籍﹐封面設計極為簡單﹕綠色的是偵探小說﹐藍色的是名人傳記﹐橙色的是小說。樸實無華﹐便於攜帶。都售六便士。於是﹐有SIXPENNY NOVEL之稱。後來企鵝的出版便以封面取勝﹐出版的世界名著﹐所配的封面名畫都恰到好處。陶傑說﹐那些封面名畫﹐會令人覺得書香更濃﹐藏之如藏藝術品。
假如你很看重一本書的封面設計﹐那麼﹐我想﹐今年聖誕節你最希望得到的禮物或許是最新的一套PENGUIN CLASSICS。
最近﹐企鵝出版社邀請的幾位名設計師﹐為五本PENGUIN CLASSICS重新設計封面。
SIR PAUL SMITH選了《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因為他很喜歡D.H.LAWRENCE。況且﹐他跟勞倫斯都是出生在諾定咸。建築師RON ARAD選了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FUEL也選了杜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罪與罰》。攝影師SAM TAYLOR-WOOD則替F.SCOTT FITZGERALD的《夜溫柔》設計。(竟然不是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包華利夫人》也有一個新的封面。
望著這些STYLISH ICONS,我實在沒有多大興趣。當然﹐可能是售價的關係。出版社把它們定價為一百英鎊。不過﹐更大的原因﹐倒是因為我還是喜歡傳統﹐喜歡懷舊。叫得做CLASSICS,當然要有點殘破。最理想﹐就是在扉頁上有從前主人的墨水簽名﹐字裡行間又有他細讀時鉛筆的眉批。這些都如雪泥鴻爪﹐都是一片心跡。況且﹐我總覺得﹐名貴裝璜的書籍﹐都是金玉其外﹐縱然這些都是經典中的經典。
只是﹐在紅色中文的污染下﹐我們的世界﹐已經再沒有梁實秋和余光中﹐已經再沒有人能夠好好用中文翻譯。
其實﹐當身邊週圍都是西化中文的時候﹐又怎可能還有人可以把其他地方的作品﹐用真正的中文寫一遍。從來﹐我都以為﹐翻譯也是一種創作。那是一種別人文化與自己文化的結集。中文翻譯,便是用中國人的話去講外國人的故事。無奈﹐現在做中文翻譯的人﹐都只會把THE RED FAT CAT說成「那隻紅色肥貓」。
所以﹐要讀屠格涅夫﹑要讀杜斯妥耶夫斯基﹑要讀佐拉﹐我唯有讀英文。
不過﹐在英語的世界﹐對於那些世界名著﹐又實在有太多翻譯本。面對著這麼多選擇﹐我始終只相信企鵝。我想﹐這又是中了陶傑的毒。
企鵝出版社創建於1935年。
有天﹐創辦人ALLEN LANE到DEVON探望完偵探小說女王AGATHA CHRISTIE後﹐正準備返回倫敦。他希望在火車上讀點新潮的書。可是﹐在EXETER火車站的書店找來找去﹐都尋不到一本合意。因為不是雜誌﹐便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品。有見及此﹐突然靈機一觸﹐ALLEN LANE決定以廉宜的價錢向群眾提供高水準的新潮讀物。從此﹐便成為了英國讀物普及的一大功臣。每年﹐出版社都買出三百萬本書。
最早面世的企鵝版書籍﹐封面設計極為簡單﹕綠色的是偵探小說﹐藍色的是名人傳記﹐橙色的是小說。樸實無華﹐便於攜帶。都售六便士。於是﹐有SIXPENNY NOVEL之稱。後來企鵝的出版便以封面取勝﹐出版的世界名著﹐所配的封面名畫都恰到好處。陶傑說﹐那些封面名畫﹐會令人覺得書香更濃﹐藏之如藏藝術品。
假如你很看重一本書的封面設計﹐那麼﹐我想﹐今年聖誕節你最希望得到的禮物或許是最新的一套PENGUIN CLASSICS。
最近﹐企鵝出版社邀請的幾位名設計師﹐為五本PENGUIN CLASSICS重新設計封面。
SIR PAUL SMITH選了《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因為他很喜歡D.H.LAWRENCE。況且﹐他跟勞倫斯都是出生在諾定咸。建築師RON ARAD選了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FUEL也選了杜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罪與罰》。攝影師SAM TAYLOR-WOOD則替F.SCOTT FITZGERALD的《夜溫柔》設計。(竟然不是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包華利夫人》也有一個新的封面。
望著這些STYLISH ICONS,我實在沒有多大興趣。當然﹐可能是售價的關係。出版社把它們定價為一百英鎊。不過﹐更大的原因﹐倒是因為我還是喜歡傳統﹐喜歡懷舊。叫得做CLASSICS,當然要有點殘破。最理想﹐就是在扉頁上有從前主人的墨水簽名﹐字裡行間又有他細讀時鉛筆的眉批。這些都如雪泥鴻爪﹐都是一片心跡。況且﹐我總覺得﹐名貴裝璜的書籍﹐都是金玉其外﹐縱然這些都是經典中的經典。
Wednesday, December 20, 2006
中學時候﹐十二月的確是一個極忙碌的月份。因為學校有太多活動舉行。為的就是那聖誕節。
老實說﹐從數量來看﹐著實不算多。才祇得兩個。一個是舞蹈比賽﹐另一個則是班房佈置比賽。不過﹐都很大型。都是班際的活動。
顧名思義﹐班房佈置比賽﹐就是學生替自己的課室佈置﹐然後由一眾老師評分。舞蹈比賽﹐則是每班派出八男八女﹐按著指定音樂﹐集體跳一隻舞來。從排舞到練習到表演﹐都是學生自己一手安排。由於都要動員大量人力﹐故此﹐十二月一開始﹐每天放學後﹐學校每一角落﹐都依然人頭湧湧﹐直至夜深。便是星期六﹐同樣擠滿了人。大家都把握著每分每秒﹐去為自己的班爭光。我記得﹐那是一年裡面﹐最興奮的時候。
印象中﹐我應該沒有怎樣幫手佈置課室。因為每年我都是那八個男生的其中一個。
大學的日子﹐根本就沒有固定的上課地點﹐所以談不上什麼課室佈置。出來社會做事後﹐聖誕的時候﹐大家也不會特別為自己的檯面佈置一下或者﹐是不想讓老闆知道﹐自己竟然還有那麼多的精力和時間。公司裡面﹐其實都會有些裝飾﹐不過﹐都是公家的罷了。
今年﹐來到了愛爾蘭生活。情形似乎有點不同。
也有公家的聖誕擺設。每層樓的大門口﹐都擺放了一棵六尺高的聖誕樹。只是﹐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為了增加節日氣氛﹐同事都很努力去裝飾自己的座位。當然﹐也是為了那個聖誕座位佈置比賽罷。那是SOCIAL CLUB聖誕的其中一個活動。每層樓有一個冠軍。然後還有一個都柏林的總冠軍。
十二月初的一天﹐下班回家﹐碰見了那位從立陶宛來的同事。他問我﹐是否打算佈置一下﹖我說﹐也不用這麼快開始罷。況且﹐我們二樓還未有人開始佈置。我倒不想做第一個。不過﹐從他口中得知﹐原來﹐三樓的同事已經開始下班後﹐留在公司裝飾自己的座位。
上星期﹐我們二樓才開始有人佈置。都圍了些燈飾﹑彩帶。也有雪人和聖誕樹。我最喜歡的﹐倒是JEAN的那三隻蝙蝠。他們都笑這位ASSOCIATE把家裡兩個月前的HOLLOWEEN擺設搬回公司。不過﹐我以為倒有NIGHTMARE BEFORE CHRISTMAS的影子。
有天中飯的時候﹐曾經跟EILEEN和NICHOLA討論過﹐如何佈置我們那一倉。NICHOLA笑說﹐我們可以弄一個馬槽出來。大家都知道﹐這是個笑話罷。最後﹐我們還是決定各自各精彩。對我來說﹐那表示什麼都不用做。知道我這個決定後﹐FIONNUALA曾經用很鄙視的眼光望著我。她說﹐總要有一些裝飾罷。IT IS CHRISTMAS TIME。
其實﹐我也想過把今年收到的聖誕卡﹐釘到座位的壁報板上﹐來做做裝飾佈置。只是﹐才得兩張﹐唯有擱置。
今天﹐TEA TIME之後﹐流傳了一個消息。都說三樓的佈置很厲害。於是﹐大家都爭相參觀。我怕LOST IN DESCRIPTION,還是不好描述出來。不過﹐看過那個佈置後﹐我和EILEEN和NICHOLA都面面相覷︰那可不是曾經在我們腦海裡出現過的畫面﹖
ENDA說﹐為了完成那個佈置﹐他們可在公司留到晚上十一點。
在香港和在愛爾蘭工作有什麼分別﹖這可又是一個例子罷。
老實說﹐從數量來看﹐著實不算多。才祇得兩個。一個是舞蹈比賽﹐另一個則是班房佈置比賽。不過﹐都很大型。都是班際的活動。
顧名思義﹐班房佈置比賽﹐就是學生替自己的課室佈置﹐然後由一眾老師評分。舞蹈比賽﹐則是每班派出八男八女﹐按著指定音樂﹐集體跳一隻舞來。從排舞到練習到表演﹐都是學生自己一手安排。由於都要動員大量人力﹐故此﹐十二月一開始﹐每天放學後﹐學校每一角落﹐都依然人頭湧湧﹐直至夜深。便是星期六﹐同樣擠滿了人。大家都把握著每分每秒﹐去為自己的班爭光。我記得﹐那是一年裡面﹐最興奮的時候。
印象中﹐我應該沒有怎樣幫手佈置課室。因為每年我都是那八個男生的其中一個。
大學的日子﹐根本就沒有固定的上課地點﹐所以談不上什麼課室佈置。出來社會做事後﹐聖誕的時候﹐大家也不會特別為自己的檯面佈置一下或者﹐是不想讓老闆知道﹐自己竟然還有那麼多的精力和時間。公司裡面﹐其實都會有些裝飾﹐不過﹐都是公家的罷了。
今年﹐來到了愛爾蘭生活。情形似乎有點不同。
也有公家的聖誕擺設。每層樓的大門口﹐都擺放了一棵六尺高的聖誕樹。只是﹐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為了增加節日氣氛﹐同事都很努力去裝飾自己的座位。當然﹐也是為了那個聖誕座位佈置比賽罷。那是SOCIAL CLUB聖誕的其中一個活動。每層樓有一個冠軍。然後還有一個都柏林的總冠軍。
十二月初的一天﹐下班回家﹐碰見了那位從立陶宛來的同事。他問我﹐是否打算佈置一下﹖我說﹐也不用這麼快開始罷。況且﹐我們二樓還未有人開始佈置。我倒不想做第一個。不過﹐從他口中得知﹐原來﹐三樓的同事已經開始下班後﹐留在公司裝飾自己的座位。
上星期﹐我們二樓才開始有人佈置。都圍了些燈飾﹑彩帶。也有雪人和聖誕樹。我最喜歡的﹐倒是JEAN的那三隻蝙蝠。他們都笑這位ASSOCIATE把家裡兩個月前的HOLLOWEEN擺設搬回公司。不過﹐我以為倒有NIGHTMARE BEFORE CHRISTMAS的影子。
有天中飯的時候﹐曾經跟EILEEN和NICHOLA討論過﹐如何佈置我們那一倉。NICHOLA笑說﹐我們可以弄一個馬槽出來。大家都知道﹐這是個笑話罷。最後﹐我們還是決定各自各精彩。對我來說﹐那表示什麼都不用做。知道我這個決定後﹐FIONNUALA曾經用很鄙視的眼光望著我。她說﹐總要有一些裝飾罷。IT IS CHRISTMAS TIME。
其實﹐我也想過把今年收到的聖誕卡﹐釘到座位的壁報板上﹐來做做裝飾佈置。只是﹐才得兩張﹐唯有擱置。
今天﹐TEA TIME之後﹐流傳了一個消息。都說三樓的佈置很厲害。於是﹐大家都爭相參觀。我怕LOST IN DESCRIPTION,還是不好描述出來。不過﹐看過那個佈置後﹐我和EILEEN和NICHOLA都面面相覷︰那可不是曾經在我們腦海裡出現過的畫面﹖
ENDA說﹐為了完成那個佈置﹐他們可在公司留到晚上十一點。
在香港和在愛爾蘭工作有什麼分別﹖這可又是一個例子罷。
Tuesday, December 19, 2006
早前﹐寫了一篇BLOG,講一群香港工程師參選特首推選委員會的競選網頁。(單從文字看﹐便可想像這個制度如何荒謬﹑無里頭。要那麼纍贅﹐方能講出選舉特首的一個小小階段。話也得說回來﹐實在要很小心的讀這篇文章。因為太多「選舉」﹑「推選」﹑「選民」﹑「候選人」等這些字眼。更甚的是﹐在複雜怪誕的制度下﹐這些名詞卻又巧妙地互相代替。今天﹐我參加選舉﹐所以是候選人。你是選民﹐希望你投我一票﹐好讓我明天當選後﹐有了權力﹐來推選你做特首候選人。)
那群工程師稱自己做E4US。全名是ENGINEERS FOR UNIVERSAL SUFFRAGE。也有一個中文名字﹐叫普選工程路線。
朋友是工程界的選民。讀了那篇文章後﹐給我寫了這一段文字﹕
今次特首推選委員會選舉﹐工程界有42個選候人﹐毎個選民有20票。忽然間好像有很多選擇。但其實﹐連有什麼特首候選人都不知道的情形下﹐真不知道怎去選推選委員。那42人的政綱(叫政綱好像不正確)﹐有提及普選的﹐似乎只有這8人。其他人的政綱﹐比這8人「搞笑」十倍也有。什麼「下屆特首﹐有頭有腦﹐有手有腳」。是不是會有個特首候選人沒有手和沒有腳﹖[假如]只要「有頭有腦﹐有手有腳」[便成],他對特首也太沒要求。其餘的政綱﹐也大多不很合題。大概﹐工程師都不太會搞政治和大多「一身叫雞氣」(但不包括女工程師) 。雖然我不太相信若這8人入選後真的能夠「重新燃點希望」(這些希望不只是給工程師的)﹐但也希望能帶出一些普選的聲音。就算明知曾蔭權會連任,你也不會想他高票當選吧﹗
......
其實,我認為你對這8人的批評太刻薄了點。
首先﹐朋友似乎也給那個荒謬制度弄得頭昏腦漲。既然名為特首推選委員會﹐在這些委員當選前﹐當然沒有什麼特首候選人。邏輯上﹐倒是說得通。不過﹐我以為﹐每個參選特首推選委員會的人﹐都應該跟自己的選民講清楚自己當選後﹐會推選那一位做特首候選人。只是﹐除了梁家傑宣佈希望成為特首外﹐再沒有其他人正式表示想做新一屆香港頭頭﹐在什麼都是未知數時候﹐便高呼某一個人的名字﹐政治風險實在太大。始終﹐香港經已回歸。一切都回到中國宮庭式鬥爭裡面。
假如真有推選委員會候選人﹐只希望特首候選人是一個有頭又有腦﹐有手又有腳的人﹐我同意﹐我對E4US的批評是過份嚴苛。甚至乎無理。
不過﹐我不以為那是因為我的標準定得太高。我想﹐那只是一個很普通的標準。難道一個選民應該容許候選人的政綱粗製濫造﹖難道一個候選人言行﹐以至容貌等一切﹐都不用給選民信心﹖
我依然以為﹐對於E4US的評語是正確。
至於﹐過份嚴苛﹐那是因為我沒有同時間批評其餘34個更低能的候選人。在這樣不公平的情形下﹐這些批評當然是無理。只是﹐假如我對這群較為正常的工程師也如此看待﹐我應該可以合理地期望﹐一個普通人能夠猜到我對其他候選人的評價。(也許﹐這個假設更不合乎情理。)
朋友以為﹐那是工程師都不太會搞政治的關係。我不以為然。政治本就是人的事﹐假如你說你不懂得政治﹐你便是不懂得如何做一個人。(當然﹐政治背後帶出來的黑暗﹐又是另一個話題。)連工程師這些專業人士也未能好好做一個人﹐未能跟大眾好好講出自己對特首的要求﹐香港的教育真的很有問題。或者﹐在這樣的教育程度下﹐香港真的不適宜普選。
評價歸評價﹐批評還批評。要知道﹐要做這些委員會的委員﹐根本不需要什麼政綱。假若你還以為需要政綱﹐那只表示你未得到欽點。再不好那樣天真無邪地﹐相信PEKING政府搞出來的選舉假象。我始終以為﹐BEFORE YOU JOIN THEM,TRY TO BEAT THEM。
那群工程師稱自己做E4US。全名是ENGINEERS FOR UNIVERSAL SUFFRAGE。也有一個中文名字﹐叫普選工程路線。
朋友是工程界的選民。讀了那篇文章後﹐給我寫了這一段文字﹕
今次特首推選委員會選舉﹐工程界有42個選候人﹐毎個選民有20票。忽然間好像有很多選擇。但其實﹐連有什麼特首候選人都不知道的情形下﹐真不知道怎去選推選委員。那42人的政綱(叫政綱好像不正確)﹐有提及普選的﹐似乎只有這8人。其他人的政綱﹐比這8人「搞笑」十倍也有。什麼「下屆特首﹐有頭有腦﹐有手有腳」。是不是會有個特首候選人沒有手和沒有腳﹖[假如]只要「有頭有腦﹐有手有腳」[便成],他對特首也太沒要求。其餘的政綱﹐也大多不很合題。大概﹐工程師都不太會搞政治和大多「一身叫雞氣」(但不包括女工程師) 。雖然我不太相信若這8人入選後真的能夠「重新燃點希望」(這些希望不只是給工程師的)﹐但也希望能帶出一些普選的聲音。就算明知曾蔭權會連任,你也不會想他高票當選吧﹗
......
其實,我認為你對這8人的批評太刻薄了點。
首先﹐朋友似乎也給那個荒謬制度弄得頭昏腦漲。既然名為特首推選委員會﹐在這些委員當選前﹐當然沒有什麼特首候選人。邏輯上﹐倒是說得通。不過﹐我以為﹐每個參選特首推選委員會的人﹐都應該跟自己的選民講清楚自己當選後﹐會推選那一位做特首候選人。只是﹐除了梁家傑宣佈希望成為特首外﹐再沒有其他人正式表示想做新一屆香港頭頭﹐在什麼都是未知數時候﹐便高呼某一個人的名字﹐政治風險實在太大。始終﹐香港經已回歸。一切都回到中國宮庭式鬥爭裡面。
假如真有推選委員會候選人﹐只希望特首候選人是一個有頭又有腦﹐有手又有腳的人﹐我同意﹐我對E4US的批評是過份嚴苛。甚至乎無理。
不過﹐我不以為那是因為我的標準定得太高。我想﹐那只是一個很普通的標準。難道一個選民應該容許候選人的政綱粗製濫造﹖難道一個候選人言行﹐以至容貌等一切﹐都不用給選民信心﹖
我依然以為﹐對於E4US的評語是正確。
至於﹐過份嚴苛﹐那是因為我沒有同時間批評其餘34個更低能的候選人。在這樣不公平的情形下﹐這些批評當然是無理。只是﹐假如我對這群較為正常的工程師也如此看待﹐我應該可以合理地期望﹐一個普通人能夠猜到我對其他候選人的評價。(也許﹐這個假設更不合乎情理。)
朋友以為﹐那是工程師都不太會搞政治的關係。我不以為然。政治本就是人的事﹐假如你說你不懂得政治﹐你便是不懂得如何做一個人。(當然﹐政治背後帶出來的黑暗﹐又是另一個話題。)連工程師這些專業人士也未能好好做一個人﹐未能跟大眾好好講出自己對特首的要求﹐香港的教育真的很有問題。或者﹐在這樣的教育程度下﹐香港真的不適宜普選。
評價歸評價﹐批評還批評。要知道﹐要做這些委員會的委員﹐根本不需要什麼政綱。假若你還以為需要政綱﹐那只表示你未得到欽點。再不好那樣天真無邪地﹐相信PEKING政府搞出來的選舉假象。我始終以為﹐BEFORE YOU JOIN THEM,TRY TO BEAT THEM。
Monday, December 18, 2006
上星期五。公司聖誕派對翌日。
當大家都回到公司後﹐JOHN發了個電郵﹐提議到WEIRS吃中飯。那是一間酒館餐廳。我們以為﹐那是DÚN LAOGHAIRE裡面最好的一間。才十塊歐羅﹐便吃得飽飽﹐而且還很美味。不過﹐因為外面下著大雨﹐便是FIONNUALA都一反常態﹐建議點DOMINO薄餅外賣。眾所週知﹐她最喜歡去WEIRS。於是﹐在那惡劣天氣下﹐到餐廳吃中飯的﹐就祇得JOHN、FIONN、EMILY和我。從「英皇娛樂」開始﹐我便不喜歡留在公司開餐。
用膳的時候﹐當然少不了談談那個聖誕派對。
我問他們有否KATE的消息。我沒有她的電話﹐不知道她能否準時到達機場。她可是要乘十一點那一班機回紐約的家鄉。只是﹐大家都找不到她。
星期四的夜晚﹐她很早便飲得很醉。是十一點的時候罷。我看到她幾次從座位摔到在地。有一次﹐她跳舞回來﹐站著休息﹐我剛巧坐在旁邊。才聊不到半句﹐她突然站立不穩﹐整個人坐在地上。我攙扶不及﹐還差點兒把頭顱栽在她那巨大的乳房裡面。我扶起她﹐她笑著叫我不用擔心。她說﹐我不會再錯過飛機。我知道﹐去年﹐她也是回家渡聖誕。只是前一晚﹐因為飲得太多﹐睡過了頭。起身的時候﹐飛機已經開走。幸好﹐那一天﹐另外一班機還有空位。始終﹐用金錢解決得到的問題﹐都不會是個問題。我常笑KATE道﹐假若一年後﹐還犯著同樣的錯﹐那實在很笨蛋。那時候﹐我望著她的臉﹐發覺她的確越來越像一個笨蛋。
接下來的夜晚﹐很多時候﹐大家都忙著照料她。或幫她找手袋﹐或幫她找回那一雙高跟鞋。EILEEN還要為她敷藥上膝蓋的傷口。
我想起了幾天前﹐倫敦時報副刊裡面的一篇文章。題面是THE OFFICE PARTY:ALL NIGHT WRONG。那是提醒我們參加公司派對要注意的地方。誠然﹐NOTHING IN THE YEAR HAS MORE POTENTIAL FOR DISASTER THAN THE OFFICE SHINDIG。裡面劈頭第一戒條便是︰SETTING YOURSELF AN ALCOHOL LIMIT AND STICK TO IT。因為在酒精影響下﹐其他戒條也不能守下去。
在派對裡面﹐當然再次遇上公司地下OFFICE的那一班美少女。都是在夏天公司到CO CARLOW旅行的時候認識。因為也有一段時間沒有碰面﹐我竟然記不起了她們的名字。以前﹐我是不會忘掉每一個女生的姓和名。都怪她們古怪的愛爾蘭名字。只靠讀音﹐當然記不牢。不過﹐自己的記憶力開始退步﹐也是不容不承認的事。
我是記得第二戒條﹕YOU HAVE TO ASK,WHAT IS DANCING AT THE OFFICE PARTY FOR? WATCH OUT YOU DON'T GET CARRIED AWAY AND END UP DOING SOME INAPPROPRIATE SNOGGING OR WORSE。雖然如此﹐我還是跟一個美少女跳了幾隻舞。她很有禮貌地﹐輕輕在我耳邊說﹐你也跳得很好。我笑著回答﹐那是功多藝熟。況且﹐夏天旅行到現在﹐也已過了六個月。好歹也要有些進步罷﹖要不便浪費了這半年在愛爾蘭的日子。我看著她﹐她笑得很甜。不過﹐她還是「留起了最後一隻舞」。因為﹐她便是JOHN最近認識的女朋友。
在酒吧旁休息的時候﹐望著BARRY不斷跟這些悉心裝扮過的女生拍照﹐我有點後悔沒有帶同我的照相機同來。
我想起了LIONEL RICHIE的ALL NIGHT LONG。
當大家都回到公司後﹐JOHN發了個電郵﹐提議到WEIRS吃中飯。那是一間酒館餐廳。我們以為﹐那是DÚN LAOGHAIRE裡面最好的一間。才十塊歐羅﹐便吃得飽飽﹐而且還很美味。不過﹐因為外面下著大雨﹐便是FIONNUALA都一反常態﹐建議點DOMINO薄餅外賣。眾所週知﹐她最喜歡去WEIRS。於是﹐在那惡劣天氣下﹐到餐廳吃中飯的﹐就祇得JOHN、FIONN、EMILY和我。從「英皇娛樂」開始﹐我便不喜歡留在公司開餐。
用膳的時候﹐當然少不了談談那個聖誕派對。
我問他們有否KATE的消息。我沒有她的電話﹐不知道她能否準時到達機場。她可是要乘十一點那一班機回紐約的家鄉。只是﹐大家都找不到她。
星期四的夜晚﹐她很早便飲得很醉。是十一點的時候罷。我看到她幾次從座位摔到在地。有一次﹐她跳舞回來﹐站著休息﹐我剛巧坐在旁邊。才聊不到半句﹐她突然站立不穩﹐整個人坐在地上。我攙扶不及﹐還差點兒把頭顱栽在她那巨大的乳房裡面。我扶起她﹐她笑著叫我不用擔心。她說﹐我不會再錯過飛機。我知道﹐去年﹐她也是回家渡聖誕。只是前一晚﹐因為飲得太多﹐睡過了頭。起身的時候﹐飛機已經開走。幸好﹐那一天﹐另外一班機還有空位。始終﹐用金錢解決得到的問題﹐都不會是個問題。我常笑KATE道﹐假若一年後﹐還犯著同樣的錯﹐那實在很笨蛋。那時候﹐我望著她的臉﹐發覺她的確越來越像一個笨蛋。
接下來的夜晚﹐很多時候﹐大家都忙著照料她。或幫她找手袋﹐或幫她找回那一雙高跟鞋。EILEEN還要為她敷藥上膝蓋的傷口。
我想起了幾天前﹐倫敦時報副刊裡面的一篇文章。題面是THE OFFICE PARTY:ALL NIGHT WRONG。那是提醒我們參加公司派對要注意的地方。誠然﹐NOTHING IN THE YEAR HAS MORE POTENTIAL FOR DISASTER THAN THE OFFICE SHINDIG。裡面劈頭第一戒條便是︰SETTING YOURSELF AN ALCOHOL LIMIT AND STICK TO IT。因為在酒精影響下﹐其他戒條也不能守下去。
在派對裡面﹐當然再次遇上公司地下OFFICE的那一班美少女。都是在夏天公司到CO CARLOW旅行的時候認識。因為也有一段時間沒有碰面﹐我竟然記不起了她們的名字。以前﹐我是不會忘掉每一個女生的姓和名。都怪她們古怪的愛爾蘭名字。只靠讀音﹐當然記不牢。不過﹐自己的記憶力開始退步﹐也是不容不承認的事。
我是記得第二戒條﹕YOU HAVE TO ASK,WHAT IS DANCING AT THE OFFICE PARTY FOR? WATCH OUT YOU DON'T GET CARRIED AWAY AND END UP DOING SOME INAPPROPRIATE SNOGGING OR WORSE。雖然如此﹐我還是跟一個美少女跳了幾隻舞。她很有禮貌地﹐輕輕在我耳邊說﹐你也跳得很好。我笑著回答﹐那是功多藝熟。況且﹐夏天旅行到現在﹐也已過了六個月。好歹也要有些進步罷﹖要不便浪費了這半年在愛爾蘭的日子。我看著她﹐她笑得很甜。不過﹐她還是「留起了最後一隻舞」。因為﹐她便是JOHN最近認識的女朋友。
在酒吧旁休息的時候﹐望著BARRY不斷跟這些悉心裝扮過的女生拍照﹐我有點後悔沒有帶同我的照相機同來。
我想起了LIONEL RICHIE的ALL NIGHT LONG。
Sunday, December 17, 2006
要不是母親的一句話﹐我想﹐我是不會在星期四夜晚飲酒跳舞狂歡到凌晨兩點半。
那天﹐在電話裡﹐我們談到聖誕派對。
我說﹐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公司的派對竟然安排了在星期四晚上舉行。第二天可還是要上班啊﹗而且舉行的地點不是市中心﹐是DALKEY那邊的一間堡壘酒店。DALKEY是都柏林南部的一個小城。那裡離住所有十五個火車站的距離。從CONNOLLY出發﹐大約要四十五分鐘車程。假若趕不上最後一班火車﹐除了等候計程車外﹐實在沒有他法(根本不可能跟上星期五一樣﹐走路回家)。到網上查過﹐星期四最後一班DART開十一點半。
那似乎很適合我。回到家﹐洗過澡﹐還有六個小時的睡眠﹐翌日應該可以精精神神上班。雖然﹐我知道﹐大家都準備星期五中飯時候才回到公司。上司AOIFE對此也不會有什麼投訴。正如朋友所說﹐好歹也是公司的活動啊﹗不過﹐對於準時上班﹐我從來都很STUBBORN。我以為﹐根本沒有一個理由容許自己遲到。所以﹐便是大家心照不宣﹐我也決定早上九時在公司出現。
其實﹐SOCIAL CLUB也不是沒有安排大家離開。他們預備了旅遊巴士接載我們或北上都柏林﹐或南下CO WICKLOW。只是﹐巴士離開時間倒是凌晨二時三十分。那是不想破壞大家狂歡興致的緣故。假如覺得太晚﹐不大合適回家﹐或想藉此來一個長週末假期﹐也可以訂酒店的房間。用公司的名義預訂﹐房租都有優惠。我以為﹐這兩個提議﹐對我來說﹐都不大合適。
豈料﹐母親卻說﹐倒有點想不到。其實以前在香港的時候﹐你也經常凌晨四﹑五點才回家﹐第二天一樣七點爬起身上班。還會打電話吵醒別人﹐叫他們準時回公司。我想不到那原來會是一個問題。
我當然聽得到她背後意思﹐甚至想像到她那扮作神氣的樣子。只是﹐母親說的﹐倒是實話。我想起了早幾年的那些荒唐歲月。那時候﹐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會到外耍樂。凌晨一點回到家算是早歸的了。每天起床﹐總會聽到她的怨言。何解來到愛爾蘭獨自生活後﹐反而變得諸多顧忌﹖難道真的是因為又多過了幾個春秋﹐知道自己精力未能跟舊時一樣快速回復﹖
也許﹐的確是年紀大了。近來﹐總覺得記憶力有點不如前。對於這個觀察﹐我倒是有點害怕。因為想不到時間真的過得這樣快。當知道幾多人在這個年紀﹐已經闖出了自己的一番事業後﹐我實在很害怕知道﹐原來自己已到了那個應該突破的時候﹐甚至乎已過了那個歲數。以前﹐我相信自己並非池中物。不過﹐到了這一刻﹐我的信心已經剩餘無幾。或者﹐我真的只是他和他和他和他和他的一份子。只是﹐我實在很不願意﹐跟他和他和他和他和他一樣﹐平淡地過自己一生。
常言道﹐努力要趁年青。我想﹐那是因為只有年輕人才有魄力和精神去為自己的理想奮鬥。當人大了﹑老了﹐便是那些尖銳的角都未有給世事和挫折磨鈍﹐我們的肉身軀體也不再適合為那飄渺遠大的理想衝刺了。始終﹐時間永遠跑在我們前頭。浪費了的時間便是浪費了的時間﹐那是追不回來。
不過﹐我也同意﹐浪費光陰是每個年青人都要做一做的事。因為那是青春的SIGNATURE﹕我能浪費光陰﹐因為我還年青﹐還有很多時間﹐你能嗎﹖當中的關鍵﹐倒是一個人究竟到什麼時候﹐方發現自己不能再浪費青春。只是﹐世上太多人都在老了的時候﹐才知道自己以前浪費得太多寶貴光陰。於是﹐大部份人都只能平白地過其一生。因為他們再沒有魄力和精神去為那偉大的理想奮鬥。
為了證實自己還年輕﹐還有力去實現那遠大的理想﹐在最後一刻﹐我到SOCIAL CLUB買了一張凌晨兩點半﹐從堡壘酒店開往都柏林的巴士票。
星期五早上﹐我九時回到公司。裡面才得不過十個人。AOIFE見到我﹐有點詫異。她以為我早早離開。我想﹐那是因為她還不十分了解我。當然﹐她更加詫異﹐當她知道我一天內便辦妥那些緊急的圖則。
那天﹐在電話裡﹐我們談到聖誕派對。
我說﹐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公司的派對竟然安排了在星期四晚上舉行。第二天可還是要上班啊﹗而且舉行的地點不是市中心﹐是DALKEY那邊的一間堡壘酒店。DALKEY是都柏林南部的一個小城。那裡離住所有十五個火車站的距離。從CONNOLLY出發﹐大約要四十五分鐘車程。假若趕不上最後一班火車﹐除了等候計程車外﹐實在沒有他法(根本不可能跟上星期五一樣﹐走路回家)。到網上查過﹐星期四最後一班DART開十一點半。
那似乎很適合我。回到家﹐洗過澡﹐還有六個小時的睡眠﹐翌日應該可以精精神神上班。雖然﹐我知道﹐大家都準備星期五中飯時候才回到公司。上司AOIFE對此也不會有什麼投訴。正如朋友所說﹐好歹也是公司的活動啊﹗不過﹐對於準時上班﹐我從來都很STUBBORN。我以為﹐根本沒有一個理由容許自己遲到。所以﹐便是大家心照不宣﹐我也決定早上九時在公司出現。
其實﹐SOCIAL CLUB也不是沒有安排大家離開。他們預備了旅遊巴士接載我們或北上都柏林﹐或南下CO WICKLOW。只是﹐巴士離開時間倒是凌晨二時三十分。那是不想破壞大家狂歡興致的緣故。假如覺得太晚﹐不大合適回家﹐或想藉此來一個長週末假期﹐也可以訂酒店的房間。用公司的名義預訂﹐房租都有優惠。我以為﹐這兩個提議﹐對我來說﹐都不大合適。
豈料﹐母親卻說﹐倒有點想不到。其實以前在香港的時候﹐你也經常凌晨四﹑五點才回家﹐第二天一樣七點爬起身上班。還會打電話吵醒別人﹐叫他們準時回公司。我想不到那原來會是一個問題。
我當然聽得到她背後意思﹐甚至想像到她那扮作神氣的樣子。只是﹐母親說的﹐倒是實話。我想起了早幾年的那些荒唐歲月。那時候﹐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會到外耍樂。凌晨一點回到家算是早歸的了。每天起床﹐總會聽到她的怨言。何解來到愛爾蘭獨自生活後﹐反而變得諸多顧忌﹖難道真的是因為又多過了幾個春秋﹐知道自己精力未能跟舊時一樣快速回復﹖
也許﹐的確是年紀大了。近來﹐總覺得記憶力有點不如前。對於這個觀察﹐我倒是有點害怕。因為想不到時間真的過得這樣快。當知道幾多人在這個年紀﹐已經闖出了自己的一番事業後﹐我實在很害怕知道﹐原來自己已到了那個應該突破的時候﹐甚至乎已過了那個歲數。以前﹐我相信自己並非池中物。不過﹐到了這一刻﹐我的信心已經剩餘無幾。或者﹐我真的只是他和他和他和他和他的一份子。只是﹐我實在很不願意﹐跟他和他和他和他和他一樣﹐平淡地過自己一生。
常言道﹐努力要趁年青。我想﹐那是因為只有年輕人才有魄力和精神去為自己的理想奮鬥。當人大了﹑老了﹐便是那些尖銳的角都未有給世事和挫折磨鈍﹐我們的肉身軀體也不再適合為那飄渺遠大的理想衝刺了。始終﹐時間永遠跑在我們前頭。浪費了的時間便是浪費了的時間﹐那是追不回來。
不過﹐我也同意﹐浪費光陰是每個年青人都要做一做的事。因為那是青春的SIGNATURE﹕我能浪費光陰﹐因為我還年青﹐還有很多時間﹐你能嗎﹖當中的關鍵﹐倒是一個人究竟到什麼時候﹐方發現自己不能再浪費青春。只是﹐世上太多人都在老了的時候﹐才知道自己以前浪費得太多寶貴光陰。於是﹐大部份人都只能平白地過其一生。因為他們再沒有魄力和精神去為那偉大的理想奮鬥。
為了證實自己還年輕﹐還有力去實現那遠大的理想﹐在最後一刻﹐我到SOCIAL CLUB買了一張凌晨兩點半﹐從堡壘酒店開往都柏林的巴士票。
星期五早上﹐我九時回到公司。裡面才得不過十個人。AOIFE見到我﹐有點詫異。她以為我早早離開。我想﹐那是因為她還不十分了解我。當然﹐她更加詫異﹐當她知道我一天內便辦妥那些緊急的圖則。
Saturday, December 16, 2006
下班後﹐在火車上讀著朝早未讀完的報紙。
看到了一段關於碧咸的新聞。那不是他決定到美國大聯盟落班﹐也不是他又給發現有婚外情。那是關於他自己那間公司的新聞。因為那間叫FOOTWORK的公司最近公佈業績。公司秘書是碧咸的老婆維多利亞。他的外父則是公司的董事。
根據公佈的業績﹐碧咸依然是全球最賺錢的足球員。BY A WIDE MARGIN。縱然他的零六年的廣告收入﹐比前一年跌了十個百分點。他的最大客戶﹐依舊是PEPSI、ADIDAS和GILLETTE。報告顯示﹐萬人迷跟這些大客戶的合約都是死約﹐直至2010年。所以﹐便是碧咸受歡迎程度繼續下降﹐也無礙他那接下來四年的可觀收入。眾所週知﹐這位前英格蘭隊長的廣告費遠超球會給他的薪金。
讀著這段新聞﹐我不其然想起了以前《信報》裡面孔少林和方卓如的專欄。我想﹐由他們來分析碧咸這一間公司﹐一定十分有趣。因為他們有這方面豐富的知識﹐亦是標準的足球迷。不過﹐拜李澤楷幫忙﹐他們都不能不告別那份財經報紙。以前﹐他們兩人對這位香港首富小兒的批判實在太過嚴苛﹑刻薄。當林行止先生把自己一生的心血賣給RICHARD後﹐孔少林和方卓如當然是要首先給革掉的人。沒有太多老闆容許下屬對自己諸多批判﹐雖然孔和方都只是《信報》的專欄作家。
早陣子﹐李澤楷的PCCW又成為了話題。(沒有錯﹐依然是他的PCCW。)他們用了一個天價﹐把英格蘭超級聯賽的香港播映權﹐從CABLE TV手上搶了過來。我不知道﹐這樣會對有線電視有什麼影響。不過﹐跟父親傾開電話﹐知道他正考慮放棄CABLE TV,只保留PCCW NOW。我想﹐有線電視現有客戶裡面有這個想法的﹐父親並不是唯一一個。印象中﹐以前有線電視吸引我的節目/電視臺﹐都已全部轉到了NOW旗下。
我以為﹐CABLE TV最錯的一著﹐便是當年放棄ESPN,讓NOW冷手執個熱煎堆。那就是PCCW NOW開始發圍的時候。跟有線一樣﹐也是從體育節目開始吸引觀眾。要知道﹐ESPN的的確確是THE WORLD LEADER IN SPORTS。以香港電視臺的規模﹐根本沒有可能發展到跟ESPN一樣。沒有了這個美國體育頻道後﹐CABLE TV就失去了兩個皇牌節目﹕英格蘭超級聯賽和歐洲聯賽冠軍杯。三年前﹐有線用高價搶回EPL。只是﹐現在又再次失去了。
假如三年後CABLE TV依然能夠生存下去﹐似乎又一場高價爭奪戰將又會展開。那個播映權的價錢將越來越高。難怪CHARLTON主席見勢色不對勁﹐便立即解僱今年夏天才聘回來的領隊。他說﹐我們不能降班﹐因為下屆的轉播費是歷史新高。所有超級聯賽球會都會從電視臺手上面﹐得到一大筆非常可觀的金錢。CHARLTON現時在聯賽榜排包尾。
只是﹐那個播映權的價錢真的將會越來越高嗎﹖
記得以前孔少林分析過世界杯轉播的事宜。他說﹐
「互聯網無遠弗屆,寬頻上網滲透率肯定比收費電視高,現在配合日漸成熟的點對點技術,在網上收看球賽質素其實比電視差不了多少,所以就算不是免費,相信絕不乏支持者,至少免去等人上門安裝的數個小時。
現在世界各地電視台要付高昂費用購買世界盃播映權,長遠來說,究竟國際足協持什麼理由需要這些中間人?BBC今年已向英國用戶以網上直播英格蘭賽事,相信國際足協現在也有能力這樣做,只不過向電視台收費較容易,而且錢又早已入袋,沒有需要試新招。將來球迷大概可直接使用信用卡付款,按每場收費形式,從國際足協網站直接收看比賽。但網上非法轉播問題始終不容易解決,尤其是大部分搞事分子都不以賺錢為目標,不能動之以利。最終內容供應者最穩陣的賺錢方法,可能都是靠廣告。為了增加廣告時間,我相信足球比賽將由現在的上下半場變成四節,再加上比賽中途的暫停,以提供更多廣告窗口─這正是美國職業球賽的形式。除此之外,球衣上的廣告,也必定大幅增加,就好像現在賽車手的戰衣一樣。」
他估計﹐四年後的南非世界盃,收費電視台如果仍嘗試以高價收購播映權以增加新用戶,成效將很有限。
我也相信﹐我們逐場付鈔﹐在網上看球賽的日子應該不遠了。
看到了一段關於碧咸的新聞。那不是他決定到美國大聯盟落班﹐也不是他又給發現有婚外情。那是關於他自己那間公司的新聞。因為那間叫FOOTWORK的公司最近公佈業績。公司秘書是碧咸的老婆維多利亞。他的外父則是公司的董事。
根據公佈的業績﹐碧咸依然是全球最賺錢的足球員。BY A WIDE MARGIN。縱然他的零六年的廣告收入﹐比前一年跌了十個百分點。他的最大客戶﹐依舊是PEPSI、ADIDAS和GILLETTE。報告顯示﹐萬人迷跟這些大客戶的合約都是死約﹐直至2010年。所以﹐便是碧咸受歡迎程度繼續下降﹐也無礙他那接下來四年的可觀收入。眾所週知﹐這位前英格蘭隊長的廣告費遠超球會給他的薪金。
讀著這段新聞﹐我不其然想起了以前《信報》裡面孔少林和方卓如的專欄。我想﹐由他們來分析碧咸這一間公司﹐一定十分有趣。因為他們有這方面豐富的知識﹐亦是標準的足球迷。不過﹐拜李澤楷幫忙﹐他們都不能不告別那份財經報紙。以前﹐他們兩人對這位香港首富小兒的批判實在太過嚴苛﹑刻薄。當林行止先生把自己一生的心血賣給RICHARD後﹐孔少林和方卓如當然是要首先給革掉的人。沒有太多老闆容許下屬對自己諸多批判﹐雖然孔和方都只是《信報》的專欄作家。
早陣子﹐李澤楷的PCCW又成為了話題。(沒有錯﹐依然是他的PCCW。)他們用了一個天價﹐把英格蘭超級聯賽的香港播映權﹐從CABLE TV手上搶了過來。我不知道﹐這樣會對有線電視有什麼影響。不過﹐跟父親傾開電話﹐知道他正考慮放棄CABLE TV,只保留PCCW NOW。我想﹐有線電視現有客戶裡面有這個想法的﹐父親並不是唯一一個。印象中﹐以前有線電視吸引我的節目/電視臺﹐都已全部轉到了NOW旗下。
我以為﹐CABLE TV最錯的一著﹐便是當年放棄ESPN,讓NOW冷手執個熱煎堆。那就是PCCW NOW開始發圍的時候。跟有線一樣﹐也是從體育節目開始吸引觀眾。要知道﹐ESPN的的確確是THE WORLD LEADER IN SPORTS。以香港電視臺的規模﹐根本沒有可能發展到跟ESPN一樣。沒有了這個美國體育頻道後﹐CABLE TV就失去了兩個皇牌節目﹕英格蘭超級聯賽和歐洲聯賽冠軍杯。三年前﹐有線用高價搶回EPL。只是﹐現在又再次失去了。
假如三年後CABLE TV依然能夠生存下去﹐似乎又一場高價爭奪戰將又會展開。那個播映權的價錢將越來越高。難怪CHARLTON主席見勢色不對勁﹐便立即解僱今年夏天才聘回來的領隊。他說﹐我們不能降班﹐因為下屆的轉播費是歷史新高。所有超級聯賽球會都會從電視臺手上面﹐得到一大筆非常可觀的金錢。CHARLTON現時在聯賽榜排包尾。
只是﹐那個播映權的價錢真的將會越來越高嗎﹖
記得以前孔少林分析過世界杯轉播的事宜。他說﹐
「互聯網無遠弗屆,寬頻上網滲透率肯定比收費電視高,現在配合日漸成熟的點對點技術,在網上收看球賽質素其實比電視差不了多少,所以就算不是免費,相信絕不乏支持者,至少免去等人上門安裝的數個小時。
現在世界各地電視台要付高昂費用購買世界盃播映權,長遠來說,究竟國際足協持什麼理由需要這些中間人?BBC今年已向英國用戶以網上直播英格蘭賽事,相信國際足協現在也有能力這樣做,只不過向電視台收費較容易,而且錢又早已入袋,沒有需要試新招。將來球迷大概可直接使用信用卡付款,按每場收費形式,從國際足協網站直接收看比賽。但網上非法轉播問題始終不容易解決,尤其是大部分搞事分子都不以賺錢為目標,不能動之以利。最終內容供應者最穩陣的賺錢方法,可能都是靠廣告。為了增加廣告時間,我相信足球比賽將由現在的上下半場變成四節,再加上比賽中途的暫停,以提供更多廣告窗口─這正是美國職業球賽的形式。除此之外,球衣上的廣告,也必定大幅增加,就好像現在賽車手的戰衣一樣。」
他估計﹐四年後的南非世界盃,收費電視台如果仍嘗試以高價收購播映權以增加新用戶,成效將很有限。
我也相信﹐我們逐場付鈔﹐在網上看球賽的日子應該不遠了。
Friday, December 15, 2006
自EU接納一些東歐國家成為會員開始﹐經濟發達的西歐國家﹐便開始充斥著從東面湧過來的勞動人口。
愛爾蘭當然沒有例外。有時候﹐在市中心走走﹐你會發覺整條街都沒有人用英語交談。因為都不是本地人。很多的是波蘭人。也有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來的人。去年的公開考試﹐甚至有波蘭文﹑拉脫維亞文﹑立陶宛文等多種東歐語言的試卷讓考生選擇。可以想像住在愛爾蘭的東歐人數目。
他們都來愛爾蘭工作﹐因為這兒的薪金比他們在自己國家的高幾倍。聽說﹐在都柏林工作兩﹑三年﹐便可以回鄉買大屋了。有著這樣大的吸引力﹐當然很多人都願意離鄉別井﹐好讓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能夠過得好些。
最近﹐便認識了一個立陶宛人。他是公司的同事。不過﹐不同部門。很多時候﹐上班下班﹐我都會跟他搭上同一班火車﹐於是﹐便開始交談起來。有時﹐我們會談談工作上的趣事﹔有時﹐我們會講講各自家鄉的事情。
今天早上﹐從火車站走回公司﹐他突然問我﹐究竟香港的最低工資是多少﹖
我望著他﹐呼出一口暖暖的白煙﹐笑著說﹐香港沒有最低工資這回事。
怎麼可能﹖所有國家都有最低工資的啊﹗
香港就是沒有。
他依然不相信。他說﹐這是否表示你可以用一角聘請一個人幫你工作﹖
我說﹐理論上﹐你是可以。不過﹐便看看你能否用一角聘請到一個人幫你工作。香港是經濟最自由的地方。
我有點氣。不過﹐不想跟他討論。我想﹐也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講得明白。怎能容易說得明白﹖
從來﹐我都很同意STIGLER的看法。從市場角度看,勞工亦是商品,其價格因此要由供求決定。眾所周知,供不應求令商品價格上升,反之下跌;工資高低亦應取決於勞工市場供需情況,不可由政府替商界代謀。工資是「中性」的,這即是說,市場決定的工資與受薪者所需無關,比方說,一名工人每月養家要一萬元,這是他的私事,與僱主無關,因此,工人所得多寡,與道德和公義完全扯不上邊。
況且﹐正如林行止先生早陣子所講﹐把最低工資定得太高反而會帶來反效果。
第一、它會使僱主不願聘請非技術非熟練工人,因為他們「不值這個工錢」,結果造成低下層工人失業情況嚴重,成為「最低工資」制度下的受害者,為社會治安製造更多問題,同時加重社會福利負擔;
第二、如果非技術非熟練工人可得比較高的「最低工資」,可能會打消那麼本來有意進職業學校學一技之長以賺取較高工資的青少年求學的主意,因為「不學無技」便有可觀的收入,為何還要在進修上作重大投資(讀書需要時間,而這有機會成本─上學的時間本可工作賺錢,有關收入因為上學而消於無形)。
香港最為我自豪的地方﹐便是她的自由經濟。
愛爾蘭當然沒有例外。有時候﹐在市中心走走﹐你會發覺整條街都沒有人用英語交談。因為都不是本地人。很多的是波蘭人。也有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來的人。去年的公開考試﹐甚至有波蘭文﹑拉脫維亞文﹑立陶宛文等多種東歐語言的試卷讓考生選擇。可以想像住在愛爾蘭的東歐人數目。
他們都來愛爾蘭工作﹐因為這兒的薪金比他們在自己國家的高幾倍。聽說﹐在都柏林工作兩﹑三年﹐便可以回鄉買大屋了。有著這樣大的吸引力﹐當然很多人都願意離鄉別井﹐好讓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能夠過得好些。
最近﹐便認識了一個立陶宛人。他是公司的同事。不過﹐不同部門。很多時候﹐上班下班﹐我都會跟他搭上同一班火車﹐於是﹐便開始交談起來。有時﹐我們會談談工作上的趣事﹔有時﹐我們會講講各自家鄉的事情。
今天早上﹐從火車站走回公司﹐他突然問我﹐究竟香港的最低工資是多少﹖
我望著他﹐呼出一口暖暖的白煙﹐笑著說﹐香港沒有最低工資這回事。
怎麼可能﹖所有國家都有最低工資的啊﹗
香港就是沒有。
他依然不相信。他說﹐這是否表示你可以用一角聘請一個人幫你工作﹖
我說﹐理論上﹐你是可以。不過﹐便看看你能否用一角聘請到一個人幫你工作。香港是經濟最自由的地方。
我有點氣。不過﹐不想跟他討論。我想﹐也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講得明白。怎能容易說得明白﹖
從來﹐我都很同意STIGLER的看法。從市場角度看,勞工亦是商品,其價格因此要由供求決定。眾所周知,供不應求令商品價格上升,反之下跌;工資高低亦應取決於勞工市場供需情況,不可由政府替商界代謀。工資是「中性」的,這即是說,市場決定的工資與受薪者所需無關,比方說,一名工人每月養家要一萬元,這是他的私事,與僱主無關,因此,工人所得多寡,與道德和公義完全扯不上邊。
況且﹐正如林行止先生早陣子所講﹐把最低工資定得太高反而會帶來反效果。
第一、它會使僱主不願聘請非技術非熟練工人,因為他們「不值這個工錢」,結果造成低下層工人失業情況嚴重,成為「最低工資」制度下的受害者,為社會治安製造更多問題,同時加重社會福利負擔;
第二、如果非技術非熟練工人可得比較高的「最低工資」,可能會打消那麼本來有意進職業學校學一技之長以賺取較高工資的青少年求學的主意,因為「不學無技」便有可觀的收入,為何還要在進修上作重大投資(讀書需要時間,而這有機會成本─上學的時間本可工作賺錢,有關收入因為上學而消於無形)。
香港最為我自豪的地方﹐便是她的自由經濟。
Thursday, December 14, 2006
在《泰晤士河畔》一書裡﹐陶傑向一些準備到英國生活的人﹐給了一些意見。他寫道﹐「...即便要揚帆移民﹐請航向多一些陽光的國度。除閣下的嗜好仍與十七歲在畫報上徵友時無異﹕愛對大海沉思﹑獨自欣賞日落﹑追尋煙雨中的康橋﹐以及在火爐邊細讀《小婦人》與《咆哮山莊》﹐否則英國絕對是閣下的人間地獄。」
最近﹐也收到一位朋友的信。她曾經在英國讀書﹐深知英國的冬天。在信裡面﹐她說﹐「...沒有太多陽光的日子﹐我知道那滋味。便是開大了暖爐﹐躲在被窩裡面﹐也是冰冷的﹑孤寂的。的確﹐讓人難耐。」
愛爾蘭跟英國﹐只隔了一個愛爾蘭海(IRISH SEA)。同樣是一個島國。大家的經緯也差不多。都是地偏北國﹐鄰近北極圈﹐面臨大西洋不絕的寒流﹐鮮有陽光眷顧﹐卻深得雨神垂青。在冬天的日子﹐這一切更加明顯。日照時間實在非常短暫。早上八時許﹐太陽才正式露面﹐六個小時之後﹐它便經已回家休息。還未提及那陰霾密佈的天氣﹐和那經常偷襲的雨雲。中午的驕陽﹐往往忽爾翻臉成無窮的油酥細雨。
現在﹐還是初冬的日子﹐空氣還不至於很冰冷。至少﹐我依然未開過家裡的電暖爐。日間的氣味大約也有九﹑十度。晚上的時候﹐跌到零度也不是經常發生的事。印象中﹐至目前為止﹐才發生過一次。記得AIDAN說過﹐二﹑三月方是此間最寒冷的時候。假若連這位仁兄也說﹐年初的日子寒冷異常﹐我想﹐我也應該要有一些心理準備。要知道﹐在十一﹑二月期間﹐他們這些愛爾蘭人依然可以穿著短袖T恤在街上行走。
我不知道什麼是「在畫報上徵友」。不過﹐我相信﹐對於我來說﹐愛爾蘭不會是一個人間地獄。因為我的確可以整天躲在被窩裡翻閱小說。縱然那並不是《小婦人》與《咆哮山莊》。
最近﹐我在讀STEPHEN KING的THE SHINING。是我首次讀這位驚嚇大師的作品。
在腦海裡﹐想像著科羅拉多的冬季和那與世隔絕的酒店﹐我深知﹐愛爾蘭根本不可能是一個人間地獄。雖然我每天都在埋頭寫我的BLOG,跟JACK TORRANCE每天都在埋頭寫他的作品一樣﹐不過﹐可知道﹐我住的地方乃是都柏林的市中心﹐跑到街上﹐不消十分鐘﹐便可以到達這兒最大的一條街道O'CONNELL STREET。還有百貨公司林立的HENRY STREET。我想﹐無論如何﹐我也不可能變成JACK TORRANCE。
便是讀完了《閃靈》﹐家裡還有一大堆未讀完﹐以至未開始讀的書。有時候﹐我總覺得﹐我買書買得有點病態。我發覺﹐我是喜歡買書﹐多過讀書。縱然﹐有人以為﹐那只是因為我買書的速度﹐比我讀書的速度快。曾經﹐我也是這樣欺騙自己。只是﹐你是可以騙得到世界上所有人﹐可唯獨是自己你是無論如何也騙不了。
最近﹐我倒是控制得了病情。
經過書店﹐看到了JEFFREY ARCHER的新書。是一個短篇故事集。都是他服刑期間﹐從一些囚犯口中聽回來的故事。我翻了翻﹐發覺很有趣。至少﹐比他上一部FALSE IMPRESSION好。(我始終以為﹐那是模仿DA VINCI CODE的作品。JEFFREY ARCHER竟然要跟DAN BROWN學習﹖希望那是一個錯的印象。)我很想買下來。不過﹐每當我準備走到櫃檯付錢的時候﹐我都刻意提醒自己家裡還有很多書。掙扎了一會兒後﹐便都能夠把書放回書架上。面對著STEPHEN KING與JOHN LE CARRÉ的新作﹐以及大家一致讚好的THE MEANING OF THE NIGHT,我都是如此應付。
如是者﹐原來我也有差不多一個月﹐沒有為家裡的書架添上新書了。或者﹐也應該藉CHRISTMAS SHOPPING的時候﹐給自己買些禮物。
最近﹐也收到一位朋友的信。她曾經在英國讀書﹐深知英國的冬天。在信裡面﹐她說﹐「...沒有太多陽光的日子﹐我知道那滋味。便是開大了暖爐﹐躲在被窩裡面﹐也是冰冷的﹑孤寂的。的確﹐讓人難耐。」
愛爾蘭跟英國﹐只隔了一個愛爾蘭海(IRISH SEA)。同樣是一個島國。大家的經緯也差不多。都是地偏北國﹐鄰近北極圈﹐面臨大西洋不絕的寒流﹐鮮有陽光眷顧﹐卻深得雨神垂青。在冬天的日子﹐這一切更加明顯。日照時間實在非常短暫。早上八時許﹐太陽才正式露面﹐六個小時之後﹐它便經已回家休息。還未提及那陰霾密佈的天氣﹐和那經常偷襲的雨雲。中午的驕陽﹐往往忽爾翻臉成無窮的油酥細雨。
現在﹐還是初冬的日子﹐空氣還不至於很冰冷。至少﹐我依然未開過家裡的電暖爐。日間的氣味大約也有九﹑十度。晚上的時候﹐跌到零度也不是經常發生的事。印象中﹐至目前為止﹐才發生過一次。記得AIDAN說過﹐二﹑三月方是此間最寒冷的時候。假若連這位仁兄也說﹐年初的日子寒冷異常﹐我想﹐我也應該要有一些心理準備。要知道﹐在十一﹑二月期間﹐他們這些愛爾蘭人依然可以穿著短袖T恤在街上行走。
我不知道什麼是「在畫報上徵友」。不過﹐我相信﹐對於我來說﹐愛爾蘭不會是一個人間地獄。因為我的確可以整天躲在被窩裡翻閱小說。縱然那並不是《小婦人》與《咆哮山莊》。
最近﹐我在讀STEPHEN KING的THE SHINING。是我首次讀這位驚嚇大師的作品。
在腦海裡﹐想像著科羅拉多的冬季和那與世隔絕的酒店﹐我深知﹐愛爾蘭根本不可能是一個人間地獄。雖然我每天都在埋頭寫我的BLOG,跟JACK TORRANCE每天都在埋頭寫他的作品一樣﹐不過﹐可知道﹐我住的地方乃是都柏林的市中心﹐跑到街上﹐不消十分鐘﹐便可以到達這兒最大的一條街道O'CONNELL STREET。還有百貨公司林立的HENRY STREET。我想﹐無論如何﹐我也不可能變成JACK TORRANCE。
便是讀完了《閃靈》﹐家裡還有一大堆未讀完﹐以至未開始讀的書。有時候﹐我總覺得﹐我買書買得有點病態。我發覺﹐我是喜歡買書﹐多過讀書。縱然﹐有人以為﹐那只是因為我買書的速度﹐比我讀書的速度快。曾經﹐我也是這樣欺騙自己。只是﹐你是可以騙得到世界上所有人﹐可唯獨是自己你是無論如何也騙不了。
最近﹐我倒是控制得了病情。
經過書店﹐看到了JEFFREY ARCHER的新書。是一個短篇故事集。都是他服刑期間﹐從一些囚犯口中聽回來的故事。我翻了翻﹐發覺很有趣。至少﹐比他上一部FALSE IMPRESSION好。(我始終以為﹐那是模仿DA VINCI CODE的作品。JEFFREY ARCHER竟然要跟DAN BROWN學習﹖希望那是一個錯的印象。)我很想買下來。不過﹐每當我準備走到櫃檯付錢的時候﹐我都刻意提醒自己家裡還有很多書。掙扎了一會兒後﹐便都能夠把書放回書架上。面對著STEPHEN KING與JOHN LE CARRÉ的新作﹐以及大家一致讚好的THE MEANING OF THE NIGHT,我都是如此應付。
如是者﹐原來我也有差不多一個月﹐沒有為家裡的書架添上新書了。或者﹐也應該藉CHRISTMAS SHOPPING的時候﹐給自己買些禮物。
Wednesday, December 13, 2006
當被問及究竟曼聯這一間球會代表什麼存在的時候﹐球壇名宿積查爾頓跟記者道﹕對於很多勞動階層來說﹐到球場看球賽﹐實是他們整個星期裡面最興奮的時候。猶記得畢士比經常對我們說﹐帶給球迷他自己做不到的事。因此﹐曼聯永遠強調打進攻足球。(For men who work on the shop floor, the one highlight of their week is to go and watch football. Matt Busby used to say you should give that man something he can't do himself. That's why Manchester Utd always play attacking football.)
積查爾頓(Jack Charlton)是曼聯歷史上面偉大的球員﹐現在是球會的高層﹔畢士比(Matt Busby)則是比費格遜更偉大的曼聯領導。
我想﹐這是紅魔鬼成功的秘訣。
跟電視﹑電影﹑流行音樂一樣﹐足球比賽也是一項娛樂事業。都是為了娛樂大眾。只要想通這一點﹐並經常把JACK CHARLTON那句話放在心上﹐如何挽救香港足球聯賽這個局﹐實不難拆。
我相信﹐關鍵就是要帶給球迷他們自己做不到的事。當球賽再未能提供娛樂﹐當球員的水準跟自己不遑多讓﹐當到球場去再不是自己一星期裡最興奮的時候﹐實在想不到一個原因﹐為何還要入場觀看球賽﹖更甚的是﹐亦想不到一個原因﹐為何還要關心那個聯賽﹖
要吸引球迷走回球場﹐辦球賽的人一定要多鑄入一些ENTERTAINERS。當然﹐最容易使人想到的便是球員。假如香港聯賽的球員能夠媲美英格蘭EPL﹑西班牙LA LIGA,香港球迷一定不會再躲在電視面前觀看球賽。
不過﹐那當然是痴人說夢。我不是說﹐香港球員的水平永遠沒有可能比得上外國球員。只是﹐我怕當他們有了那個水準的時候,香港已經再沒有什麼足球聯賽。
始終﹐遠水不能救近火。
我以為﹐香港足總應該注視的是球場裡面的氣氛。這是唯一能夠贏得歐洲聯賽的範疇。因為到球場看球賽跟在電視面前看﹐實在相差得太遠。要讓球迷記起到球場看球賽的滋味。那是球圈中人要多研究的地方。
也許﹐你會說﹐那是雞和雞蛋的問題。因為假如球賽吸引﹐一定能使球迷入場觀看﹔一多球迷入場觀看﹐球場氣氛自然好﹔現場看球賽的氣氛好﹐球迷必定不斷捧場。
你的講法當然有道理。不過﹐實在有很多方法吸引球迷。球賽水準其實只是其中一樣。
例如﹐兩年前﹐正值「愛國論」討論熾熱的時候﹐香港便要在世界杯外圍賽面對中國隊。假如香港足總夠GUTS,就應該來一個政治和足球的CROSSOVER,廣邀民主派跟土共討論香港隊在這個DILEMMA底下﹐應該如何自處。或者暗中出錢﹐宣傳中資機構僱員到球場支持中國隊有叉燒飯送﹐然後又免費在球場替民主派候選人拉橫額。甚至巧妙地散播謠言﹐暗示有人要求香港隊故意輸掉球賽(只是﹐那個是一個事實)。太多太多的方法﹐去讓球賽成為焦點﹔太多太多的方法﹐去吸引球迷以至非球迷入場觀看球賽。只是﹐他們都一一錯過。
要拉球迷走回球場﹐我們當然不能跟歐洲聯賽比拼水準。我們只有用其他方法。不過﹐倒是要動動腦筋﹐和敢拿出一點勇氣才成。
只是﹐為什麼我還未香港足球操心﹖我不是說過要香港足總倒閉的麼﹖
積查爾頓(Jack Charlton)是曼聯歷史上面偉大的球員﹐現在是球會的高層﹔畢士比(Matt Busby)則是比費格遜更偉大的曼聯領導。
我想﹐這是紅魔鬼成功的秘訣。
跟電視﹑電影﹑流行音樂一樣﹐足球比賽也是一項娛樂事業。都是為了娛樂大眾。只要想通這一點﹐並經常把JACK CHARLTON那句話放在心上﹐如何挽救香港足球聯賽這個局﹐實不難拆。
我相信﹐關鍵就是要帶給球迷他們自己做不到的事。當球賽再未能提供娛樂﹐當球員的水準跟自己不遑多讓﹐當到球場去再不是自己一星期裡最興奮的時候﹐實在想不到一個原因﹐為何還要入場觀看球賽﹖更甚的是﹐亦想不到一個原因﹐為何還要關心那個聯賽﹖
要吸引球迷走回球場﹐辦球賽的人一定要多鑄入一些ENTERTAINERS。當然﹐最容易使人想到的便是球員。假如香港聯賽的球員能夠媲美英格蘭EPL﹑西班牙LA LIGA,香港球迷一定不會再躲在電視面前觀看球賽。
不過﹐那當然是痴人說夢。我不是說﹐香港球員的水平永遠沒有可能比得上外國球員。只是﹐我怕當他們有了那個水準的時候,香港已經再沒有什麼足球聯賽。
始終﹐遠水不能救近火。
我以為﹐香港足總應該注視的是球場裡面的氣氛。這是唯一能夠贏得歐洲聯賽的範疇。因為到球場看球賽跟在電視面前看﹐實在相差得太遠。要讓球迷記起到球場看球賽的滋味。那是球圈中人要多研究的地方。
也許﹐你會說﹐那是雞和雞蛋的問題。因為假如球賽吸引﹐一定能使球迷入場觀看﹔一多球迷入場觀看﹐球場氣氛自然好﹔現場看球賽的氣氛好﹐球迷必定不斷捧場。
你的講法當然有道理。不過﹐實在有很多方法吸引球迷。球賽水準其實只是其中一樣。
例如﹐兩年前﹐正值「愛國論」討論熾熱的時候﹐香港便要在世界杯外圍賽面對中國隊。假如香港足總夠GUTS,就應該來一個政治和足球的CROSSOVER,廣邀民主派跟土共討論香港隊在這個DILEMMA底下﹐應該如何自處。或者暗中出錢﹐宣傳中資機構僱員到球場支持中國隊有叉燒飯送﹐然後又免費在球場替民主派候選人拉橫額。甚至巧妙地散播謠言﹐暗示有人要求香港隊故意輸掉球賽(只是﹐那個是一個事實)。太多太多的方法﹐去讓球賽成為焦點﹔太多太多的方法﹐去吸引球迷以至非球迷入場觀看球賽。只是﹐他們都一一錯過。
要拉球迷走回球場﹐我們當然不能跟歐洲聯賽比拼水準。我們只有用其他方法。不過﹐倒是要動動腦筋﹐和敢拿出一點勇氣才成。
只是﹐為什麼我還未香港足球操心﹖我不是說過要香港足總倒閉的麼﹖
Tuesday, December 12, 2006
早幾天讀倫敦時報﹐看見了一個熟悉的臉孔。
那是梁家傑。
他宣佈參選特首﹐是上星期一THE TIMES五宗國際大事的其中一樣﹐佔了一整版。
JANE MACARTNEY替陶傑做了一個正面教材﹐示範了一次如何只寫故事主角身邊客觀的事和物﹐便能使讀者自自然然﹐走到了記者希望大家走到的那一邊。陶傑時常說﹐寫文章﹐要LET THE FACT SPEAK THE STORY。他說的FACT,便是指週邊的一切事件和物件。的確﹐它們都不會說話。不過﹐就是它們都不會說話﹐只要作者能夠正確選擇材料﹐便能從容冷靜地﹐讓文章在不偏不倚裡BIASED。那是觀察力和想像力的最佳FUSION。
以下是文中一些例子﹕
A well-dressed barrister and experienced politician, Alan Leong has just decided to run an almost hopless race.
Sitting in his smart book-lined office in central Hong Kong, surrounded by family photos and wearing a well-cut suit and matching tie and pocket handkerchief, he hardly fits the image of a crusader.
不過﹐整篇文章吸引我的﹐倒是JANE MACARTNEY如何寫曾蔭權。更直接的﹐應該是如何稱呼這位香港特首。
我不知道﹐現在南華早報寫曾蔭權時﹐還會否稱他做SIR DONALD。不過﹐在倫敦時報裡﹐曾蔭權已經只不過是DONALD TSANG。在英國傳媒眼中﹐他已經不配做大英帝國的爵士。那位駐北京的英國記者是這樣寫的﹐
Donald Tsang, the incumbent, is the clear favourite and has already effectively been anointed by the territory's communist masters in Beijing.
眾所週知﹐英國人階級觀念很重。所以﹐只要從英女皇手上領過了什麼銜頭﹐在報紙上﹐你的名字前面便不會再只是MR,或者MS。正如﹐曼聯領隊費格遜﹐在體育版的所有文章一提及他﹐就是SIR ALEX﹐ 不會只是ALEX FERGUSON。當然﹐還有那些LORD。
我不知道曾蔭權翻到那一頁時﹐有什麼想法。
也許﹐倫敦時報是一時大意﹐沒有查清所有材料﹐忽略了曾蔭權原來竟然是SIR DONALD。不過﹐倒也難怪他們。因為一隻PEKING政府的傀儡酒狗﹐怎麼可能是大英帝國的爵士﹖記者稱香港的宗主國做COMMUNIST MASTERS IN BEIJING。
始終是一篇講梁家傑參選特首的報導﹐記者是這樣簡單一句結束全文﹕MR LEONG PUTS ON A BRAVE FACE。
那是梁家傑。
他宣佈參選特首﹐是上星期一THE TIMES五宗國際大事的其中一樣﹐佔了一整版。
JANE MACARTNEY替陶傑做了一個正面教材﹐示範了一次如何只寫故事主角身邊客觀的事和物﹐便能使讀者自自然然﹐走到了記者希望大家走到的那一邊。陶傑時常說﹐寫文章﹐要LET THE FACT SPEAK THE STORY。他說的FACT,便是指週邊的一切事件和物件。的確﹐它們都不會說話。不過﹐就是它們都不會說話﹐只要作者能夠正確選擇材料﹐便能從容冷靜地﹐讓文章在不偏不倚裡BIASED。那是觀察力和想像力的最佳FUSION。
以下是文中一些例子﹕
A well-dressed barrister and experienced politician, Alan Leong has just decided to run an almost hopless race.
Sitting in his smart book-lined office in central Hong Kong, surrounded by family photos and wearing a well-cut suit and matching tie and pocket handkerchief, he hardly fits the image of a crusader.
不過﹐整篇文章吸引我的﹐倒是JANE MACARTNEY如何寫曾蔭權。更直接的﹐應該是如何稱呼這位香港特首。
我不知道﹐現在南華早報寫曾蔭權時﹐還會否稱他做SIR DONALD。不過﹐在倫敦時報裡﹐曾蔭權已經只不過是DONALD TSANG。在英國傳媒眼中﹐他已經不配做大英帝國的爵士。那位駐北京的英國記者是這樣寫的﹐
Donald Tsang, the incumbent, is the clear favourite and has already effectively been anointed by the territory's communist masters in Beijing.
眾所週知﹐英國人階級觀念很重。所以﹐只要從英女皇手上領過了什麼銜頭﹐在報紙上﹐你的名字前面便不會再只是MR,或者MS。正如﹐曼聯領隊費格遜﹐在體育版的所有文章一提及他﹐就是SIR ALEX﹐ 不會只是ALEX FERGUSON。當然﹐還有那些LORD。
我不知道曾蔭權翻到那一頁時﹐有什麼想法。
也許﹐倫敦時報是一時大意﹐沒有查清所有材料﹐忽略了曾蔭權原來竟然是SIR DONALD。不過﹐倒也難怪他們。因為一隻PEKING政府的傀儡酒狗﹐怎麼可能是大英帝國的爵士﹖記者稱香港的宗主國做COMMUNIST MASTERS IN BEIJING。
始終是一篇講梁家傑參選特首的報導﹐記者是這樣簡單一句結束全文﹕MR LEONG PUTS ON A BRAVE FACE。
Monday, December 11, 2006
有天﹐我在這裡說﹕
不知道從那時候開始﹐香港人便很喜歡把自己跟老伴在房中的事﹐肆無忌憚地講出口。什麼事情﹐都習慣在後面多加一個「性」字。像選擇性﹑建設性。或許﹐這是社會開放進步的象徵。只是﹐我依然是一個傳統的人。對於「競爭性特首選舉」這個詞語﹐我實在很反感。不過﹐在「一身叫雞氣」下﹐那又似乎使用得很自然。至少﹐很符合身份。
朋友讀後﹐留言道﹕
當the Oxford Dictionary每年都編進不少slang的時候,便代表語言是會隨着潮流改變。當人人都說「選擇性﹑建設性」的時候,中文裏多一個「性」字,也未至於改變原文的意思,也許還能令今時今日的讀者更易明白。
我想﹐她寫的the Oxford Dictionary就是大名鼎鼎的O.E.D.-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那是我準備送給女兒的第一份禮物。我以為﹐每一個家庭﹐都應該有一套牛津英文字典。)
我知道﹐隨著生活轉變﹐每年O.E.D.都會加入一些新字。像EMAIL這一個新字,經過編輯多年討論﹐就在近年編進字典裡面。只是﹐我真的不知道O.E.D.是否每年都會加入不少俚語﹐也很懶沒有去查究。不過﹐我很同意﹐語文應該有生命力。正如我在今年國慶日那篇BLOG寫道﹕
語文﹐從來都應該是跳躍的﹑活潑的。為了使自己更加完美﹐語文應該不斷吸收其他外來語的優越地方﹐來補自己的不足。例如﹐在法律條文裡面﹐中文始終未能像英文一樣﹐簡潔而條理地把事情表達出來。因為中文本身就有很多含糊的地方。三思而行的「三」便不是解三次﹐那是多次的意思。中文實在應該在保存模糊美的同時﹐也引入一些英語的思想﹐好讓自己能夠簡單直接說好規定和要求。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有望得到法治。法律條文總不能人言人殊。這應該是中文應走的方向。這應該是中文的出路。這是中國成為世界大國必定要走的路。
可是﹐我們又是否真的有需要在一些詞語後面多加一個「性」字﹖多加一個「性」字後﹐是否可以彌補到我們語文本身的不足﹖
我以為﹐並不如此。
「選擇性﹑建設性」這些詞語其實都不是中文。它們都是英文的直接翻譯。「選擇性」就是SELECTIVE。「建設性」便是CONSTRUCTIVE。「決定性」則是DECISIVE。很明顯﹐都是很粗暴地製造出來的新中文詞彙﹕先把字首翻譯過來﹐然後再把那個-TIVE變做「性」。很簡單。不過﹐那是既不尊重中文﹐也不理解英文的流氓行徑。我贊成引入外語﹐來填補語文裡面本身沒有的思想。可是﹐當我們自己本來就有一個(甚至多個)同樣意思的詞語時﹐我們是否還需要向外求助﹖盲目地把外文變做自己語文的一部份﹐只會增加民族裡面溝通的不便。我甚至以為﹐那是等於數典忘祖。是變賣自己歷史悠久的文化。
我不認為「選擇性﹑建設性」這些詞語能令今時今日的讀者更易明白。假如它們真的能夠讓讀者較易理解句子﹐那是因為那些讀者的大腦都鬧上便秘。給餵食了太多紅肉﹐沒有一點蔬菜水果﹐怎能不便秘﹖
況且﹐謊話講得多變會成真。人人都錯的時候﹐我們便會誤以為那是正確。那不是約定俗成。那是集體地賤賣優美的中國語文。
假如大家都認為那沒有問題﹐那麼﹐我們真的是來到了決定性的一刻﹐實在有需要選擇性地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假如你們以為這一句話通順無誤﹐假如你們以為這一句容易理解﹐我將無言。
不知道從那時候開始﹐香港人便很喜歡把自己跟老伴在房中的事﹐肆無忌憚地講出口。什麼事情﹐都習慣在後面多加一個「性」字。像選擇性﹑建設性。或許﹐這是社會開放進步的象徵。只是﹐我依然是一個傳統的人。對於「競爭性特首選舉」這個詞語﹐我實在很反感。不過﹐在「一身叫雞氣」下﹐那又似乎使用得很自然。至少﹐很符合身份。
朋友讀後﹐留言道﹕
當the Oxford Dictionary每年都編進不少slang的時候,便代表語言是會隨着潮流改變。當人人都說「選擇性﹑建設性」的時候,中文裏多一個「性」字,也未至於改變原文的意思,也許還能令今時今日的讀者更易明白。
我想﹐她寫的the Oxford Dictionary就是大名鼎鼎的O.E.D.-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那是我準備送給女兒的第一份禮物。我以為﹐每一個家庭﹐都應該有一套牛津英文字典。)
我知道﹐隨著生活轉變﹐每年O.E.D.都會加入一些新字。像EMAIL這一個新字,經過編輯多年討論﹐就在近年編進字典裡面。只是﹐我真的不知道O.E.D.是否每年都會加入不少俚語﹐也很懶沒有去查究。不過﹐我很同意﹐語文應該有生命力。正如我在今年國慶日那篇BLOG寫道﹕
語文﹐從來都應該是跳躍的﹑活潑的。為了使自己更加完美﹐語文應該不斷吸收其他外來語的優越地方﹐來補自己的不足。例如﹐在法律條文裡面﹐中文始終未能像英文一樣﹐簡潔而條理地把事情表達出來。因為中文本身就有很多含糊的地方。三思而行的「三」便不是解三次﹐那是多次的意思。中文實在應該在保存模糊美的同時﹐也引入一些英語的思想﹐好讓自己能夠簡單直接說好規定和要求。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有望得到法治。法律條文總不能人言人殊。這應該是中文應走的方向。這應該是中文的出路。這是中國成為世界大國必定要走的路。
可是﹐我們又是否真的有需要在一些詞語後面多加一個「性」字﹖多加一個「性」字後﹐是否可以彌補到我們語文本身的不足﹖
我以為﹐並不如此。
「選擇性﹑建設性」這些詞語其實都不是中文。它們都是英文的直接翻譯。「選擇性」就是SELECTIVE。「建設性」便是CONSTRUCTIVE。「決定性」則是DECISIVE。很明顯﹐都是很粗暴地製造出來的新中文詞彙﹕先把字首翻譯過來﹐然後再把那個-TIVE變做「性」。很簡單。不過﹐那是既不尊重中文﹐也不理解英文的流氓行徑。我贊成引入外語﹐來填補語文裡面本身沒有的思想。可是﹐當我們自己本來就有一個(甚至多個)同樣意思的詞語時﹐我們是否還需要向外求助﹖盲目地把外文變做自己語文的一部份﹐只會增加民族裡面溝通的不便。我甚至以為﹐那是等於數典忘祖。是變賣自己歷史悠久的文化。
我不認為「選擇性﹑建設性」這些詞語能令今時今日的讀者更易明白。假如它們真的能夠讓讀者較易理解句子﹐那是因為那些讀者的大腦都鬧上便秘。給餵食了太多紅肉﹐沒有一點蔬菜水果﹐怎能不便秘﹖
況且﹐謊話講得多變會成真。人人都錯的時候﹐我們便會誤以為那是正確。那不是約定俗成。那是集體地賤賣優美的中國語文。
假如大家都認為那沒有問題﹐那麼﹐我們真的是來到了決定性的一刻﹐實在有需要選擇性地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假如你們以為這一句話通順無誤﹐假如你們以為這一句容易理解﹐我將無言。
Sunday, December 10, 2006
週末假期。
睡夢中﹐給老朋友的電話吵醒。沒有多談﹐因為我實在太累。掛了線後﹐望望床頭的鐘。原來經已十一時許。朋友倒是計算好了時間﹐只是未有料到我才在床上睡了五句鐘。前一天夜晚﹐聖誕派對關係﹐凌晨四時方回到住所。
不過﹐也著實很多謝這一個電話。要知道﹐在愛爾蘭的冬天﹐遲起床的代價﹐便是一整天要活在黑暗的世界裡面。拉開窗帘﹐看見外面難得陽光燦爛。我知道﹐更應該是起床的時候。縱然可能還有一些宿醉未醒。
我刷著牙﹐感到小腿依然有點疲乏。
這倒也難怪。昨天晚上﹐是走了太多的路。跟JOHN和BARRY分手後﹐我竟然聽從了FIONN的建議﹐從都柏林第四區走回家。我是住在第一區。那是六個火車站的路程。當然﹐想過乘的士。只是滿眼所見﹐沒有一輛的士沒有乘客﹐的士站也排滿了長長的人龍。始終﹐是凌晨三時。大家喝醉後都趕著回家。
其實﹐假如能夠截得了一架計程車﹐我們一行四人倒是應該到了HOWL ON THE MOON去。那是一間酒吧的士高。在MERRION SQUARE附近。一眾女生倒是在那兒等候我們。
派對結束後﹐我們是一起離開餐廳。那時候﹐應該是兩點多。LEEANN提議﹐要繼續狂歡下去。於是﹐便帶同所有女生﹐跳上一輛剛巧停泊在路旁的的士﹐直奔MERRION SQUARE。剩下我們四個男生﹐在凜冽的寒風下﹐等候下一架沒有載客的計程車。
我們一邊伸手截的士﹐一邊高舉一支又一支的紅酒和白酒對飲。可能是酒精關係﹐BARRY開始講起自己不愉快的遭遇。我們都竟然有點身同感受。談論間﹐我們開始互相熊抱起來。我感覺到BARRY的顫抖。我知道﹐那不是冰冷空氣裡的抖震。那是宣泄內心不滿後的餘震。我也聽到擁吻的聲音。FIONN笑著問﹐在這個天主教的國度裡﹐同性跟同性是否容許在街上擁吻﹖我當然不知道答案。不過﹐我發現﹐原來男人跟女生一樣﹐在非常不開心的情形下﹐也需要一個男人的大力擁抱。
把剩餘的酒都灌進了發愁的身體裡面後﹐BARRY竟然哼起了YESTERDAY的旋律。我們於是就在街上唱起歌來。他們都不大記得歌詞。倒是我還能夠把整首歌原原本本唱完。BARRY指著我說﹐D-! YOU ARE REALLY A MUSICAL LEGEND!
老實說﹐假如唱的是ARCTIC MONKEY,又或者是THE RED HOT CHILLI PEPPER,我一定跟不上。只是﹐你們唱的是披頭四的作品。他們方是恆久不滅的音樂傳奇。
花了一個小時﹐也未能找到一輛沒有載客的計程車﹐街上也越來越多人爭截的士。JOHN便撥了個電話予MARIA,告訴她我們決定將各自返家。
本來我跟FIONN同路。只是﹐因為他要趕著乘最後一班夜車﹐北上到愛爾蘭的邊境。我不想拖慢他的腳步。況且﹐臨分手的時候﹐BARRY又再多擁抱了我一次。他在我耳邊,喃喃地講著一大堆說話。我不是聽得很真。只聽到一些詞語﹐像最好朋友﹑亞洲﹑越南﹑香港﹑聖誕和回家。我著JOHN看緊BARRY。因為他似乎飲得很多。
獨自一人在冰冷的空氣裡慢走﹐我的醉意開始給清洗掉。我覺得有點精神。我想起了早前跟老朋友通過的一趟電話。知道我將有很多聖誕派對﹐他叮囑我小心酒後亂性。我笑著回答﹐聖誕派對的目的不就是為了要亂性麼﹖
為什麼都柏林夜晚的計程車這麼少﹖
刷完牙﹐洗過臉後﹐我翻翻月曆﹐記起了下星期四的第二個派對。
睡夢中﹐給老朋友的電話吵醒。沒有多談﹐因為我實在太累。掛了線後﹐望望床頭的鐘。原來經已十一時許。朋友倒是計算好了時間﹐只是未有料到我才在床上睡了五句鐘。前一天夜晚﹐聖誕派對關係﹐凌晨四時方回到住所。
不過﹐也著實很多謝這一個電話。要知道﹐在愛爾蘭的冬天﹐遲起床的代價﹐便是一整天要活在黑暗的世界裡面。拉開窗帘﹐看見外面難得陽光燦爛。我知道﹐更應該是起床的時候。縱然可能還有一些宿醉未醒。
我刷著牙﹐感到小腿依然有點疲乏。
這倒也難怪。昨天晚上﹐是走了太多的路。跟JOHN和BARRY分手後﹐我竟然聽從了FIONN的建議﹐從都柏林第四區走回家。我是住在第一區。那是六個火車站的路程。當然﹐想過乘的士。只是滿眼所見﹐沒有一輛的士沒有乘客﹐的士站也排滿了長長的人龍。始終﹐是凌晨三時。大家喝醉後都趕著回家。
其實﹐假如能夠截得了一架計程車﹐我們一行四人倒是應該到了HOWL ON THE MOON去。那是一間酒吧的士高。在MERRION SQUARE附近。一眾女生倒是在那兒等候我們。
派對結束後﹐我們是一起離開餐廳。那時候﹐應該是兩點多。LEEANN提議﹐要繼續狂歡下去。於是﹐便帶同所有女生﹐跳上一輛剛巧停泊在路旁的的士﹐直奔MERRION SQUARE。剩下我們四個男生﹐在凜冽的寒風下﹐等候下一架沒有載客的計程車。
我們一邊伸手截的士﹐一邊高舉一支又一支的紅酒和白酒對飲。可能是酒精關係﹐BARRY開始講起自己不愉快的遭遇。我們都竟然有點身同感受。談論間﹐我們開始互相熊抱起來。我感覺到BARRY的顫抖。我知道﹐那不是冰冷空氣裡的抖震。那是宣泄內心不滿後的餘震。我也聽到擁吻的聲音。FIONN笑著問﹐在這個天主教的國度裡﹐同性跟同性是否容許在街上擁吻﹖我當然不知道答案。不過﹐我發現﹐原來男人跟女生一樣﹐在非常不開心的情形下﹐也需要一個男人的大力擁抱。
把剩餘的酒都灌進了發愁的身體裡面後﹐BARRY竟然哼起了YESTERDAY的旋律。我們於是就在街上唱起歌來。他們都不大記得歌詞。倒是我還能夠把整首歌原原本本唱完。BARRY指著我說﹐D-! YOU ARE REALLY A MUSICAL LEGEND!
老實說﹐假如唱的是ARCTIC MONKEY,又或者是THE RED HOT CHILLI PEPPER,我一定跟不上。只是﹐你們唱的是披頭四的作品。他們方是恆久不滅的音樂傳奇。
花了一個小時﹐也未能找到一輛沒有載客的計程車﹐街上也越來越多人爭截的士。JOHN便撥了個電話予MARIA,告訴她我們決定將各自返家。
本來我跟FIONN同路。只是﹐因為他要趕著乘最後一班夜車﹐北上到愛爾蘭的邊境。我不想拖慢他的腳步。況且﹐臨分手的時候﹐BARRY又再多擁抱了我一次。他在我耳邊,喃喃地講著一大堆說話。我不是聽得很真。只聽到一些詞語﹐像最好朋友﹑亞洲﹑越南﹑香港﹑聖誕和回家。我著JOHN看緊BARRY。因為他似乎飲得很多。
獨自一人在冰冷的空氣裡慢走﹐我的醉意開始給清洗掉。我覺得有點精神。我想起了早前跟老朋友通過的一趟電話。知道我將有很多聖誕派對﹐他叮囑我小心酒後亂性。我笑著回答﹐聖誕派對的目的不就是為了要亂性麼﹖
為什麼都柏林夜晚的計程車這麼少﹖
刷完牙﹐洗過臉後﹐我翻翻月曆﹐記起了下星期四的第二個派對。
Saturday, December 09, 2006
曾經﹐我們是一個充滿自信的民族。自信得近乎自大。我們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我們叫自己住的地方做中原。中原以外﹐便是蠻夷。
其實﹐我們也不是自大得沒有理由。翻開歷史書﹐那時候﹐我們的GDP比所有蠻夷的總和還要多。有著這樣逢勃的經濟﹐我們自然吸引到不少外向的野蠻民族。始終﹐人人都想過豐衣足食的日子。假如自己的地方提供不了﹐到外面尋找確實是唯一的路。自古以來﹐我們總受到一定程度的外族威脅。遠古有匈奴﹑突厥﹐後來又有契丹﹑大金﹑蒙古和女真。他們都有一個特點﹕居住的地方都在我們週邊。要入侵﹐都是靠陸路。
可是﹐道光皇帝以後﹐要來富庶中原分一杯羹的﹐已經是另一個大陸的民族。他們科技發達﹐技術先進﹐有可以遠行的艦隊﹐有無堅不摧的武器。無疑﹐他們都是中國歷史上最厲害的外族。見識過洋人船堅炮利後﹐我們開始知道﹐原來自己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再不是世界的中心。我們發現﹐我們經常掛在口邊的什麼天朝大國﹐都不過是一場空話。一次又一次戰敗﹐一條又一條不平等條約後﹐我們開始承認自己有不如洋人的地方。洋務運動開始﹐就標誌著我們便從極自大的世界﹐走到了極自卑的世界。
在世界舞台上﹐我們對自己已經完全沒有一絲信心。
直至現在﹐或翻開報紙﹐或扭開電視﹐無論講的是什麼﹑討論的是什麼﹐我們都很容易聽到這樣的理據﹕
「不單只我們中國方有這個毛病﹐便是英美等西方列強﹐也同樣犯著這樣的錯。」
我很不明白。
我不明白﹐何解老是要用別人來做衡量的標準。我不明白﹐何解老是要用別國的過失﹐來為自己開脫。我們不時聽到我們的領導人說﹐要超英趕美﹐要做亞洲的曼克頓﹑東方的倫敦紐約。我們又聽過我們的領導人說﹐美國也有死刑﹐也會錯判無辜的人﹐所以我們把沒有犯罪的人槍斃﹐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不過﹐倒也奇怪﹐他們總不會說﹐英美的民主選舉很成功﹐我們應該爭相傚法。)
仿彿一切只要跟得上世界列強﹐便是犯錯也跟他們犯上同樣的錯﹐我們就是做到最好。
最近﹐有朋友對我早前的兩篇文章有些意見。其中﹐她說﹐寫不好母語的,不只是中國人。以英文為母語的人也會串錯字呢﹗
我相信﹐世界上寫不好母語的人﹐多如恆沙。我也知道﹐有英國大學生經常串錯字﹐他們的英文甚至比香港的還要差。不過﹐是否因為「以英文為母語的人也會串錯字」﹐我們便可以躲懶﹐我們便可以得過且過﹐只寫大眾都能讀懂的不太爛中文﹐不再堅持寫真正中文﹖
我想﹐便是因為世界上有太多寫不好母語的人﹐我們更加要堅持寫真正中文﹐放棄那些西化文字和英文直接翻譯。因為我們要做受世界景仰的民族。
從來﹐我以為﹐做任何事情﹐都不應只是AS GOOD AS,或者BETTER THAN。我們做事一定要做到THE BEST。我也相信﹐世界上都不應有任何標準讓我們跟從。因為我們就是世界的標準。
其實﹐我們也不是自大得沒有理由。翻開歷史書﹐那時候﹐我們的GDP比所有蠻夷的總和還要多。有著這樣逢勃的經濟﹐我們自然吸引到不少外向的野蠻民族。始終﹐人人都想過豐衣足食的日子。假如自己的地方提供不了﹐到外面尋找確實是唯一的路。自古以來﹐我們總受到一定程度的外族威脅。遠古有匈奴﹑突厥﹐後來又有契丹﹑大金﹑蒙古和女真。他們都有一個特點﹕居住的地方都在我們週邊。要入侵﹐都是靠陸路。
可是﹐道光皇帝以後﹐要來富庶中原分一杯羹的﹐已經是另一個大陸的民族。他們科技發達﹐技術先進﹐有可以遠行的艦隊﹐有無堅不摧的武器。無疑﹐他們都是中國歷史上最厲害的外族。見識過洋人船堅炮利後﹐我們開始知道﹐原來自己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再不是世界的中心。我們發現﹐我們經常掛在口邊的什麼天朝大國﹐都不過是一場空話。一次又一次戰敗﹐一條又一條不平等條約後﹐我們開始承認自己有不如洋人的地方。洋務運動開始﹐就標誌著我們便從極自大的世界﹐走到了極自卑的世界。
在世界舞台上﹐我們對自己已經完全沒有一絲信心。
直至現在﹐或翻開報紙﹐或扭開電視﹐無論講的是什麼﹑討論的是什麼﹐我們都很容易聽到這樣的理據﹕
「不單只我們中國方有這個毛病﹐便是英美等西方列強﹐也同樣犯著這樣的錯。」
我很不明白。
我不明白﹐何解老是要用別人來做衡量的標準。我不明白﹐何解老是要用別國的過失﹐來為自己開脫。我們不時聽到我們的領導人說﹐要超英趕美﹐要做亞洲的曼克頓﹑東方的倫敦紐約。我們又聽過我們的領導人說﹐美國也有死刑﹐也會錯判無辜的人﹐所以我們把沒有犯罪的人槍斃﹐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不過﹐倒也奇怪﹐他們總不會說﹐英美的民主選舉很成功﹐我們應該爭相傚法。)
仿彿一切只要跟得上世界列強﹐便是犯錯也跟他們犯上同樣的錯﹐我們就是做到最好。
最近﹐有朋友對我早前的兩篇文章有些意見。其中﹐她說﹐寫不好母語的,不只是中國人。以英文為母語的人也會串錯字呢﹗
我相信﹐世界上寫不好母語的人﹐多如恆沙。我也知道﹐有英國大學生經常串錯字﹐他們的英文甚至比香港的還要差。不過﹐是否因為「以英文為母語的人也會串錯字」﹐我們便可以躲懶﹐我們便可以得過且過﹐只寫大眾都能讀懂的不太爛中文﹐不再堅持寫真正中文﹖
我想﹐便是因為世界上有太多寫不好母語的人﹐我們更加要堅持寫真正中文﹐放棄那些西化文字和英文直接翻譯。因為我們要做受世界景仰的民族。
從來﹐我以為﹐做任何事情﹐都不應只是AS GOOD AS,或者BETTER THAN。我們做事一定要做到THE BEST。我也相信﹐世界上都不應有任何標準讓我們跟從。因為我們就是世界的標準。
Friday, December 08, 2006
我想﹐你不會不同意這樣的觀察﹕
連鎖超級市場和便利店壟斷了市場﹐小企業備受淘汰。在大財團猛烈的攻勢下﹐士多辦館一家又一家陷落。小孩子買東西說上「SEVEN」﹑到「百佳」﹐他們已不知道什麼是「士多」﹑什麼是「辦館」。這兩個名詞﹐早隨著殖民地時代漸漸消失了。
也許﹐法國人是病了。陶傑說,那是病在心理,壞在精神。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感覺﹕法國正在慢慢Downgrade成第三世界。巴黎滿街是搶匪,老鼠橫行,售貨員粗野。他們都不明白﹐為什麼唯美的法國人會淪落到這個樣子?
不過﹐便是多麼病﹐他們依然懂得保護自己的文化。他們不會讓大財團破壞社會一切的和諧秩序。
早前﹐為了好讓那些角落小店能夠跟那些連鎖超級市場和便利店競爭﹐法國總統希拉克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減稅和依舊不批准SUPERMARKET在星期天開門營業。他也不准許超級市場和便利店減價。
角落小店就是英文CORNER SHOP的直接翻譯。英國人都很悶蛋地把那些雜貨店﹐一律統稱叫CORNER SHOP。跟英國人很不同﹐法文裡面﹐那些店都有一個性感的名字﹐ÉPICERIE。其實﹐它跟CORNER SHOP不盡相同。因為ÉPICERIE是那麼的FRENCHNESS。ÉPICERIE這個名詞﹐早在中世紀已經出現。很明顯﹐那是法國人生活的傳統。巴黎最古老的百貨公司LE BON MARCHÉ,起家的時候便是一間ÉPICERIE。那是1838年。也不好跟香港的雜貨店混在一起。因為可有一些ÉPICERIE專售高價貨。還記得電影AMÉLIE嗎﹖像巴黎的L'ÉPICERIE。那兒有九十種果醬﹑七十種芥辣﹐供顧客選擇。
調查發現﹐法國人都依然很願意幫襯這些傳統小店。
跟以前香港的士多辦館一樣﹐ÉPICERIE都是有人情味的地方。老闆ABDELLAH FAITH對著從英國來的記者說﹐I SELL EVERYTHING FROM CONDOMS TO WHISKY WITH A WARM WELCOME FOR MY CUSTOMERS。
陶傑寫過﹕士多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士多店的老闆娘﹐可以記得每一個來買汽水和廁紙的小朋友﹐叫得出他們的乳名。士多流行的時代﹐汽水仍是瓶裝。買幾瓶汽水回家﹐瓶子要交按金﹐叫做「按樽」。按樽的錢﹐就是對士多老闆娘的一個小小承諾﹐答應她﹐我們不會永遠不再回頭。有一天﹐我們一定會穿著小木屐把空瓶子再提回來﹐把按樽費領回去。
只是﹐在大財主﹑大集團老闆﹐方是特首選舉的提名人和選民的情況下﹐要希望行政長官傚法希拉克﹐讓小企業可以跟連鎖超級市場和便利店競爭﹐實在是痴人說夢。於是﹐小生意便像城市裡的樹木一樣﹐越來越少發芽成長的空間。香港所有商場都變得一模一樣﹐都是售賣著相同的貨品。
話得說回來。早年經濟蕭條﹐政府不想打救﹐於是呼籲失業市民想辦法創業。究竟會有幾多人會盲目聽從政府的呼籲﹖也不知道這樣害死了幾多人﹖
要知道﹐在這樣的政治環境底下﹐香港根本不是適宜小本創業的地方。
那再不是一個尋夢理想地。
連鎖超級市場和便利店壟斷了市場﹐小企業備受淘汰。在大財團猛烈的攻勢下﹐士多辦館一家又一家陷落。小孩子買東西說上「SEVEN」﹑到「百佳」﹐他們已不知道什麼是「士多」﹑什麼是「辦館」。這兩個名詞﹐早隨著殖民地時代漸漸消失了。
也許﹐法國人是病了。陶傑說,那是病在心理,壞在精神。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感覺﹕法國正在慢慢Downgrade成第三世界。巴黎滿街是搶匪,老鼠橫行,售貨員粗野。他們都不明白﹐為什麼唯美的法國人會淪落到這個樣子?
不過﹐便是多麼病﹐他們依然懂得保護自己的文化。他們不會讓大財團破壞社會一切的和諧秩序。
早前﹐為了好讓那些角落小店能夠跟那些連鎖超級市場和便利店競爭﹐法國總統希拉克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減稅和依舊不批准SUPERMARKET在星期天開門營業。他也不准許超級市場和便利店減價。
角落小店就是英文CORNER SHOP的直接翻譯。英國人都很悶蛋地把那些雜貨店﹐一律統稱叫CORNER SHOP。跟英國人很不同﹐法文裡面﹐那些店都有一個性感的名字﹐ÉPICERIE。其實﹐它跟CORNER SHOP不盡相同。因為ÉPICERIE是那麼的FRENCHNESS。ÉPICERIE這個名詞﹐早在中世紀已經出現。很明顯﹐那是法國人生活的傳統。巴黎最古老的百貨公司LE BON MARCHÉ,起家的時候便是一間ÉPICERIE。那是1838年。也不好跟香港的雜貨店混在一起。因為可有一些ÉPICERIE專售高價貨。還記得電影AMÉLIE嗎﹖像巴黎的L'ÉPICERIE。那兒有九十種果醬﹑七十種芥辣﹐供顧客選擇。
調查發現﹐法國人都依然很願意幫襯這些傳統小店。
跟以前香港的士多辦館一樣﹐ÉPICERIE都是有人情味的地方。老闆ABDELLAH FAITH對著從英國來的記者說﹐I SELL EVERYTHING FROM CONDOMS TO WHISKY WITH A WARM WELCOME FOR MY CUSTOMERS。
陶傑寫過﹕士多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士多店的老闆娘﹐可以記得每一個來買汽水和廁紙的小朋友﹐叫得出他們的乳名。士多流行的時代﹐汽水仍是瓶裝。買幾瓶汽水回家﹐瓶子要交按金﹐叫做「按樽」。按樽的錢﹐就是對士多老闆娘的一個小小承諾﹐答應她﹐我們不會永遠不再回頭。有一天﹐我們一定會穿著小木屐把空瓶子再提回來﹐把按樽費領回去。
只是﹐在大財主﹑大集團老闆﹐方是特首選舉的提名人和選民的情況下﹐要希望行政長官傚法希拉克﹐讓小企業可以跟連鎖超級市場和便利店競爭﹐實在是痴人說夢。於是﹐小生意便像城市裡的樹木一樣﹐越來越少發芽成長的空間。香港所有商場都變得一模一樣﹐都是售賣著相同的貨品。
話得說回來。早年經濟蕭條﹐政府不想打救﹐於是呼籲失業市民想辦法創業。究竟會有幾多人會盲目聽從政府的呼籲﹖也不知道這樣害死了幾多人﹖
要知道﹐在這樣的政治環境底下﹐香港根本不是適宜小本創業的地方。
那再不是一個尋夢理想地。
Thursday, December 07, 2006
跟一般香港人一樣﹐從小﹐寫的字便非常醜。
為了遮掩醜怪異常的字體﹐不知道何時開始﹐我選擇了「行草」。當然﹐那不是正式的行草。那是只有我才能完全讀懂的書法。(不過﹐老實說﹐假如你不每個字看﹐只看整幅圖畫﹐其實那也算漂亮。)便是如此﹐我還是很喜歡跟人寫信。於是﹐經常惹來不少投訴。都說﹐讀不到我寫的字﹐不知道我在說什麼。早陣子﹐收到一位朋友的信。她寫道﹐你的字永遠都很草。每次讀你的信﹐總是要看幾回﹐才能猜曉你的意思。你的所說所想﹐真是少一點耐性﹑少花一點心機﹐也不會明白。
忽然﹐想起了另外一個她。
我想﹐也許直到現在﹐她還未能完全讀懂我寫給她的每一行意思﹐更遑論字裡行間的天使。不過﹐話得說回來。她能讀懂才怪﹗因為便是有閑情逸致﹐她也根本不可能還會翻開那一張張信箋﹐重讀我心底裡的每一句話語。因為﹐對於她來說﹐那些已經是一句又一句的廢話。我更相信的﹐是她早已把那些信箋如垃圾般拋掉。
我同意﹐我的所說所想﹐真是少一點耐性﹑少花一點心機﹐也不會明白。不過﹐那不是因為我那些潦草的字體。那是因為﹐我從來都不是一個直截了當的人。我總喜歡繞著圓心跑。有時候﹐那個半徑可以很短﹔有時候﹐那個半徑實在很長。不過﹐無論如何﹐總不會是零。
早前讀報﹐知道愛丁堡有一間小學決定﹐今年開始﹐要所有學生學寫墨水筆字。
有見太多VOWEL FREE的短訊﹐和文法完全不通的電郵﹐使到現今兒童﹐以至大學生和老師都寫不出一手讓人讀懂的字體﹐劉意思校長(B.LEWIS)相信﹐寫得一手好的墨水筆書法﹐會增強兒童自信心﹐使他們肯定自我。校長規定﹐所有教師都要懂得使用墨水筆﹐要寫得出端正的字體﹐因為他們都要教學生寫字。我不知道﹐有幾多人因此失業。
從前﹐墨水筆是每個學生必須學曉的東西。只是﹐原子筆出現後﹐社會有了很大的變化。大家都放棄了墨水筆。因為墨水筆很難使用﹐很容易把整頁紙弄污。又會漏墨水。一個不小心﹐整件衣服都可能要報銷。
不過﹐劉意思校長這個建議﹐得到了社會讚賞。尤其得到當權的認同。
眾所週知﹐貝理雅總是用墨水筆﹐把所有演講辭寫好一遍﹐才遞給秘書打進電腦裡面。他也很喜歡送人邱吉爾牌(CHURCHILL)的墨水筆。上年BOOKER PRIZE得主JOHN BANVILLE說﹐用墨水筆寫作的速度剛剛好。用電腦寫作﹐很多時候﹐都是電腦走得比自己的腦袋快。
倫敦時報說﹐THIS IS THE LAST-DITCH ATTEMPT TO SAVE THE NATION'S HANDWRITING。
的確如此。
來到都柏林後﹐我發覺﹐我的字體原來很漂亮。因為其他愛爾蘭的同事﹐無論男或女﹑年青或老成﹐他們的字竟然都像幼稚園學生的字。說來見笑﹐上司AOIFE便曾經稱讚過我的字體。
我的確很想寫好我的字。只是﹐假如我把我的字寫好﹐你豈不是不會把我的信讀完又讀﹖
為了遮掩醜怪異常的字體﹐不知道何時開始﹐我選擇了「行草」。當然﹐那不是正式的行草。那是只有我才能完全讀懂的書法。(不過﹐老實說﹐假如你不每個字看﹐只看整幅圖畫﹐其實那也算漂亮。)便是如此﹐我還是很喜歡跟人寫信。於是﹐經常惹來不少投訴。都說﹐讀不到我寫的字﹐不知道我在說什麼。早陣子﹐收到一位朋友的信。她寫道﹐你的字永遠都很草。每次讀你的信﹐總是要看幾回﹐才能猜曉你的意思。你的所說所想﹐真是少一點耐性﹑少花一點心機﹐也不會明白。
忽然﹐想起了另外一個她。
我想﹐也許直到現在﹐她還未能完全讀懂我寫給她的每一行意思﹐更遑論字裡行間的天使。不過﹐話得說回來。她能讀懂才怪﹗因為便是有閑情逸致﹐她也根本不可能還會翻開那一張張信箋﹐重讀我心底裡的每一句話語。因為﹐對於她來說﹐那些已經是一句又一句的廢話。我更相信的﹐是她早已把那些信箋如垃圾般拋掉。
我同意﹐我的所說所想﹐真是少一點耐性﹑少花一點心機﹐也不會明白。不過﹐那不是因為我那些潦草的字體。那是因為﹐我從來都不是一個直截了當的人。我總喜歡繞著圓心跑。有時候﹐那個半徑可以很短﹔有時候﹐那個半徑實在很長。不過﹐無論如何﹐總不會是零。
早前讀報﹐知道愛丁堡有一間小學決定﹐今年開始﹐要所有學生學寫墨水筆字。
有見太多VOWEL FREE的短訊﹐和文法完全不通的電郵﹐使到現今兒童﹐以至大學生和老師都寫不出一手讓人讀懂的字體﹐劉意思校長(B.LEWIS)相信﹐寫得一手好的墨水筆書法﹐會增強兒童自信心﹐使他們肯定自我。校長規定﹐所有教師都要懂得使用墨水筆﹐要寫得出端正的字體﹐因為他們都要教學生寫字。我不知道﹐有幾多人因此失業。
從前﹐墨水筆是每個學生必須學曉的東西。只是﹐原子筆出現後﹐社會有了很大的變化。大家都放棄了墨水筆。因為墨水筆很難使用﹐很容易把整頁紙弄污。又會漏墨水。一個不小心﹐整件衣服都可能要報銷。
不過﹐劉意思校長這個建議﹐得到了社會讚賞。尤其得到當權的認同。
眾所週知﹐貝理雅總是用墨水筆﹐把所有演講辭寫好一遍﹐才遞給秘書打進電腦裡面。他也很喜歡送人邱吉爾牌(CHURCHILL)的墨水筆。上年BOOKER PRIZE得主JOHN BANVILLE說﹐用墨水筆寫作的速度剛剛好。用電腦寫作﹐很多時候﹐都是電腦走得比自己的腦袋快。
倫敦時報說﹐THIS IS THE LAST-DITCH ATTEMPT TO SAVE THE NATION'S HANDWRITING。
的確如此。
來到都柏林後﹐我發覺﹐我的字體原來很漂亮。因為其他愛爾蘭的同事﹐無論男或女﹑年青或老成﹐他們的字竟然都像幼稚園學生的字。說來見笑﹐上司AOIFE便曾經稱讚過我的字體。
我的確很想寫好我的字。只是﹐假如我把我的字寫好﹐你豈不是不會把我的信讀完又讀﹖
Wednesday, December 06, 2006
離開香港後﹐我發覺﹐飲食上﹐我是一個哈日族。也許﹐是都柏林沒有一間合意的日本料理店。我最惦掛的竟然是魚生﹑壽司﹑天婦羅和鰻魚飯。
有天下班﹐在火車上碰見公司秘書DANIELLE。她對我說﹐從香港來到都柏林﹐最不適應的該是飲食罷﹖在愛爾蘭的首都﹐沒有一間特別出眾的食店。我回答道﹐其實也不然。亦有幾間很好的店子。老實說﹐中菜也很不錯。我提起了GRUEL、GALLAGHER、101 TOBALT和中興樓。
言談間﹐我們提到日本料理。我們都以為都柏林實在沒有讓人滿意的日本食物。DANIELLE說﹐以前在三藩市﹐她最喜歡的便是魚生和壽司。那裡實在有太多出色的日本廚師。在DUBLIN,所有日本食物都變了樣﹐變得很IRISH。
曾經根據雜誌THE DUBLINER的THE BEST OF DUBLIN 2006介紹﹐到了SOUTH GREAT GEORGE STREET上面的一間料理店YAMAMORI。跟妹妹試了一次後﹐都很同意文章的最後一句﹐THERE IS STILL PLENTY OF ROOMS IN THE MARKET FOR SOME COMPETITION,THOUGH。我知道﹐還有兩間店可以吃到日本菜。其中一間是迴轉壽司。只是﹐我想﹐也不用去試試了。無謂浪費金錢。
在愛爾蘭﹐假如想吃日本料理﹐還是過海到倫敦去罷。
記得有人說過﹐FOODWISEV,IF YOU CAN'T FIND SOMETHING TO SUIT YOU IN LONDON THEN THERE'S NO HOPE FOR YOU。英國是沒有出眾的菜式﹐也沒有一樣東西叫BRIT CUISINE。只是﹐你卻可以在倫敦吃到很多很好的不同國家菜式。
日本料理﹐當然是其中一樣。
最近﹐我便在英國首都找到兩間很好的日本料理。當然﹐你不能跟NADAMAN比較。只是家庭式經驗。我覺得好﹐因為都是日本人開的店﹐幫襯的都有日本人。而且都很便宜。要知道﹐日本人在外地很少吃本國的菜。他們以為﹐吃得入口的日本料理﹐都在日本。
一間在LECEISTER SQUARE。在唐人街附近。跟旺記同一條街。假如旺記在街頭﹐那間日本料理店便在街尾。裡面很像天才小廚師洋一的食店。供應的都是便當。也有魚生飯。最多人吃的是日本CURRY。份量都很多﹐卻不用十英鎊。
另一間則在GOLDERS GREEN。就在地鐵站對面。裡面全部都是日本人。吃的都是日本家庭式料理。那天下午﹐我們點了一個魚生定食和一個壽司定食。我想起了以前到日本旅行的回憶。更意外的是每人也不用六英鎊。
我知道﹐WAGAMAMA依然人頭湧湧﹐依然很受歡迎。
也許﹐大家都不當它是一間日本食店罷。的確﹐實在很難當它是一間日本食店。因為他們供應的都不是日本食物。
有天下班﹐在火車上碰見公司秘書DANIELLE。她對我說﹐從香港來到都柏林﹐最不適應的該是飲食罷﹖在愛爾蘭的首都﹐沒有一間特別出眾的食店。我回答道﹐其實也不然。亦有幾間很好的店子。老實說﹐中菜也很不錯。我提起了GRUEL、GALLAGHER、101 TOBALT和中興樓。
言談間﹐我們提到日本料理。我們都以為都柏林實在沒有讓人滿意的日本食物。DANIELLE說﹐以前在三藩市﹐她最喜歡的便是魚生和壽司。那裡實在有太多出色的日本廚師。在DUBLIN,所有日本食物都變了樣﹐變得很IRISH。
曾經根據雜誌THE DUBLINER的THE BEST OF DUBLIN 2006介紹﹐到了SOUTH GREAT GEORGE STREET上面的一間料理店YAMAMORI。跟妹妹試了一次後﹐都很同意文章的最後一句﹐THERE IS STILL PLENTY OF ROOMS IN THE MARKET FOR SOME COMPETITION,THOUGH。我知道﹐還有兩間店可以吃到日本菜。其中一間是迴轉壽司。只是﹐我想﹐也不用去試試了。無謂浪費金錢。
在愛爾蘭﹐假如想吃日本料理﹐還是過海到倫敦去罷。
記得有人說過﹐FOODWISEV,IF YOU CAN'T FIND SOMETHING TO SUIT YOU IN LONDON THEN THERE'S NO HOPE FOR YOU。英國是沒有出眾的菜式﹐也沒有一樣東西叫BRIT CUISINE。只是﹐你卻可以在倫敦吃到很多很好的不同國家菜式。
日本料理﹐當然是其中一樣。
最近﹐我便在英國首都找到兩間很好的日本料理。當然﹐你不能跟NADAMAN比較。只是家庭式經驗。我覺得好﹐因為都是日本人開的店﹐幫襯的都有日本人。而且都很便宜。要知道﹐日本人在外地很少吃本國的菜。他們以為﹐吃得入口的日本料理﹐都在日本。
一間在LECEISTER SQUARE。在唐人街附近。跟旺記同一條街。假如旺記在街頭﹐那間日本料理店便在街尾。裡面很像天才小廚師洋一的食店。供應的都是便當。也有魚生飯。最多人吃的是日本CURRY。份量都很多﹐卻不用十英鎊。
另一間則在GOLDERS GREEN。就在地鐵站對面。裡面全部都是日本人。吃的都是日本家庭式料理。那天下午﹐我們點了一個魚生定食和一個壽司定食。我想起了以前到日本旅行的回憶。更意外的是每人也不用六英鎊。
我知道﹐WAGAMAMA依然人頭湧湧﹐依然很受歡迎。
也許﹐大家都不當它是一間日本食店罷。的確﹐實在很難當它是一間日本食店。因為他們供應的都不是日本食物。
Tuesday, December 05, 2006
正如MARIA所說﹐沒有一次銀行假期﹐我是會留在愛爾蘭。
十月尾的銀行假期﹐我如常到了倫敦。
到EMIRATES STADIUM看完EVERTON的精彩演出後﹐我們到了LECEISTER SQUARE,打算看看還有沒有可能找到兩張MUSICAL的票子。我始終很想看LES MIS、PHANTOM和LION KING。(十一月後﹐還有ANDREW LLYOD WEBER的新作THE SOUND OF MUSIC。)不過﹐世界上面實在沒有太多幸運的事情。所有即晚的門票都已售罄。想過到電影院去﹐只是又不捨得花十三英鎊看一部電影。(在倫敦其他地方﹐如BAYSWATER,只需八英鎊。)於是﹐我們決定找一間餐廳吃頓好的。
妹妹說﹐也有一段時間沒有吃過印度菜。我們便到了一間印度餐廳。就在PICCADILLY CIRCUS附近。其實﹐整條街都是印度餐廳。我們只選了一間裝修最好。
餐廳很滿座。碰巧﹐有人用膳完畢﹐我們方能不用等候太久。
我們點了SAMOSA做前菜。也有烤雞和乳酪波菜矮瓜。我記得﹐以前在印度會吃過一款茄醬咖哩,只是記不起它的名字。翻閱餐牌良久﹐找到一款有茄醬的咖哩。不過﹐當菜來了後﹐又發覺好像有點不同。當然﹐少不得NAN。本來﹐還想點我喜歡的烤羊肉卷。只是才得兩個人﹐也不好點太多的菜﹐以免浪費。
本來﹐我便喜歡吃印度菜。加上可能是太久沒有吃過印度菜﹐的確覺得很好味。有侍應以為我們是日本人﹐跑了過來問我們HOW-CHI,A-LI-A-DO。我沒有矯正他。因為我常記得陶傑的一句話﹕在外地給人誤會是日本人﹐是三生修來的福份。
至少﹐我們依然很DECENT。並未給紅色大陸污染。
吃畢主菜﹐侍應便給我們遞上了甜點餐牌。望著那些甜品照片﹐我想起了GAY LORD的甜品和那些鮮紅得很假的甜醬。印度菜裡面﹐我最怕的就是那些DESSERT。我知道﹐LECEISTER SQUARE那兒有一間意大利雪糕店。我便提議吃意大利甜點。(GAY LORD是香港的一間印度餐廳。)
正要結賬的時候﹐妹妹的電話響了起來。是她公司裡面的一個朋友。在電話裡面﹐她跟她的朋友說,正在PICCADILLY CIRCUS的一間印度餐廳用膳。接著﹐她竟然為電話另一端的朋友描述了一次餐廳的裝修和間隔。突然﹐我聽到妹妹很大聲的說了一句「WHAT?」。然後﹐便很為難地拿開電話﹐向附近的一位侍應示意﹐要他走過來﹐就像有一個新的ORDER。
她把電話遞給了那位侍應﹐很尷尬地說﹐這兒是我的一位朋友。她說認得你﹐希望跟你談談。侍應當然很詫異﹐有點不知所措地拿取了妹妹的手提電話。我聽到他用我不懂得語言跟電話的另一頭交談。
我有點驚奇地聽著妹妹的解釋。
原來﹐這間餐廳是她朋友的家族生意。很久以前﹐當知道她很喜歡印度菜後﹐已經說要給妹妹一張VIP CARD。現在﹐她要父親的夥計給我們打個折頭。
世界上面不是有太多幸運的事情。不過﹐總可以碰到一些。
註﹕我喜歡的那種咖哩叫MALASA。
十月尾的銀行假期﹐我如常到了倫敦。
到EMIRATES STADIUM看完EVERTON的精彩演出後﹐我們到了LECEISTER SQUARE,打算看看還有沒有可能找到兩張MUSICAL的票子。我始終很想看LES MIS、PHANTOM和LION KING。(十一月後﹐還有ANDREW LLYOD WEBER的新作THE SOUND OF MUSIC。)不過﹐世界上面實在沒有太多幸運的事情。所有即晚的門票都已售罄。想過到電影院去﹐只是又不捨得花十三英鎊看一部電影。(在倫敦其他地方﹐如BAYSWATER,只需八英鎊。)於是﹐我們決定找一間餐廳吃頓好的。
妹妹說﹐也有一段時間沒有吃過印度菜。我們便到了一間印度餐廳。就在PICCADILLY CIRCUS附近。其實﹐整條街都是印度餐廳。我們只選了一間裝修最好。
餐廳很滿座。碰巧﹐有人用膳完畢﹐我們方能不用等候太久。
我們點了SAMOSA做前菜。也有烤雞和乳酪波菜矮瓜。我記得﹐以前在印度會吃過一款茄醬咖哩,只是記不起它的名字。翻閱餐牌良久﹐找到一款有茄醬的咖哩。不過﹐當菜來了後﹐又發覺好像有點不同。當然﹐少不得NAN。本來﹐還想點我喜歡的烤羊肉卷。只是才得兩個人﹐也不好點太多的菜﹐以免浪費。
本來﹐我便喜歡吃印度菜。加上可能是太久沒有吃過印度菜﹐的確覺得很好味。有侍應以為我們是日本人﹐跑了過來問我們HOW-CHI,A-LI-A-DO。我沒有矯正他。因為我常記得陶傑的一句話﹕在外地給人誤會是日本人﹐是三生修來的福份。
至少﹐我們依然很DECENT。並未給紅色大陸污染。
吃畢主菜﹐侍應便給我們遞上了甜點餐牌。望著那些甜品照片﹐我想起了GAY LORD的甜品和那些鮮紅得很假的甜醬。印度菜裡面﹐我最怕的就是那些DESSERT。我知道﹐LECEISTER SQUARE那兒有一間意大利雪糕店。我便提議吃意大利甜點。(GAY LORD是香港的一間印度餐廳。)
正要結賬的時候﹐妹妹的電話響了起來。是她公司裡面的一個朋友。在電話裡面﹐她跟她的朋友說,正在PICCADILLY CIRCUS的一間印度餐廳用膳。接著﹐她竟然為電話另一端的朋友描述了一次餐廳的裝修和間隔。突然﹐我聽到妹妹很大聲的說了一句「WHAT?」。然後﹐便很為難地拿開電話﹐向附近的一位侍應示意﹐要他走過來﹐就像有一個新的ORDER。
她把電話遞給了那位侍應﹐很尷尬地說﹐這兒是我的一位朋友。她說認得你﹐希望跟你談談。侍應當然很詫異﹐有點不知所措地拿取了妹妹的手提電話。我聽到他用我不懂得語言跟電話的另一頭交談。
我有點驚奇地聽著妹妹的解釋。
原來﹐這間餐廳是她朋友的家族生意。很久以前﹐當知道她很喜歡印度菜後﹐已經說要給妹妹一張VIP CARD。現在﹐她要父親的夥計給我們打個折頭。
世界上面不是有太多幸運的事情。不過﹐總可以碰到一些。
註﹕我喜歡的那種咖哩叫MALASA。
Monday, December 04, 2006
上星期五﹐可能因為知道以後的幾個星期將會有很多派對要參加﹐很多同事都在這個週末回家鄉去。於是﹐下班的時候﹐公司裡面實在沒有剩下太多人。
為趕上那些長途巴士﹐回家鄉的人都會提早一點離開。吃過中飯後﹐便會陸續聽見人家跟你講「有個好週末﹐我們星期一再見」之類的說話。公司對此﹐也很了解﹐不會有什麼投訴。因為大家都很明白我們是為了家庭生活才工作﹐都同意家庭生活方是生活最重要的部份﹐工作不過次要。所以﹐我們實在要主次分明﹐不能因為工作而忘記家庭﹐不能只為了腦海裡的將來而忽略了眼前的現在。
五點半離開公司的﹐便只有我跟ADRIAN、SUNDAR三個異鄉人。印度藉的SUNDAR也不能算做一個。因為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已搬來了這個國家。下班後﹐他都要趕回家﹐享受一下天倫樂。要到外面找節目的﹐其實只得我和ADRIAN兩個。
我提議吃愛爾蘭的傳統菜。
在都柏林﹐打正旗號供應愛爾蘭傳統食物的餐廳﹐我知道兩間。都在TEMPLE BAR。
GALLAGHER我是到過很多次了。那是一間專售BOXTY的餐廳。假如你讀過'TIS三部曲﹐對於BOXTY也不會陌生。那是用薯仔做的PANCAKE,再佩上一些肉來做餡料。故事說﹐以前愛爾蘭人生活很苦﹐都很窮﹐買不起雞蛋﹐可是卻又很想吃PANCAKE,於是便心生一計﹐用滿地都是的土豆﹐來代替雞蛋。那就是BOXTY的由來。經過百多年來的鑽研﹐GALLAGHER的BOXTY的確很美味。很多時候﹐店外都會有一條長龍在等候座位。
我想試新。於是﹐我們到了GALLAGHER斜對面的OLIVER ST JOHN GOGARTY。那是一間酒館餐廳。整年都有現場音樂表演。是其中一間經常都擠滿了人的店。從外面看﹐裡面永遠水泄不通。望著那人山人海﹐我們想﹐這不會是一間很爛的店。始終﹐群眾的選擇較少出錯。
店的樓下兩層﹐都是酒館。餐廳則在三樓。跟酒館比較﹐餐廳的確少很多人。至少﹐還有沒有坐人的座位。也許﹐要特別安排﹐我們在等了良久﹐侍應方領我們就座。的確是特別安排的座位﹐桌面很細﹐才僅過半米乘半米的大小。餐牌只得一面A4紙﹐油印了大大的字體﹐原來已經是所有STARTER、SOUP和MIANCOURSE。跟GALLAGHER更不同的﹐竟然沒有是日精選。餐牌底下﹐還印有一排字﹐寫道﹕每人最低消費十九塊半。
從來﹐我對設最低消費的餐廳﹐都很反感。我以為﹐你總不可能限制著顧客的選擇。為什麼我不能堂堂正正地只點一個沙拉和一杯清水﹖為什麼硬要我多點一樣菜﹖要不﹐就多要我五塊錢。幸好﹐這兒的定價也算「合理」。一個MAINCOURSE,最便宜的也要算你十九塊九毫半。不用為那最低消費操心和勞氣。
我們都點了一個CASSAROLE。ADRIAN要的是雞﹐我要的是浸過GUINNESS的牛肉。還有兩杯清水。
餐廳很有效率。才點了菜﹐轉個頭兩個CASSAROLE便已送到面前﹐可那兩杯清水還未來到。望著那兩個菜﹐我實在分不到什麼是IRISH STEW、什麼是CASSAROLE、什麼是湯。我膚淺地以為它們都是一樣的東西。ADRIAN笑著道﹐顏色有點不同﹐CASSAROLE的顏色比較深。我咬著那尚有微溫的牛肉﹐唯有苦笑點頭稱是。
當我們拒絕要甜點的時候﹐賬單便神速地來到桌上。餐廳的效率﹐又可再見一斑。剛好每人二十塊。我們都沒有給小賬。到快餐店吃預製好的食物﹐是不用給小賬的罷﹖
在TEMPLE BAR的鵝卵石上走著﹐望見了GALLAGHER店外的人龍。我們發現﹐到OLIVER ST JOHN GOGARTY的人﹐不過都是到樓下的酒館飲酒聽音樂罷了。
為趕上那些長途巴士﹐回家鄉的人都會提早一點離開。吃過中飯後﹐便會陸續聽見人家跟你講「有個好週末﹐我們星期一再見」之類的說話。公司對此﹐也很了解﹐不會有什麼投訴。因為大家都很明白我們是為了家庭生活才工作﹐都同意家庭生活方是生活最重要的部份﹐工作不過次要。所以﹐我們實在要主次分明﹐不能因為工作而忘記家庭﹐不能只為了腦海裡的將來而忽略了眼前的現在。
五點半離開公司的﹐便只有我跟ADRIAN、SUNDAR三個異鄉人。印度藉的SUNDAR也不能算做一個。因為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已搬來了這個國家。下班後﹐他都要趕回家﹐享受一下天倫樂。要到外面找節目的﹐其實只得我和ADRIAN兩個。
我提議吃愛爾蘭的傳統菜。
在都柏林﹐打正旗號供應愛爾蘭傳統食物的餐廳﹐我知道兩間。都在TEMPLE BAR。
GALLAGHER我是到過很多次了。那是一間專售BOXTY的餐廳。假如你讀過'TIS三部曲﹐對於BOXTY也不會陌生。那是用薯仔做的PANCAKE,再佩上一些肉來做餡料。故事說﹐以前愛爾蘭人生活很苦﹐都很窮﹐買不起雞蛋﹐可是卻又很想吃PANCAKE,於是便心生一計﹐用滿地都是的土豆﹐來代替雞蛋。那就是BOXTY的由來。經過百多年來的鑽研﹐GALLAGHER的BOXTY的確很美味。很多時候﹐店外都會有一條長龍在等候座位。
我想試新。於是﹐我們到了GALLAGHER斜對面的OLIVER ST JOHN GOGARTY。那是一間酒館餐廳。整年都有現場音樂表演。是其中一間經常都擠滿了人的店。從外面看﹐裡面永遠水泄不通。望著那人山人海﹐我們想﹐這不會是一間很爛的店。始終﹐群眾的選擇較少出錯。
店的樓下兩層﹐都是酒館。餐廳則在三樓。跟酒館比較﹐餐廳的確少很多人。至少﹐還有沒有坐人的座位。也許﹐要特別安排﹐我們在等了良久﹐侍應方領我們就座。的確是特別安排的座位﹐桌面很細﹐才僅過半米乘半米的大小。餐牌只得一面A4紙﹐油印了大大的字體﹐原來已經是所有STARTER、SOUP和MIANCOURSE。跟GALLAGHER更不同的﹐竟然沒有是日精選。餐牌底下﹐還印有一排字﹐寫道﹕每人最低消費十九塊半。
從來﹐我對設最低消費的餐廳﹐都很反感。我以為﹐你總不可能限制著顧客的選擇。為什麼我不能堂堂正正地只點一個沙拉和一杯清水﹖為什麼硬要我多點一樣菜﹖要不﹐就多要我五塊錢。幸好﹐這兒的定價也算「合理」。一個MAINCOURSE,最便宜的也要算你十九塊九毫半。不用為那最低消費操心和勞氣。
我們都點了一個CASSAROLE。ADRIAN要的是雞﹐我要的是浸過GUINNESS的牛肉。還有兩杯清水。
餐廳很有效率。才點了菜﹐轉個頭兩個CASSAROLE便已送到面前﹐可那兩杯清水還未來到。望著那兩個菜﹐我實在分不到什麼是IRISH STEW、什麼是CASSAROLE、什麼是湯。我膚淺地以為它們都是一樣的東西。ADRIAN笑著道﹐顏色有點不同﹐CASSAROLE的顏色比較深。我咬著那尚有微溫的牛肉﹐唯有苦笑點頭稱是。
當我們拒絕要甜點的時候﹐賬單便神速地來到桌上。餐廳的效率﹐又可再見一斑。剛好每人二十塊。我們都沒有給小賬。到快餐店吃預製好的食物﹐是不用給小賬的罷﹖
在TEMPLE BAR的鵝卵石上走著﹐望見了GALLAGHER店外的人龍。我們發現﹐到OLIVER ST JOHN GOGARTY的人﹐不過都是到樓下的酒館飲酒聽音樂罷了。
Sunday, December 03, 2006
未知是否因為聖誕節的關係﹐最近﹐愛爾蘭的郵政服務改善了很多。
上星期﹐收到的三份郵件。都竟然只用了四天,便從香港跑到來都柏林。是以前的一半時間。有時候﹐甚至需要兩個﹑以至三個星期﹐方能安全抵達。我記得﹐曾經等一位朋友寄給我的信﹐等了足足二十一個工作天。那時候﹐我們都以為是寄失了。不過﹐話得說回來﹐便是如何差勁﹐愛爾蘭的郵政服務總比墨西哥的好。前幾天﹐跟一位在那跳豆國家工作的朋友聊聊電話。原來﹐他才剛收到我在布達佩斯寄給他的那張明信片。天﹗我把明信片投進郵筒﹐是六十多個二十四小時前的事了。我怕﹐在香港的那些朋友﹐可能已經在家裡遺失了那張從東歐寄出的POSTCARD。
我對愛爾蘭的郵政服務改觀﹐除了是他們的速度加快了很多外﹐還有是他們寄給我的一張溫馨提示。當然﹐他們沒有像回歸後的香港那樣﹐明碼標明是溫馨提示。老實說﹐我也很討厭「溫馨提示」這一類字眼。我想﹐提示溫馨與否﹐那不是宣之於口的事。那應該是一種無形的感覺。
那其實是一張單張。上面有一個雪人﹐手裡執著一封郵件。還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THE MOMENT YOU SEND A CARD,IT'S CHRISTMAS.
DOWN THE ROAD OR AROUND THE WORLD,
WHEREVER YOU SEND YOUR CARDS
THEY'LL BE GREETED WITH JOY.
BECAUSE THE MOMENT YOU
SEND A CARD, IT'S CHRISTMAS.
EVERYONE LOVES TO GET A CARD XX
簡單的幾句﹐我知道截郵的時間快到。縱然他沒有清楚講明截郵的時間。正如陶傑教寫作時說過﹐不好當讀者是笨蛋。應該在文字裡面﹐多留些讓人想像的空間。跟國畫裡面的留白同理。況且﹐收到這封提示後﹐打算寄聖誕卡的人一定知道如何做法。實在用不著處處提醒。九七回歸後﹐香港的其中一個問題﹐便是政府老是當市民大笨蕉﹐什麼事情也得要管著。於是﹐市民也就養成依賴的習慣。當問題發生﹐他們自自然然歸咎政府﹐從不會以為那可能是自己的問題。在這樣的環境下﹐香港政府怎能不處於劣勢﹖
簡單的幾句﹐我知道截郵的時間快到。縱然我也實在不用他的提示。因為收到這個提示的同一天﹐我也收到了今年的第一封聖誕卡。還有一份聖誕禮物﹐是我喜歡的歌曲。
回家放低了那些重甸甸的文件後﹐在跟朋友到餐館吃飯前﹐我跑到了O'CONNELL STREET上面的郵政總局﹐買了兩排空郵郵票。那是都柏林裡面唯一一間七點鐘依然營業的郵局。
我發覺﹐裡面的燈火﹐今晚特別通明。只希望他們不會再令我失望。但願如此。
上星期﹐收到的三份郵件。都竟然只用了四天,便從香港跑到來都柏林。是以前的一半時間。有時候﹐甚至需要兩個﹑以至三個星期﹐方能安全抵達。我記得﹐曾經等一位朋友寄給我的信﹐等了足足二十一個工作天。那時候﹐我們都以為是寄失了。不過﹐話得說回來﹐便是如何差勁﹐愛爾蘭的郵政服務總比墨西哥的好。前幾天﹐跟一位在那跳豆國家工作的朋友聊聊電話。原來﹐他才剛收到我在布達佩斯寄給他的那張明信片。天﹗我把明信片投進郵筒﹐是六十多個二十四小時前的事了。我怕﹐在香港的那些朋友﹐可能已經在家裡遺失了那張從東歐寄出的POSTCARD。
我對愛爾蘭的郵政服務改觀﹐除了是他們的速度加快了很多外﹐還有是他們寄給我的一張溫馨提示。當然﹐他們沒有像回歸後的香港那樣﹐明碼標明是溫馨提示。老實說﹐我也很討厭「溫馨提示」這一類字眼。我想﹐提示溫馨與否﹐那不是宣之於口的事。那應該是一種無形的感覺。
那其實是一張單張。上面有一個雪人﹐手裡執著一封郵件。還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THE MOMENT YOU SEND A CARD,IT'S CHRISTMAS.
DOWN THE ROAD OR AROUND THE WORLD,
WHEREVER YOU SEND YOUR CARDS
THEY'LL BE GREETED WITH JOY.
BECAUSE THE MOMENT YOU
SEND A CARD, IT'S CHRISTMAS.
EVERYONE LOVES TO GET A CARD XX
簡單的幾句﹐我知道截郵的時間快到。縱然他沒有清楚講明截郵的時間。正如陶傑教寫作時說過﹐不好當讀者是笨蛋。應該在文字裡面﹐多留些讓人想像的空間。跟國畫裡面的留白同理。況且﹐收到這封提示後﹐打算寄聖誕卡的人一定知道如何做法。實在用不著處處提醒。九七回歸後﹐香港的其中一個問題﹐便是政府老是當市民大笨蕉﹐什麼事情也得要管著。於是﹐市民也就養成依賴的習慣。當問題發生﹐他們自自然然歸咎政府﹐從不會以為那可能是自己的問題。在這樣的環境下﹐香港政府怎能不處於劣勢﹖
簡單的幾句﹐我知道截郵的時間快到。縱然我也實在不用他的提示。因為收到這個提示的同一天﹐我也收到了今年的第一封聖誕卡。還有一份聖誕禮物﹐是我喜歡的歌曲。
回家放低了那些重甸甸的文件後﹐在跟朋友到餐館吃飯前﹐我跑到了O'CONNELL STREET上面的郵政總局﹐買了兩排空郵郵票。那是都柏林裡面唯一一間七點鐘依然營業的郵局。
我發覺﹐裡面的燈火﹐今晚特別通明。只希望他們不會再令我失望。但願如此。
Saturday, December 02, 2006
朋友﹐恭喜了。今天(1 DEC)是你們的大喜日子。
的確很希望能夠親身來恭賀你倆。只是﹐未有人贊助機票﹐唯有利用這個專欄﹐做一做BEST MAN的一個重要職責﹕GIVE A TOAST。
假如沒有記錯﹐你們兩個應該是在中大讀書的時候認識。從BACHELOR到MASTER。只是﹐結婚倒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結了婚後﹐男生會失去了個BACHELOR;女的卻又無端多了一個MASTER。所以說﹐讀書的確實在無用。
況且﹐朋友﹐從今天起﹐你是註定當不成一個哲學家。還要那個MPhil幹什﹖要知道﹐你比蘇格拉底幸運。
早知道你們很恩愛。以前在香港的時候﹐一起出來聚會﹐總不免見到你倆親嘴。因為實在很FREQUENT。很是羨煞旁人。
不過﹐結了婚﹐就是TWO BECOMES ONE。要兩個人黏在一起﹐不能單靠親嘴。便是學習法國的一套﹐也不是一個有用的辦法。印度作家TARUN TEJPAL便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方法。她說﹕LOVE IS NOT THE GREATEST GLUE BETWEEN TWO PEOPLE. SEX IS.
所以﹐朋友﹐從今天晚上開始﹐你應該每晚都要唱一唱﹕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Come over here and gently close the door
Lay your body soft and low beside me
And drop your petticoat upon the floor
我知道﹐這將會是你最喜歡的一首歌。
還記得年初﹐在地鐵裡面﹐我問過你的婚期﹖那時候﹐我正在為你寫一個很短很短的MUSICAL,希望能和其他THE MOSQUITOES的成員一起在你的婚讌上﹐送給你做新婚禮物。我想知道我還有幾多時間去完成。其實﹐早在我離開香港﹐遠走愛爾蘭的時候﹐我已經完成了MUSICAL裡面的詞。只是﹐我是一個自私的人。沒有我做導演﹐我不希望那個歌劇上演。況且﹐我想﹐唯有THE MOSQUITOES一起演出方有意思。希望你也同意。
談到THE MOSQUITOES﹐還記得我們第一次公開演出的那首歌嗎﹖
希望你們到六十四歲後﹐繼續恩愛﹐那些膠水依然強勁有力。
CONGRATULATIONS!
註﹕朋友﹐知道嗎﹖你實在是太遲提議了。幸好﹐早在我的愛華頓擊敗你的利物浦的前一天﹐我
便已把你在晚宴上看到的一切錄影好。
的確很希望能夠親身來恭賀你倆。只是﹐未有人贊助機票﹐唯有利用這個專欄﹐做一做BEST MAN的一個重要職責﹕GIVE A TOAST。
假如沒有記錯﹐你們兩個應該是在中大讀書的時候認識。從BACHELOR到MASTER。只是﹐結婚倒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結了婚後﹐男生會失去了個BACHELOR;女的卻又無端多了一個MASTER。所以說﹐讀書的確實在無用。
況且﹐朋友﹐從今天起﹐你是註定當不成一個哲學家。還要那個MPhil幹什﹖要知道﹐你比蘇格拉底幸運。
早知道你們很恩愛。以前在香港的時候﹐一起出來聚會﹐總不免見到你倆親嘴。因為實在很FREQUENT。很是羨煞旁人。
不過﹐結了婚﹐就是TWO BECOMES ONE。要兩個人黏在一起﹐不能單靠親嘴。便是學習法國的一套﹐也不是一個有用的辦法。印度作家TARUN TEJPAL便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方法。她說﹕LOVE IS NOT THE GREATEST GLUE BETWEEN TWO PEOPLE. SEX IS.
所以﹐朋友﹐從今天晚上開始﹐你應該每晚都要唱一唱﹕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Come over here and gently close the door
Lay your body soft and low beside me
And drop your petticoat upon the floor
我知道﹐這將會是你最喜歡的一首歌。
還記得年初﹐在地鐵裡面﹐我問過你的婚期﹖那時候﹐我正在為你寫一個很短很短的MUSICAL,希望能和其他THE MOSQUITOES的成員一起在你的婚讌上﹐送給你做新婚禮物。我想知道我還有幾多時間去完成。其實﹐早在我離開香港﹐遠走愛爾蘭的時候﹐我已經完成了MUSICAL裡面的詞。只是﹐我是一個自私的人。沒有我做導演﹐我不希望那個歌劇上演。況且﹐我想﹐唯有THE MOSQUITOES一起演出方有意思。希望你也同意。
談到THE MOSQUITOES﹐還記得我們第一次公開演出的那首歌嗎﹖
希望你們到六十四歲後﹐繼續恩愛﹐那些膠水依然強勁有力。
CONGRATULATIONS!
註﹕朋友﹐知道嗎﹖你實在是太遲提議了。幸好﹐早在我的愛華頓擊敗你的利物浦的前一天﹐我
便已把你在晚宴上看到的一切錄影好。
Friday, December 01, 2006
也許﹐正如陶傑所說﹐遇上一個Football-free的男人,比遇上一個Nonsmoking的君子更加稀罕。
早陣子﹐連續幾天都寫了一些關於足球的事情。於是﹐便有朋友寫信來問﹐為什麼男孩子總喜歡足球﹖他們走在一起﹐一定有一些時間在講波經。她說﹐她不明白球場上二十多個人追逐一個小足球的趣味。因為她自己就很怕有身體碰撞的球類活動。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都不知道答案。不過﹐我想﹐答案應該跟女孩子為什麼都喜歡棍網球(LACROSSE)和投球(NETBALL)相似罷。
生活在香港﹐或者﹐你會有點不明所以。因為那是一個很英國的答案。LACROSSE和NETBALL都是英國女中學生的熱門運動。(在香港﹐唯有讀香港大學﹐方能有機會打LACROSSE。投球則實在很不流行。印象中﹐KGV有一隊NETBALL隊。)
早前﹐英國有一間私立女校﹐為了使父親能夠多了解自己的女兒﹐便邀請了他們參觀學生的棍網球和投球練習。同時間﹐也安排了一連串的工作坊﹐讓父親弄清楚女兒的想法。因為越來越多調查發現﹐父親對女孩子的自我肯定影響重大。哈佛大學發現﹐多跟父親相處的孩子﹐IQ也比較高。
學校校長ALICE PHILIPS表示﹐對於很多父親來說﹐女兒都是一個大謎團。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的女兒對著自己﹐總是說生活過得很好﹐縱然明顯地她們在講相反詞。他們也不了解為何直髮器如此重要。當要跟女兒一起的時候﹐他們竟然會覺得很大壓力。他們會有點不知所措。
當然﹐那部份是因為父親跟女兒相處的時間實在太少。
工作坊開始前﹐學校讀了一些學生的願望給在場的父親聽。大家發現﹐女孩子都很希望多跟父親一起。她們希望父親能多留在家。她們不想只跟父親在CLARIDGE'S吃下午茶﹐或到MONSOON購物。她們也想跟父親在後花園嬉戲。校長說﹐與孩子相處﹐QUANTITY跟QUALITY實是同樣重要。
女孩子亦希望父親能夠多聽自己的想法。當跟母親意見不合的時候﹐她們期望父親能夠站在她們那一方。因為她們以為﹐父親應該會鼓勵她們多冒險嘗試。傳統上﹐母親都是安全至上。她們相信父親能夠給她們另外一種想法。
根據父親與女兒的網頁(www.dadsanddaughters.com)﹐我希望能夠對下面問題都答「是」。
1.我能夠講出女兒的三個最親密朋友。
2.我知道她在學校做什麼PROJECT。
3.我會為全家弄晚餐。
4.我知道女兒今天關心什麼事情。
5.跟女兒傾心事的時候﹐都是她講我聽。
我很細心讀著那個報導。因為我希望我是女兒的理想父親。(我是希望第一個孩子是女孩。)
早陣子﹐連續幾天都寫了一些關於足球的事情。於是﹐便有朋友寫信來問﹐為什麼男孩子總喜歡足球﹖他們走在一起﹐一定有一些時間在講波經。她說﹐她不明白球場上二十多個人追逐一個小足球的趣味。因為她自己就很怕有身體碰撞的球類活動。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都不知道答案。不過﹐我想﹐答案應該跟女孩子為什麼都喜歡棍網球(LACROSSE)和投球(NETBALL)相似罷。
生活在香港﹐或者﹐你會有點不明所以。因為那是一個很英國的答案。LACROSSE和NETBALL都是英國女中學生的熱門運動。(在香港﹐唯有讀香港大學﹐方能有機會打LACROSSE。投球則實在很不流行。印象中﹐KGV有一隊NETBALL隊。)
早前﹐英國有一間私立女校﹐為了使父親能夠多了解自己的女兒﹐便邀請了他們參觀學生的棍網球和投球練習。同時間﹐也安排了一連串的工作坊﹐讓父親弄清楚女兒的想法。因為越來越多調查發現﹐父親對女孩子的自我肯定影響重大。哈佛大學發現﹐多跟父親相處的孩子﹐IQ也比較高。
學校校長ALICE PHILIPS表示﹐對於很多父親來說﹐女兒都是一個大謎團。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的女兒對著自己﹐總是說生活過得很好﹐縱然明顯地她們在講相反詞。他們也不了解為何直髮器如此重要。當要跟女兒一起的時候﹐他們竟然會覺得很大壓力。他們會有點不知所措。
當然﹐那部份是因為父親跟女兒相處的時間實在太少。
工作坊開始前﹐學校讀了一些學生的願望給在場的父親聽。大家發現﹐女孩子都很希望多跟父親一起。她們希望父親能多留在家。她們不想只跟父親在CLARIDGE'S吃下午茶﹐或到MONSOON購物。她們也想跟父親在後花園嬉戲。校長說﹐與孩子相處﹐QUANTITY跟QUALITY實是同樣重要。
女孩子亦希望父親能夠多聽自己的想法。當跟母親意見不合的時候﹐她們期望父親能夠站在她們那一方。因為她們以為﹐父親應該會鼓勵她們多冒險嘗試。傳統上﹐母親都是安全至上。她們相信父親能夠給她們另外一種想法。
根據父親與女兒的網頁(www.dadsanddaughters.com)﹐我希望能夠對下面問題都答「是」。
1.我能夠講出女兒的三個最親密朋友。
2.我知道她在學校做什麼PROJECT。
3.我會為全家弄晚餐。
4.我知道女兒今天關心什麼事情。
5.跟女兒傾心事的時候﹐都是她講我聽。
我很細心讀著那個報導。因為我希望我是女兒的理想父親。(我是希望第一個孩子是女孩。)
Thursday, November 30, 2006
我對孩子的期望的確很高。
有可能是過高﹐甚至高得有點不設實際。這是一些朋友的意見。
我曾經跟KATE說過﹐假如我是美國人﹐我要我的孩子是美國總統。那是最起碼的要求。KATE是一個從美國來到愛爾蘭工作的同事。那天﹐無緣無故﹐在TEA TIME的時候﹐我們竟然談起了孩子。她聽到我的言論後﹐都笑得合不攏嘴。她以為﹐我在講一個很差的笑話。
也許﹐當時我的表情很FUNNY。不過﹐我絕不會用我的孩子來開玩笑。
不記得是什麼時候開始﹐我改變了想法。以前﹐我是很不希望生孩子。因為我既怕教不好﹐讓世界多一個壞人﹔我又怕世界已經太壞﹐無緣無故害苦了一個無辜的生命。我有一個朋友,直到現在﹐他依然很不讚同生孩子。他的想法﹐跟我以前的差不多。他說﹐只因一己一時的歡喜﹐便從零度的空間裡﹐給這個世界帶來一個生命﹐那是很自私的行為。
或者﹐我真的很自私。是年紀越大﹐越自私。
我想﹐我開始改變想法﹐是當我發覺有很多夢都不能逐一實現的時候。那時候﹐我的確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實現我的每一個夢想。
我希望他能夠精通六國語言﹕中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要懂得閱讀拉丁文﹔我希望他能夠寫得一手好書法﹔我希望他懂得寫詩和畫畫﹔我希望他能夠懂得兩種樂器﹔我希望他是學校辯論隊隊長﹐也是板球隊的成員﹔我希望他喜歡研究歷史。(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希望他在大學選修考古學。)
有著這樣的希望﹐我能夠讓他在香港讀書嗎﹖
我記得﹐這些都是我讀畢JEFFREY ARCHER的FIRST AMONG EQUAL後所希望的。ETON似乎已是他一定要入的學校。
早陣子﹐英國有一個私立學校調查。他們發現﹐近十年間﹐英國的BROADING SCHOOLS一年的學費已從一萬多英鎊﹐漲至二萬多英鎊。調查說﹐...an engineer would have to cough up 28 per cent of his or her earnings to cover the fees for a private prep or secondary school...only a handful of workers, such as judges and chief executives, earn enough to cover the cost of school fees from their paypacket comfortably。他們建議﹐假如要讓孩子入讀這些BROADING SCHOOLS,家長便應從今天起以後的十一年﹐每個月儲五百英鎊。
望著這些學費﹐怎能不在孩子還未出世的時候﹐便開始儲錢﹖或者﹐更應該在未結婚前﹐便要預留一些錢做這個學費。況且﹐根據JEFFREY ARCHER所說﹐要入讀ETON,差不多要在孩子還在母親的肚子裡面的時候﹐便給他報名。
這裡﹐我說的是「他」。其實﹐如果是「她」﹐也許更好。不過﹐她不能夠做一個ETONIAN。
註﹕以下是一些有名的ENGLISH BROADING SCHOOLS零五年的收費﹐
CHARTERHOUSE:23,955英鎊﹔ETON:23,688英鎊﹔HARROW:23,625英鎊﹔WINCHESTER:23,500英鎊﹔RUGBY:22,500英鎊﹔WESTMINSTER:21,948英鎊﹔ST PAUL'S:15,000英鎊。
有可能是過高﹐甚至高得有點不設實際。這是一些朋友的意見。
我曾經跟KATE說過﹐假如我是美國人﹐我要我的孩子是美國總統。那是最起碼的要求。KATE是一個從美國來到愛爾蘭工作的同事。那天﹐無緣無故﹐在TEA TIME的時候﹐我們竟然談起了孩子。她聽到我的言論後﹐都笑得合不攏嘴。她以為﹐我在講一個很差的笑話。
也許﹐當時我的表情很FUNNY。不過﹐我絕不會用我的孩子來開玩笑。
不記得是什麼時候開始﹐我改變了想法。以前﹐我是很不希望生孩子。因為我既怕教不好﹐讓世界多一個壞人﹔我又怕世界已經太壞﹐無緣無故害苦了一個無辜的生命。我有一個朋友,直到現在﹐他依然很不讚同生孩子。他的想法﹐跟我以前的差不多。他說﹐只因一己一時的歡喜﹐便從零度的空間裡﹐給這個世界帶來一個生命﹐那是很自私的行為。
或者﹐我真的很自私。是年紀越大﹐越自私。
我想﹐我開始改變想法﹐是當我發覺有很多夢都不能逐一實現的時候。那時候﹐我的確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實現我的每一個夢想。
我希望他能夠精通六國語言﹕中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要懂得閱讀拉丁文﹔我希望他能夠寫得一手好書法﹔我希望他懂得寫詩和畫畫﹔我希望他能夠懂得兩種樂器﹔我希望他是學校辯論隊隊長﹐也是板球隊的成員﹔我希望他喜歡研究歷史。(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希望他在大學選修考古學。)
有著這樣的希望﹐我能夠讓他在香港讀書嗎﹖
我記得﹐這些都是我讀畢JEFFREY ARCHER的FIRST AMONG EQUAL後所希望的。ETON似乎已是他一定要入的學校。
早陣子﹐英國有一個私立學校調查。他們發現﹐近十年間﹐英國的BROADING SCHOOLS一年的學費已從一萬多英鎊﹐漲至二萬多英鎊。調查說﹐...an engineer would have to cough up 28 per cent of his or her earnings to cover the fees for a private prep or secondary school...only a handful of workers, such as judges and chief executives, earn enough to cover the cost of school fees from their paypacket comfortably。他們建議﹐假如要讓孩子入讀這些BROADING SCHOOLS,家長便應從今天起以後的十一年﹐每個月儲五百英鎊。
望著這些學費﹐怎能不在孩子還未出世的時候﹐便開始儲錢﹖或者﹐更應該在未結婚前﹐便要預留一些錢做這個學費。況且﹐根據JEFFREY ARCHER所說﹐要入讀ETON,差不多要在孩子還在母親的肚子裡面的時候﹐便給他報名。
這裡﹐我說的是「他」。其實﹐如果是「她」﹐也許更好。不過﹐她不能夠做一個ETONIAN。
註﹕以下是一些有名的ENGLISH BROADING SCHOOLS零五年的收費﹐
CHARTERHOUSE:23,955英鎊﹔ETON:23,688英鎊﹔HARROW:23,625英鎊﹔WINCHESTER:23,500英鎊﹔RUGBY:22,500英鎊﹔WESTMINSTER:21,948英鎊﹔ST PAUL'S:15,000英鎊。
Wednesday, November 29, 2006
今天晚上﹐不知怎地﹐總是睡不著。輾轉反側﹐依然未能入眠。倒是多次弄醒了枕邊人。
她矇矓地說﹐怎麼老是不能好好入夢﹖市面一片平靜。也沒有什麼大事發生。大家也都在準備聖誕。還有什麼事情想不通﹖一切都盡在你掌握中了罷﹖
正躊躇如何敷衍回答﹐卻又再聽到她夢中的呼吸聲。我坐起了身子﹐望出窗外﹐看見了那皎潔的明月。外面的確風平浪靜﹐魚池的錦鯉也再沒有悽慘地叫起來。為何還是不能入睡﹖我實在已沒有再想前兩天晚上的事情。那實在有點可怕。
前幾晚﹐睡到半響﹐便聽到外面那幾尾心愛的魚兒﹐很悲淒地輕哼著一些小調。兩年前﹐我給委任做清潔大隊長的時候﹐它們也如此叫過。跟兩年前一樣﹐第二朝起來﹐全個家亦好像只有我聽到那些錦鯉的叫聲。我探聽過園丁花王的口風﹐他們似乎也未發覺有何異樣。我依舊不敢跟薇講。我不想她擔心。況且﹐她從來就不贊成搬到這兒住。對於老董的話﹐她倒很相信。都說這裡的風水不好。只是﹐花了這麼多錢裝修﹐無論如何都要住下去﹐不能讓那些人有什麼藉口指責我。我根本不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
望著那月兒的倒影﹐我竟然想起了以前哈佛的歲月。我想起了那一課管理學。我想起了「彼得定律」。那是指表現出色的僱員,終有一天會被擢升至不能勝任的崗位,以致失敗收場。例如公司的皇牌推銷員,由於工作表現優異,漸漸晉升為管理層,但擅長銷售並不代表也精於領導或管理,又例如「數佬」不一定可以成為出色的CEO。根據彼得定律,升遷決定通常只是基於僱員目前工作的表現,而忽略其勝任下一個崗位的潛質,結果使那些優秀僱員都落得黯淡下場。
想想算算﹐我見已經是早上五點。於是﹐便決定放棄在床上掙扎入眠﹐提早工作。
我放輕了腳步﹐走到書房去。
翻翻報紙﹐我又看到了那個廣告。是一間叫做GLOBAL LEADERSHIP FORUM公司的廣告。地址在倫敦。
我知道這間公司。他的創辦人是F.W.de Klerk。他是前南非總統。公司開業了三年﹐專向非洲﹑東歐﹑亞洲﹐以至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統治者﹑領導人﹐提供MENTORSHIP。他們說﹐IN THE LONELY CLUBOF RULERS, KINGS AND PRESIDENTS, FEW PROVE TO BE TRUER FRIENDS THAN THOSE WHO HAVE DONE THE JOB BEFORE。因為有很多大財團捐款﹐所以他們的收費實在很廉宜。只要一個非執行董事開董事局會議的價錢﹐他們便會在22個成員裡面﹐挑選一個最適合你的﹐跟你傾談你的問題﹐希望能幫你解決那困擾著你的難題。那22個成員都是退休的國家領袖﹐所以都有豐富的國際經驗。不過﹐很多時候﹐前非洲國家的領袖﹐都會協助非洲的國家﹔亞洲的幫回亞洲。因為那才是他們最熟悉的地方和環境。
我知道他們的保密工作都做得很好。除非你自己跟人說你到外尋找幫忙﹐否則絕對不會有人知道你曾經付錢給這一間公司﹐要求MENTORSHIP。
剛接手老董留下來的這個爛攤子時﹐確實曾經想過找他們幫手。因為我只是一個皇牌推銷員﹐並不精於領導或管理。只是﹐我實在很怕北大人的間諜網。假如這件事傳到了他們的耳裡﹐我知道﹐我也不用期待零七年後依然可以得到他們的祝福。
到了這個時候﹐也更不用找他們幫手了。因為我已猜到他們會派誰做我的MENTOR。
想不到那個臭婆娘不跟我爭坐第一把交椅﹐卻跑了去做GLOBAL LEADERSHIP FORUM的成員。希望藉此﹐影響我們週圍的地方和國家。
想到她那四萬般的笑容﹐我實在有點作嘔。
她矇矓地說﹐怎麼老是不能好好入夢﹖市面一片平靜。也沒有什麼大事發生。大家也都在準備聖誕。還有什麼事情想不通﹖一切都盡在你掌握中了罷﹖
正躊躇如何敷衍回答﹐卻又再聽到她夢中的呼吸聲。我坐起了身子﹐望出窗外﹐看見了那皎潔的明月。外面的確風平浪靜﹐魚池的錦鯉也再沒有悽慘地叫起來。為何還是不能入睡﹖我實在已沒有再想前兩天晚上的事情。那實在有點可怕。
前幾晚﹐睡到半響﹐便聽到外面那幾尾心愛的魚兒﹐很悲淒地輕哼著一些小調。兩年前﹐我給委任做清潔大隊長的時候﹐它們也如此叫過。跟兩年前一樣﹐第二朝起來﹐全個家亦好像只有我聽到那些錦鯉的叫聲。我探聽過園丁花王的口風﹐他們似乎也未發覺有何異樣。我依舊不敢跟薇講。我不想她擔心。況且﹐她從來就不贊成搬到這兒住。對於老董的話﹐她倒很相信。都說這裡的風水不好。只是﹐花了這麼多錢裝修﹐無論如何都要住下去﹐不能讓那些人有什麼藉口指責我。我根本不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
望著那月兒的倒影﹐我竟然想起了以前哈佛的歲月。我想起了那一課管理學。我想起了「彼得定律」。那是指表現出色的僱員,終有一天會被擢升至不能勝任的崗位,以致失敗收場。例如公司的皇牌推銷員,由於工作表現優異,漸漸晉升為管理層,但擅長銷售並不代表也精於領導或管理,又例如「數佬」不一定可以成為出色的CEO。根據彼得定律,升遷決定通常只是基於僱員目前工作的表現,而忽略其勝任下一個崗位的潛質,結果使那些優秀僱員都落得黯淡下場。
想想算算﹐我見已經是早上五點。於是﹐便決定放棄在床上掙扎入眠﹐提早工作。
我放輕了腳步﹐走到書房去。
翻翻報紙﹐我又看到了那個廣告。是一間叫做GLOBAL LEADERSHIP FORUM公司的廣告。地址在倫敦。
我知道這間公司。他的創辦人是F.W.de Klerk。他是前南非總統。公司開業了三年﹐專向非洲﹑東歐﹑亞洲﹐以至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統治者﹑領導人﹐提供MENTORSHIP。他們說﹐IN THE LONELY CLUBOF RULERS, KINGS AND PRESIDENTS, FEW PROVE TO BE TRUER FRIENDS THAN THOSE WHO HAVE DONE THE JOB BEFORE。因為有很多大財團捐款﹐所以他們的收費實在很廉宜。只要一個非執行董事開董事局會議的價錢﹐他們便會在22個成員裡面﹐挑選一個最適合你的﹐跟你傾談你的問題﹐希望能幫你解決那困擾著你的難題。那22個成員都是退休的國家領袖﹐所以都有豐富的國際經驗。不過﹐很多時候﹐前非洲國家的領袖﹐都會協助非洲的國家﹔亞洲的幫回亞洲。因為那才是他們最熟悉的地方和環境。
我知道他們的保密工作都做得很好。除非你自己跟人說你到外尋找幫忙﹐否則絕對不會有人知道你曾經付錢給這一間公司﹐要求MENTORSHIP。
剛接手老董留下來的這個爛攤子時﹐確實曾經想過找他們幫手。因為我只是一個皇牌推銷員﹐並不精於領導或管理。只是﹐我實在很怕北大人的間諜網。假如這件事傳到了他們的耳裡﹐我知道﹐我也不用期待零七年後依然可以得到他們的祝福。
到了這個時候﹐也更不用找他們幫手了。因為我已猜到他們會派誰做我的MENTOR。
想不到那個臭婆娘不跟我爭坐第一把交椅﹐卻跑了去做GLOBAL LEADERSHIP FORUM的成員。希望藉此﹐影響我們週圍的地方和國家。
想到她那四萬般的笑容﹐我實在有點作嘔。
Tuesday, November 28, 2006
最近﹐我又要到附近華人開的店買米。是在都柏林生活後的第四次。
數數手指﹐才剛過了半年﹐原來我在愛爾蘭已吃掉了三十公斤米。我想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罷﹖香港一個四人家庭平均要花多少時間才能耗掉一袋八公斤的米呢﹖我心裡完全沒有大概。因為這從來不是我關心的事情。因為從來我都不需要關心。
我知道﹐我是一個幸福的人。
買米當然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為住所附近便有幾間中國人開的小型超級市場﹐所以捧著一袋十公斤的米回家﹐也不是很辛苦。就是最怕遇著電梯壞了。要知道﹐我可是住在頂層。抱著那袋沉甸甸的麻布袋爬四層樓梯﹐實在不是講笑。也許﹐可以當做一個很好的運動罷。我這幢樓的電梯﹐每個月總會很準時地壞兩次。都是在週末的時候。可週末便是我都超級市場買食物﹑為住所添置用品的時候。
早陣子﹐我亦買了一部吸塵機。因為我發覺﹐掃地實在既幾花時間﹐又沒有實際效用。掃完左邊﹐然後到右邊﹐豈料﹐才掃完右邊﹐左邊已又有一小堆灰塵。都是在掃右邊的時候﹐因為空氣流動﹐飄游過去的。於是﹐掃完左﹐又掃右﹐再掃左﹐再掃右﹐完全是一個不能停止的的工作。除非﹐你容許那些微塵黏在地板上面。況且﹐也很不健康。掃地的時候﹐塵土飛揚﹐我們卻不斷地吸。
望著那些灰塵﹐心裡面便有一個疑問﹕究竟它們從何而來﹖
每天早上七時五十分離家上班﹐到晚上六時半方回到家。期間﹐所有窗戶都是緊閉。此外﹐現在是冬天﹐便是留在家裡面﹐我也沒有開窗。實在很奇怪為何住所裡面竟然這樣多塵。
為了應付那些不知從哪兒來的灰塵﹐我決定到ARGOS買部吸塵機。希望能有效地減少家裡塵堆的數目。
翻閱ARGOS CATALOGUE的時候﹐我也找到一些廚房用具。早前﹐在一個電視烹飪的節目裡面﹐主持人便是用那個PROCESSOR完成一個西蘭花忌廉湯。我仍然記得那個湯的做法。因為實在很容易。最重要的﹐還是那個手提電器。因為要用它來把所有湯料攪成茸。看著熒光屏﹐我知道﹐那將會是我最先學會煮的一個湯。
不想一次過花上太多的錢。所以只是買了那個吸塵機。
還是留待下個月才把那個PROCESSOR帶回家。在外面冰冷的天氣下﹐在廚房弄弄點吃﹐會是一個很好的消遣方法。
在電影LITTLE CHILDREN裡面﹐KATE WINSLET愛上了一個住家男人。早前﹐倫敦時報副刊便做了一個專題﹐研究何解STAY-AT-HOME DADS是新潮的SEX SYMBOLS。
我想﹐要成為最POP的性感標誌﹐我算是走近了一步。正如﹐一個朋友所講﹐我是有點變了。縱然還有一段很長很長的路要走。長得以環繞地球一周做量度單位。
數數手指﹐才剛過了半年﹐原來我在愛爾蘭已吃掉了三十公斤米。我想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罷﹖香港一個四人家庭平均要花多少時間才能耗掉一袋八公斤的米呢﹖我心裡完全沒有大概。因為這從來不是我關心的事情。因為從來我都不需要關心。
我知道﹐我是一個幸福的人。
買米當然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為住所附近便有幾間中國人開的小型超級市場﹐所以捧著一袋十公斤的米回家﹐也不是很辛苦。就是最怕遇著電梯壞了。要知道﹐我可是住在頂層。抱著那袋沉甸甸的麻布袋爬四層樓梯﹐實在不是講笑。也許﹐可以當做一個很好的運動罷。我這幢樓的電梯﹐每個月總會很準時地壞兩次。都是在週末的時候。可週末便是我都超級市場買食物﹑為住所添置用品的時候。
早陣子﹐我亦買了一部吸塵機。因為我發覺﹐掃地實在既幾花時間﹐又沒有實際效用。掃完左邊﹐然後到右邊﹐豈料﹐才掃完右邊﹐左邊已又有一小堆灰塵。都是在掃右邊的時候﹐因為空氣流動﹐飄游過去的。於是﹐掃完左﹐又掃右﹐再掃左﹐再掃右﹐完全是一個不能停止的的工作。除非﹐你容許那些微塵黏在地板上面。況且﹐也很不健康。掃地的時候﹐塵土飛揚﹐我們卻不斷地吸。
望著那些灰塵﹐心裡面便有一個疑問﹕究竟它們從何而來﹖
每天早上七時五十分離家上班﹐到晚上六時半方回到家。期間﹐所有窗戶都是緊閉。此外﹐現在是冬天﹐便是留在家裡面﹐我也沒有開窗。實在很奇怪為何住所裡面竟然這樣多塵。
為了應付那些不知從哪兒來的灰塵﹐我決定到ARGOS買部吸塵機。希望能有效地減少家裡塵堆的數目。
翻閱ARGOS CATALOGUE的時候﹐我也找到一些廚房用具。早前﹐在一個電視烹飪的節目裡面﹐主持人便是用那個PROCESSOR完成一個西蘭花忌廉湯。我仍然記得那個湯的做法。因為實在很容易。最重要的﹐還是那個手提電器。因為要用它來把所有湯料攪成茸。看著熒光屏﹐我知道﹐那將會是我最先學會煮的一個湯。
不想一次過花上太多的錢。所以只是買了那個吸塵機。
還是留待下個月才把那個PROCESSOR帶回家。在外面冰冷的天氣下﹐在廚房弄弄點吃﹐會是一個很好的消遣方法。
在電影LITTLE CHILDREN裡面﹐KATE WINSLET愛上了一個住家男人。早前﹐倫敦時報副刊便做了一個專題﹐研究何解STAY-AT-HOME DADS是新潮的SEX SYMBOLS。
我想﹐要成為最POP的性感標誌﹐我算是走近了一步。正如﹐一個朋友所講﹐我是有點變了。縱然還有一段很長很長的路要走。長得以環繞地球一周做量度單位。
Monday, November 27, 2006
我常以為﹐香港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假如不能寫好中文﹐那的確是對自己最大的侮辱。
可是﹐歷史關係﹐我們的中文都受了英文影響。很多時候﹐它都是英文的直接翻譯。加上科技突飛猛進﹐隨著外來潮流文化到來﹐我們的語文更受了其他外語影響。當中﹐以日文為甚。街上走走﹐不難讀到那些冒充中文的日文漢字。(同時間﹐我們的英文卻又受著中文影響。那叫做CHINGLISH。於是﹐在這個特殊的地域裡﹐我們寫的﹑講的﹐都是語文混合物。)
最近﹐到了那個普選工程路線的網頁瀏覽﹐這個說法更加得到肯定。
那是一群中年香港工程師參加選舉委員會委員的競選網頁。網頁裡面不是一些從英文原文粗暴搬過來的中文﹐便是一些很含糊﹑又很纍贅的文字。而且﹐邏輯和事實﹐都有點問題。我想﹐也許他們的思想亦很混亂。不過﹐在這樣無里頭的選舉制度下﹐除了那些欽點人和給人欽點的人外﹐有誰不感到不混亂﹖
他們說﹐「我們是來自不同崗位,包括私營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工程師。我們並非共同屬於任何一個政治團體,但我們擁有共同的理念:香港人理應享有更民主的體制和更有效的管治」。
他們又說﹐「在特區過去十年的特首選舉中,工程界的候選人少有以爭取普選為目標,以致工程師從來未有機會作出真正的選擇。我們參與作為選舉委員會的候選人,目的在於提供一個促成轉變的契機,為香港的政冶發展打破悶局,重新燃點希望」。
我想﹐這樣的文字只比「總書記指出,加強思想理論建設,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在實踐中繼續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而神聖的使命。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緊密結合新世紀新階段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提出以人為本,實現科學發展、建構社會主義和諧、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新型國家,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等重大戰略思想和戰略任務,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稍稍優勝。始終﹐香港才回歸紅色中國不夠十年﹐大家還未給污染到那個無可救藥的地步。
不過﹐便是因為我們遭污染的程度依然有限﹐我們更要把握時間﹐好好加強基本功﹐以抵抗那些紅色中文南下的猛烈攻擊。
我同意﹐多聽多寫多講﹐語文自然好。可是﹐假如多聽多寫多講的都只是比那些紅色中文稍稍優勝的不太爛中文﹐我們又怎能夠期望自己對紅色中文有免疫力﹖奈何﹐在我們週圍,都鮮有一些真正的中文文字。也不用太有觀察力﹐你也總能發覺﹐在我們週邊﹐常常充斥著這樣的句子﹕「作為香港的特首﹐我對於這件人神共憤的惡行﹐實在感到痛心疾首」﹑「星期五開會後﹐銀行公會決定作出加息行動」﹑「百貨公司決定作出大割引」﹑「使用中」等。更甚的是﹐這樣的文字竟然也出現在我們的報章上面。
老實說﹐在香港﹐能夠寫真正中文的人已經不多。除了金庸﹑董橋和陶傑外﹐我想不到另外一個。(也許﹐林行止先生會是第四個。只是﹐我總常在他的文章裡找到一些西化的句子。)不過﹐這倒也方便我們去加強自己的中文基本功。況且﹐董橋和陶傑都有在《蘋果日報》寫專欄。每天一份《蘋果》﹐的確可以加強自己的免疫能力。
對於普選工程路線的那些文字﹐我可大膽地有以下粗略改動(見笑)﹕
「我們都是工程師﹐來自不同崗位﹐包括私營企業與政府部門。我們不屬於任何政治團體。我們相信﹐香港應有更民主的體制和更有效的管治。在過去選舉委員會競選中﹐工程師鮮能有真正選擇。今次﹐我們決定參選﹐乃是希望能為香港政冶發展打破悶局,重新為香港工程師燃點希望。」
未知一些朋友的朋友是否同意﹖
可是﹐歷史關係﹐我們的中文都受了英文影響。很多時候﹐它都是英文的直接翻譯。加上科技突飛猛進﹐隨著外來潮流文化到來﹐我們的語文更受了其他外語影響。當中﹐以日文為甚。街上走走﹐不難讀到那些冒充中文的日文漢字。(同時間﹐我們的英文卻又受著中文影響。那叫做CHINGLISH。於是﹐在這個特殊的地域裡﹐我們寫的﹑講的﹐都是語文混合物。)
最近﹐到了那個普選工程路線的網頁瀏覽﹐這個說法更加得到肯定。
那是一群中年香港工程師參加選舉委員會委員的競選網頁。網頁裡面不是一些從英文原文粗暴搬過來的中文﹐便是一些很含糊﹑又很纍贅的文字。而且﹐邏輯和事實﹐都有點問題。我想﹐也許他們的思想亦很混亂。不過﹐在這樣無里頭的選舉制度下﹐除了那些欽點人和給人欽點的人外﹐有誰不感到不混亂﹖
他們說﹐「我們是來自不同崗位,包括私營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工程師。我們並非共同屬於任何一個政治團體,但我們擁有共同的理念:香港人理應享有更民主的體制和更有效的管治」。
他們又說﹐「在特區過去十年的特首選舉中,工程界的候選人少有以爭取普選為目標,以致工程師從來未有機會作出真正的選擇。我們參與作為選舉委員會的候選人,目的在於提供一個促成轉變的契機,為香港的政冶發展打破悶局,重新燃點希望」。
我想﹐這樣的文字只比「總書記指出,加強思想理論建設,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在實踐中繼續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而神聖的使命。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緊密結合新世紀新階段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提出以人為本,實現科學發展、建構社會主義和諧、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新型國家,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等重大戰略思想和戰略任務,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稍稍優勝。始終﹐香港才回歸紅色中國不夠十年﹐大家還未給污染到那個無可救藥的地步。
不過﹐便是因為我們遭污染的程度依然有限﹐我們更要把握時間﹐好好加強基本功﹐以抵抗那些紅色中文南下的猛烈攻擊。
我同意﹐多聽多寫多講﹐語文自然好。可是﹐假如多聽多寫多講的都只是比那些紅色中文稍稍優勝的不太爛中文﹐我們又怎能夠期望自己對紅色中文有免疫力﹖奈何﹐在我們週圍,都鮮有一些真正的中文文字。也不用太有觀察力﹐你也總能發覺﹐在我們週邊﹐常常充斥著這樣的句子﹕「作為香港的特首﹐我對於這件人神共憤的惡行﹐實在感到痛心疾首」﹑「星期五開會後﹐銀行公會決定作出加息行動」﹑「百貨公司決定作出大割引」﹑「使用中」等。更甚的是﹐這樣的文字竟然也出現在我們的報章上面。
老實說﹐在香港﹐能夠寫真正中文的人已經不多。除了金庸﹑董橋和陶傑外﹐我想不到另外一個。(也許﹐林行止先生會是第四個。只是﹐我總常在他的文章裡找到一些西化的句子。)不過﹐這倒也方便我們去加強自己的中文基本功。況且﹐董橋和陶傑都有在《蘋果日報》寫專欄。每天一份《蘋果》﹐的確可以加強自己的免疫能力。
對於普選工程路線的那些文字﹐我可大膽地有以下粗略改動(見笑)﹕
「我們都是工程師﹐來自不同崗位﹐包括私營企業與政府部門。我們不屬於任何政治團體。我們相信﹐香港應有更民主的體制和更有效的管治。在過去選舉委員會競選中﹐工程師鮮能有真正選擇。今次﹐我們決定參選﹐乃是希望能為香港政冶發展打破悶局,重新為香港工程師燃點希望。」
未知一些朋友的朋友是否同意﹖
Sunday, November 26, 2006
早陣子﹐有朋友給我發了一個電郵。裡面有一個網址﹐是一群香港工程師參選選舉委員會的競選網頁。電郵裡寫道﹐他們都支持普選。在這個大前提下﹐他們組成了一個聯盟﹐希望能夠抵抗工程界裡面的傳統勢力。他們稱自己做E4US。全名是ENGINEERS FOR UNIVERSAL SUFFRAGE。也有一個中文名字﹐叫普選工程路線。
難得還有香港工程師願意為政治獻身。好奇下﹐我走到了那個網頁逛逛。
才來到那個網頁﹐還未讀到他們的政綱﹐我知道那將會是一個笑話。單看那八個候選人的照片﹐便是他們的政綱如何吸引﹑如何使我有共鳴﹐我也不會相信他們﹐他們也不可能得到我的一票。我不可能把我的票投給那些或賊眉賊眼﹑或擠眉弄眼的香港典型中年男人。縱然都是一身名牌西裝,我看到的竟然是一個又一個穿汗衫的小巴司機和送貨員。也許﹐那就是陶傑所講的「一身叫雞氣」。最可怕的是﹐那些照片都經過精心挑選。
他們的政綱有三大重點﹕(一) 競爭性特首選舉﹑(二)普選﹑(三)可持續基建。
不知道從那時候開始﹐香港人便很喜歡把自己跟老伴在房中的事﹐肆無忌憚地講出口。什麼事情﹐都習慣在後面多加一個「性」字。像選擇性﹑建設性。或許﹐這是社會開放進步的象徵。只是﹐我依然是一個傳統的人。對於「競爭性特首選舉」這個詞語﹐我實在很反感。不過﹐在「一身叫雞氣」下﹐那又似乎使用得很自然。至少﹐很符合身份。
他們表示﹐要運用提名權,致力促使最少兩名特首候選人競爭,提升透明度和鼓勵公開辯論。讀到這裡﹐我們能不替自己感到可憐﹑為自己感到悲哀﹖這竟然可以是政綱﹗我們知道自己不能一人一票選特首﹐於是便盲目捧一些人出來﹐跟共產黨合力創造一個類似公開的民主選舉﹐以慰藉廣大市民心中的寂寥。那不是「運用」﹐那是名符其實的「濫用」。不過﹐他們倒也算老實。一早講明﹐便是那個人如何不濟﹐他們也會推舉他成為特首候選人。
他們又說﹐會全力支持2012年實行普選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席,並以此作為選擇特首的首要準則。
其實﹐我是不大明白這句話的意思﹐總覺得有語病。也許﹐在那個「並」字上面。我想﹐他們是說﹐他們推舉的特首候選人﹐必須支持2012年實行普選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席罷﹖此外﹐既然有首要準則﹐那麼次要準則﹑和第三準則又是些什麼呢﹖找遍整個網頁﹐也尋不到。相反﹐我倒找到兩個「首要準則」。莫要忘記﹐他們劈頭便說﹐要特首選舉有多過一個候選人。那即是當一個參選者獲得了很多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後﹐他們便會不顧一切﹐推舉另外一位。兩個「首要準則」﹐孰重孰輕﹐似乎連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政綱是他們跟選民溝通的基石。如此粗製濫造﹐怎能得人信心﹖
他們又談到可持續基建。他們寫道﹐因應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加大投資、加快建設可持續基建和社區設施,以致力改善環境質素、消減貧窮和提升本土文化發展。
一群工程師﹐當然不能不講基建。因為那是他們賴以維生的基本事情。他們要政府加大投資、加快建設﹐實在無可厚非。我不相信﹐他們是什麼忠實的凱恩斯信徒。至於改善環境質素、消減貧窮和提升本土文化發展﹐只不過是掩飾自私的化妝。誰不為己﹖要做工程界在選舉委員會的代表﹐實在不能不顧及一下業界利益。至於﹐有沒有候選人理會﹐那又是另一回事。(上星期﹐MILTON FRIEDMAN去世。一座國際城市﹐應該要再次掀起討論這位經濟學家的說法。始終﹐那是列根政府和戴卓爾夫人政府的根本。佛利民說﹐政府加大投資建設﹐只會做成高通脹﹐並不能改善生產和就業情況。未知這一群工程師對此如何看法﹖)
或者﹐我不應該太挑剔。因為都不是他們的錯。他們不是在爭做特首﹐他們只是在爭取推舉特首候選人的特權。他們只是參選選舉委員會罷了。何解需要一個政綱﹐去討回那個本應是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況且﹐在現有制度下﹐有遠大理想﹑有政治魄力的人﹐都不會跑出來投身政治﹔在當今社會裡﹐我們的候選人﹐無論是那一樣的候選人﹐都能夠有什麼政綱﹖當一個城市的「政界」的上位之路,給上頭的主人用水泥封了頂,所有參與政治的人都變成了在泥漿打滾浮沉的一群泥鰍,不見天日。我們怎能期待有一個DAVID CAMERON出現﹖除了做夢的時候。
「幸運地」﹐我也認識一個特權份子。他是選委會委員﹐亦是人大代表。跟他談論間﹐我知道這一個遊戲規則。對於這一群工程師能否走入建制﹐我心存懷疑。更遑論走入建制﹐以促使改變。要知道﹐要做選舉委員會委員﹐根本不需要什麼政綱。假若你還以為需要政綱﹐那表示你未得到欽點。何苦自己跑去做這一場鬧劇的丑角﹐做這一個笑話裡面的大笑話﹖你們的精力應該花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面。
我同意﹐IF YOU CAN'T BEAT THEM,JOIN THEM的講法。只是﹐我們可曾否嘗試過打敗他們﹖
難得還有香港工程師願意為政治獻身。好奇下﹐我走到了那個網頁逛逛。
才來到那個網頁﹐還未讀到他們的政綱﹐我知道那將會是一個笑話。單看那八個候選人的照片﹐便是他們的政綱如何吸引﹑如何使我有共鳴﹐我也不會相信他們﹐他們也不可能得到我的一票。我不可能把我的票投給那些或賊眉賊眼﹑或擠眉弄眼的香港典型中年男人。縱然都是一身名牌西裝,我看到的竟然是一個又一個穿汗衫的小巴司機和送貨員。也許﹐那就是陶傑所講的「一身叫雞氣」。最可怕的是﹐那些照片都經過精心挑選。
他們的政綱有三大重點﹕(一) 競爭性特首選舉﹑(二)普選﹑(三)可持續基建。
不知道從那時候開始﹐香港人便很喜歡把自己跟老伴在房中的事﹐肆無忌憚地講出口。什麼事情﹐都習慣在後面多加一個「性」字。像選擇性﹑建設性。或許﹐這是社會開放進步的象徵。只是﹐我依然是一個傳統的人。對於「競爭性特首選舉」這個詞語﹐我實在很反感。不過﹐在「一身叫雞氣」下﹐那又似乎使用得很自然。至少﹐很符合身份。
他們表示﹐要運用提名權,致力促使最少兩名特首候選人競爭,提升透明度和鼓勵公開辯論。讀到這裡﹐我們能不替自己感到可憐﹑為自己感到悲哀﹖這竟然可以是政綱﹗我們知道自己不能一人一票選特首﹐於是便盲目捧一些人出來﹐跟共產黨合力創造一個類似公開的民主選舉﹐以慰藉廣大市民心中的寂寥。那不是「運用」﹐那是名符其實的「濫用」。不過﹐他們倒也算老實。一早講明﹐便是那個人如何不濟﹐他們也會推舉他成為特首候選人。
他們又說﹐會全力支持2012年實行普選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席,並以此作為選擇特首的首要準則。
其實﹐我是不大明白這句話的意思﹐總覺得有語病。也許﹐在那個「並」字上面。我想﹐他們是說﹐他們推舉的特首候選人﹐必須支持2012年實行普選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席罷﹖此外﹐既然有首要準則﹐那麼次要準則﹑和第三準則又是些什麼呢﹖找遍整個網頁﹐也尋不到。相反﹐我倒找到兩個「首要準則」。莫要忘記﹐他們劈頭便說﹐要特首選舉有多過一個候選人。那即是當一個參選者獲得了很多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後﹐他們便會不顧一切﹐推舉另外一位。兩個「首要準則」﹐孰重孰輕﹐似乎連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政綱是他們跟選民溝通的基石。如此粗製濫造﹐怎能得人信心﹖
他們又談到可持續基建。他們寫道﹐因應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加大投資、加快建設可持續基建和社區設施,以致力改善環境質素、消減貧窮和提升本土文化發展。
一群工程師﹐當然不能不講基建。因為那是他們賴以維生的基本事情。他們要政府加大投資、加快建設﹐實在無可厚非。我不相信﹐他們是什麼忠實的凱恩斯信徒。至於改善環境質素、消減貧窮和提升本土文化發展﹐只不過是掩飾自私的化妝。誰不為己﹖要做工程界在選舉委員會的代表﹐實在不能不顧及一下業界利益。至於﹐有沒有候選人理會﹐那又是另一回事。(上星期﹐MILTON FRIEDMAN去世。一座國際城市﹐應該要再次掀起討論這位經濟學家的說法。始終﹐那是列根政府和戴卓爾夫人政府的根本。佛利民說﹐政府加大投資建設﹐只會做成高通脹﹐並不能改善生產和就業情況。未知這一群工程師對此如何看法﹖)
或者﹐我不應該太挑剔。因為都不是他們的錯。他們不是在爭做特首﹐他們只是在爭取推舉特首候選人的特權。他們只是參選選舉委員會罷了。何解需要一個政綱﹐去討回那個本應是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況且﹐在現有制度下﹐有遠大理想﹑有政治魄力的人﹐都不會跑出來投身政治﹔在當今社會裡﹐我們的候選人﹐無論是那一樣的候選人﹐都能夠有什麼政綱﹖當一個城市的「政界」的上位之路,給上頭的主人用水泥封了頂,所有參與政治的人都變成了在泥漿打滾浮沉的一群泥鰍,不見天日。我們怎能期待有一個DAVID CAMERON出現﹖除了做夢的時候。
「幸運地」﹐我也認識一個特權份子。他是選委會委員﹐亦是人大代表。跟他談論間﹐我知道這一個遊戲規則。對於這一群工程師能否走入建制﹐我心存懷疑。更遑論走入建制﹐以促使改變。要知道﹐要做選舉委員會委員﹐根本不需要什麼政綱。假若你還以為需要政綱﹐那表示你未得到欽點。何苦自己跑去做這一場鬧劇的丑角﹐做這一個笑話裡面的大笑話﹖你們的精力應該花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面。
我同意﹐IF YOU CAN'T BEAT THEM,JOIN THEM的講法。只是﹐我們可曾否嘗試過打敗他們﹖
Saturday, November 25, 2006
在都柏林﹐我是獨個兒居住。
我知道﹐跟別人同住﹐我是可以省回一大筆屋租﹐也可以住在較大的房子裡面﹐可以有前後花園﹐夏天更可以每個星期開燒烤派對﹐飲得醉醉。
只是﹐我實在太看重自己的私隱。始終﹐再不是年青的日子。我不想監察別人﹐當然也不想別人監察我的生活起居。在陌生的國度跟一些陌生的人住在一起﹐我可不大接受得了。活到了這個年紀﹐假如要同居飲食﹐我們都應該只跟自己心愛的人一起。
我知道﹐一個獨居男人的家﹐可能會為一個女人帶來無限追憶。所以﹐我實在不能讓它變成一個狗竇。(雖然﹐很多時候﹐男人都是一條狗。)我不能使那一夜的甜蜜留下一絲遺憾。當然﹐在一個狗竇裡﹐能否有一夜的甜蜜﹐那是另一回事。
假若女生按著陶傑開的CHECKLIST來到我的住所﹐我相信﹐離開的時候﹐她們應該很滿意﹐手上拿著的是一張滿是剔號的紙。
陶傑建議女生﹐第一次應邀到男人的家作客﹐要睜大眼睛留意他獨居的家。因為從家居的一些細節﹐可以看出修飾不來的真性情。
首先粗看客廳的擺設﹕是否打算整齊﹐書架上的書是何等品種﹐CD架上有什麼音樂。然後﹐藉口要一杯汽水﹐趁他打開冰箱時看看裡面食物有沒有用保鮮盒儲存好。這個男生喜歡下廚嗎﹖留意醬油的瓶子有沒有一層油漬﹐隔夜的碗碟有沒有洗掉。也到他的浴室去。鬚後水和古龍水名貴與否不打緊﹐要看看洗面毛巾有沒有疊好﹐廁紙有沒有用完還未換上﹐牙刷是不是舊得捲起了毛。
在我愛爾蘭的家﹐那些書大多數都是小說。JOHN LE CARRÉ的間諜小說最多。其次是JEFFREY ARCHER的作品。也有王爾德﹑SAMMUEL BECKETT的劇作和一些PENGUIN CLASSICS。非小說類則有一本論及阿拉伯和猶太人關係的書﹑一本講RYANAIR發跡的書。還有一本書﹐輕談尼日利亞民風習俗。都是在都柏林的二手書店買。
CD實在不是太多。因為我一張CD也沒有從香港帶來﹐我只把一些BEATLES、OASIS、PULP、張學友、譚詠麟﹑陳亦迅儲了到電腦和iPOD裡面。老實說﹐也有一些更低檔次的港產流行曲﹐像TWINS和容祖兒。況且﹐這兒的CD都很貴﹐動輒要二十塊歐羅。不過﹐來到愛爾蘭後﹐我是喜歡上了ROD STEWART。於是﹐也買了幾張他的舊碟。陶傑說﹐「男人的收藏至少要有一打古典音樂。喜歡POP MUSIC不大緊﹐要有檔次稍高一點的產品。」或者﹐在這方面我是僅僅及格。
以前﹐我不喜歡下廚。只是﹐最近我開始留意電視的烹飪節目﹐到書店也有翻翻那些COOKBOOKS。正如我跟其中一個上司ANN說﹐AT LEAST I AM NOW A BETTER COOK THAN I WAS。而且﹐我相信﹐這只會越來越好。PRACTICE MAKES PERFECT。廚房裡面一定沒有隔夜的碗碟還未洗掉。此外﹐浴室裡的洗面毛巾一定疊好﹐廁紙不會用完還未換上﹐牙刷不會舊得捲起了毛。
檢查到此﹐也應該來到我的睡房了罷。
我也應該看到你那滿意甜美的笑容。知道嗎﹖那半邊床可是留待給你。
我知道﹐跟別人同住﹐我是可以省回一大筆屋租﹐也可以住在較大的房子裡面﹐可以有前後花園﹐夏天更可以每個星期開燒烤派對﹐飲得醉醉。
只是﹐我實在太看重自己的私隱。始終﹐再不是年青的日子。我不想監察別人﹐當然也不想別人監察我的生活起居。在陌生的國度跟一些陌生的人住在一起﹐我可不大接受得了。活到了這個年紀﹐假如要同居飲食﹐我們都應該只跟自己心愛的人一起。
我知道﹐一個獨居男人的家﹐可能會為一個女人帶來無限追憶。所以﹐我實在不能讓它變成一個狗竇。(雖然﹐很多時候﹐男人都是一條狗。)我不能使那一夜的甜蜜留下一絲遺憾。當然﹐在一個狗竇裡﹐能否有一夜的甜蜜﹐那是另一回事。
假若女生按著陶傑開的CHECKLIST來到我的住所﹐我相信﹐離開的時候﹐她們應該很滿意﹐手上拿著的是一張滿是剔號的紙。
陶傑建議女生﹐第一次應邀到男人的家作客﹐要睜大眼睛留意他獨居的家。因為從家居的一些細節﹐可以看出修飾不來的真性情。
首先粗看客廳的擺設﹕是否打算整齊﹐書架上的書是何等品種﹐CD架上有什麼音樂。然後﹐藉口要一杯汽水﹐趁他打開冰箱時看看裡面食物有沒有用保鮮盒儲存好。這個男生喜歡下廚嗎﹖留意醬油的瓶子有沒有一層油漬﹐隔夜的碗碟有沒有洗掉。也到他的浴室去。鬚後水和古龍水名貴與否不打緊﹐要看看洗面毛巾有沒有疊好﹐廁紙有沒有用完還未換上﹐牙刷是不是舊得捲起了毛。
在我愛爾蘭的家﹐那些書大多數都是小說。JOHN LE CARRÉ的間諜小說最多。其次是JEFFREY ARCHER的作品。也有王爾德﹑SAMMUEL BECKETT的劇作和一些PENGUIN CLASSICS。非小說類則有一本論及阿拉伯和猶太人關係的書﹑一本講RYANAIR發跡的書。還有一本書﹐輕談尼日利亞民風習俗。都是在都柏林的二手書店買。
CD實在不是太多。因為我一張CD也沒有從香港帶來﹐我只把一些BEATLES、OASIS、PULP、張學友、譚詠麟﹑陳亦迅儲了到電腦和iPOD裡面。老實說﹐也有一些更低檔次的港產流行曲﹐像TWINS和容祖兒。況且﹐這兒的CD都很貴﹐動輒要二十塊歐羅。不過﹐來到愛爾蘭後﹐我是喜歡上了ROD STEWART。於是﹐也買了幾張他的舊碟。陶傑說﹐「男人的收藏至少要有一打古典音樂。喜歡POP MUSIC不大緊﹐要有檔次稍高一點的產品。」或者﹐在這方面我是僅僅及格。
以前﹐我不喜歡下廚。只是﹐最近我開始留意電視的烹飪節目﹐到書店也有翻翻那些COOKBOOKS。正如我跟其中一個上司ANN說﹐AT LEAST I AM NOW A BETTER COOK THAN I WAS。而且﹐我相信﹐這只會越來越好。PRACTICE MAKES PERFECT。廚房裡面一定沒有隔夜的碗碟還未洗掉。此外﹐浴室裡的洗面毛巾一定疊好﹐廁紙不會用完還未換上﹐牙刷不會舊得捲起了毛。
檢查到此﹐也應該來到我的睡房了罷。
我也應該看到你那滿意甜美的笑容。知道嗎﹖那半邊床可是留待給你。
Friday, November 24, 2006
離開公司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七點半。除了我之外﹐公司裡面一個人也沒有。這是我來到愛爾蘭後﹐第一次因為工作關係﹐遲過六點鐘下班。
ANN比我早一點離開。臨走的時候﹐她問用不用送我一程。我知道﹐也算是順路。不過﹐我亦知道﹐這個時候市中心的交通非常繁忙。到處都是人車爭路。我不想因此阻礙了她兩個孩子吃晚飯的時間。況且﹐我也想休息一會兒。跟她同車﹐少不免又要繼續跟她傾談公事。我經已和她討論了一整天。
沒有搭順風車﹐我當然依舊乘火車回家。走到月臺﹐望望熒光屏﹐慶幸下一班車還有三分鐘便到站。不用在寒冷的空氣裡站立等候太久。要知道﹐非繁忙時候﹐每班火車可相隔十五分鐘。為了增加身體的熱量﹐我決定在月臺上慢走。卻竟然給我看到放在一角的小食機。早忘記了的肚餓﹐又突然湧上心頭。不知道是午餐的那份三明治做得太小﹐還是討論的事情實在太悶蛋﹖下午開會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的腦海裡便只是一些食物。我想起了家裡的那個黃瓜﹑冰箱裡的那些雪條。還想起了廚櫃裡面的那些紅豆。他們在研究機場第二階段擴建的工作﹐我則獨自鑽研做紅豆沙的方法。憑著我僅有的入廚知識﹐我想到的﹐只是把冰糖煮溶﹐然後再加紅豆一起﹐煮到一團便成。應該不是一個很難的甜品罷。
我找來一些硬幣﹐買了一排朱古力上車。
車廂裡﹐便只得我一個。始終是星期一的夜晚﹐沒有太多人會到市中心去。我一邊咬著朱古力﹐一邊望著窗外的夜色。我決定上館子吃晚飯。心裡算算﹐知道回到家也過了八點﹐弄得一些菜來﹐吃完飯﹐洗過碗碟﹐就要差不多十時。洗過澡後﹐便再沒有什麼時間完成在公司未完成的那三個REPORTS。我不想太晚上床﹐因為明天還要到機場PRESENT那三個REPORTS。我想精神一點。我以為﹐因為休息不夠﹐所以開會時魂遊太虛﹐在食物的森林裡漫遊。
以前在香港﹐獨自一人吃飯﹐我會買外賣。始終﹐一個人到館子去﹐感覺總是有點怪怪的。
不過﹐異鄉的生活使我改變了。
我已經習慣了一個人吃飯。在家﹑還是在館子﹐都變得沒有所謂。會有什麼所謂﹖對於我來說﹐其實都是一樣的地方。只是﹐這也是我在都柏林第一次獨自到館子去。
我到了住所附近的一間中菜館。我點了半斤水餃和一碟蒜茸菜心。我以為﹐到館子吃飯會較省時間。只是一邊讀著報紙﹐一邊啃著那些水餃﹐不經不覺也過了一句鐘。我很不情願地收起了報紙﹐走到櫃檯結賬。老實說﹐我應該要加快腳步。因為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可是﹐越想加快﹐雙腳卻越不聽話。他們竟然越走越慢。平時﹐從O'CONNELL STREET走回家不用十分鐘。今天﹐竟然多花了五分鐘。
回到家﹐洗過澡。碰巧﹐有朋友從墨西哥撥了個電話過來。我們便傾談一段時候。之後﹐又有母親的來電。於是﹐到了十一點半﹐才正式開始改動那三個REPORTS。
在電腦面前﹐我想了又想。最後﹐對於那三個REPORTS,也沒有什麼大改動。我以為﹐還豎明天PRESENT的時候﹐也會收到CLIENT的COMMENT,倒不如之後一次過更改﹐免得浪費時間。況且﹐我還未有為今天的專欄下筆。自BLOOMSDAY後﹐除了那些不在家的日子﹐我每天至少寫好一篇BLOG。對於一些習慣了的事情﹐我倒是很有恆心堅持。於是﹐在半個小時內﹐我寫了這一篇無聊的文章。都只是我今天無聊的生活日記。
ANN比我早一點離開。臨走的時候﹐她問用不用送我一程。我知道﹐也算是順路。不過﹐我亦知道﹐這個時候市中心的交通非常繁忙。到處都是人車爭路。我不想因此阻礙了她兩個孩子吃晚飯的時間。況且﹐我也想休息一會兒。跟她同車﹐少不免又要繼續跟她傾談公事。我經已和她討論了一整天。
沒有搭順風車﹐我當然依舊乘火車回家。走到月臺﹐望望熒光屏﹐慶幸下一班車還有三分鐘便到站。不用在寒冷的空氣裡站立等候太久。要知道﹐非繁忙時候﹐每班火車可相隔十五分鐘。為了增加身體的熱量﹐我決定在月臺上慢走。卻竟然給我看到放在一角的小食機。早忘記了的肚餓﹐又突然湧上心頭。不知道是午餐的那份三明治做得太小﹐還是討論的事情實在太悶蛋﹖下午開會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的腦海裡便只是一些食物。我想起了家裡的那個黃瓜﹑冰箱裡的那些雪條。還想起了廚櫃裡面的那些紅豆。他們在研究機場第二階段擴建的工作﹐我則獨自鑽研做紅豆沙的方法。憑著我僅有的入廚知識﹐我想到的﹐只是把冰糖煮溶﹐然後再加紅豆一起﹐煮到一團便成。應該不是一個很難的甜品罷。
我找來一些硬幣﹐買了一排朱古力上車。
車廂裡﹐便只得我一個。始終是星期一的夜晚﹐沒有太多人會到市中心去。我一邊咬著朱古力﹐一邊望著窗外的夜色。我決定上館子吃晚飯。心裡算算﹐知道回到家也過了八點﹐弄得一些菜來﹐吃完飯﹐洗過碗碟﹐就要差不多十時。洗過澡後﹐便再沒有什麼時間完成在公司未完成的那三個REPORTS。我不想太晚上床﹐因為明天還要到機場PRESENT那三個REPORTS。我想精神一點。我以為﹐因為休息不夠﹐所以開會時魂遊太虛﹐在食物的森林裡漫遊。
以前在香港﹐獨自一人吃飯﹐我會買外賣。始終﹐一個人到館子去﹐感覺總是有點怪怪的。
不過﹐異鄉的生活使我改變了。
我已經習慣了一個人吃飯。在家﹑還是在館子﹐都變得沒有所謂。會有什麼所謂﹖對於我來說﹐其實都是一樣的地方。只是﹐這也是我在都柏林第一次獨自到館子去。
我到了住所附近的一間中菜館。我點了半斤水餃和一碟蒜茸菜心。我以為﹐到館子吃飯會較省時間。只是一邊讀著報紙﹐一邊啃著那些水餃﹐不經不覺也過了一句鐘。我很不情願地收起了報紙﹐走到櫃檯結賬。老實說﹐我應該要加快腳步。因為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可是﹐越想加快﹐雙腳卻越不聽話。他們竟然越走越慢。平時﹐從O'CONNELL STREET走回家不用十分鐘。今天﹐竟然多花了五分鐘。
回到家﹐洗過澡。碰巧﹐有朋友從墨西哥撥了個電話過來。我們便傾談一段時候。之後﹐又有母親的來電。於是﹐到了十一點半﹐才正式開始改動那三個REPORTS。
在電腦面前﹐我想了又想。最後﹐對於那三個REPORTS,也沒有什麼大改動。我以為﹐還豎明天PRESENT的時候﹐也會收到CLIENT的COMMENT,倒不如之後一次過更改﹐免得浪費時間。況且﹐我還未有為今天的專欄下筆。自BLOOMSDAY後﹐除了那些不在家的日子﹐我每天至少寫好一篇BLOG。對於一些習慣了的事情﹐我倒是很有恆心堅持。於是﹐在半個小時內﹐我寫了這一篇無聊的文章。都只是我今天無聊的生活日記。
Thursday, November 23, 2006
上個月﹐每朝早起床的時候﹐我都會對著鏡子﹐唱著這一厥歌﹕PAULINE一走那天﹐我決定紮辮。
不記得是誰的作品了。是太極罷﹖
人生差不多來到第三個十年﹐除了母親以前的一位同事外﹐我實在不認識一個叫PAULINE的女性。每天早上也會哼起那句歌詞﹐其實都只因最後的那兩個字。望著鏡中倒影﹐在腦海裡營造一個叫PAULINE的女生的雛形﹐竟然也變得很自然。
印象中﹐是未試過留著那樣長的頭髮﹕兩邊過耳﹐後面及肩。
上次到理髮店﹐已經是八月頭的事了。那是銀行假期﹐我依舊到了倫敦去。離開香港後﹐我總是在倫敦剪頭髮。第一次是六月初。第二次﹐便是對上一次了。所以﹐留著很長很長的頭髮﹐實在不難理解。以前在香港﹐差不多一個月多﹐我便要到理髮店去。
本來﹐我是想過依舊待到銀行假期才去剪頭髮。因為在倫敦那間理髮店﹐我根本不用多說﹐他們都曉得如何修理好我一頭長髮。可能﹐他們都是從香港過來的緣故罷。雖然價錢是貴了一點。比起我在香港理髮貴了一百塊港幣。至少﹐對上兩次﹐我都很滿意。
只是﹐一天早上﹐我花了一段時間﹐依然未能弄好那頭長髮。我知道﹐我是不能等到倫敦去了。是它們等待不了。
於是﹐到倫敦前的一個星期六早上﹐我便走到了ST STEPHEN'GREEN去。那兒有一間似乎很像樣的理髮店。才二十六塊歐羅。(比倫敦平一半。)ADRIAN幫襯過。他說﹐應該是那個價錢裡面最好的一間。他們全程都只用剪刀。
不過﹐當我走了入店後﹐我感覺到後悔。原來﹐裡面的理髮師大部份都是東歐人。才得一個愛爾蘭人。假如我是信得過這些從東歐來的女人﹐我早就到了住所附近那間店﹐讓她們為我剪髮。她們才要我五塊。每天黃昏﹐那間店外面都有一條長龍等候。只是當看到從店裡面走出來的顧客﹐我寧願多花一點錢。
可是﹐當你花了二十六塊﹐才發覺那些東歐女人﹐原來真的只懂得ROY KEANE的髮型後﹐你會暗罵自己的笨﹕竟然用五倍的價錢去買來人家賣五塊的貨物。
我說﹐她們只懂得ROY KEANE的髮型﹐因為我覺得那根本不用什麼技術。
我怕﹐她們不懂得如何理髮。眼前的這個這個東歐女人竟然一邊剪﹐一邊問我如何剪法。天﹗我怎知道如何剪法?我是習慣一走入理髮店﹐洗好頭後﹐就坐著墮進夢鄉。我從來不干涉。從來﹐我都只有一個要求﹕剪短﹐不過又不可太短。假如有新的創意﹐都是理髮師跟我介紹。現在﹐她卻問我如何剪法﹐還要不斷的問﹐而CUT IT SHORT BUT NOT SKIN HEAD竟然不是一個答案。我實在不能不投降。怎麼可能落剪前﹐還未知道怎樣個剪法﹖
我於是改變了想法。我不要她幫我剪短頭髮了。我說﹐還是長長的罷。不好短了。
我怕﹐我最後會變成ROY KEANE。
況且﹐聖誕前﹐我也會到倫敦一趟。有些錢﹐是不能不花的。
走在街上﹐望到玻璃窗上的倒影﹐我明白到﹐何解早陣子J會因為一頭剪得很差的髮型弄得心情很差。雖然MARIA似乎很欣賞我這個新的髮型。
不記得是誰的作品了。是太極罷﹖
人生差不多來到第三個十年﹐除了母親以前的一位同事外﹐我實在不認識一個叫PAULINE的女性。每天早上也會哼起那句歌詞﹐其實都只因最後的那兩個字。望著鏡中倒影﹐在腦海裡營造一個叫PAULINE的女生的雛形﹐竟然也變得很自然。
印象中﹐是未試過留著那樣長的頭髮﹕兩邊過耳﹐後面及肩。
上次到理髮店﹐已經是八月頭的事了。那是銀行假期﹐我依舊到了倫敦去。離開香港後﹐我總是在倫敦剪頭髮。第一次是六月初。第二次﹐便是對上一次了。所以﹐留著很長很長的頭髮﹐實在不難理解。以前在香港﹐差不多一個月多﹐我便要到理髮店去。
本來﹐我是想過依舊待到銀行假期才去剪頭髮。因為在倫敦那間理髮店﹐我根本不用多說﹐他們都曉得如何修理好我一頭長髮。可能﹐他們都是從香港過來的緣故罷。雖然價錢是貴了一點。比起我在香港理髮貴了一百塊港幣。至少﹐對上兩次﹐我都很滿意。
只是﹐一天早上﹐我花了一段時間﹐依然未能弄好那頭長髮。我知道﹐我是不能等到倫敦去了。是它們等待不了。
於是﹐到倫敦前的一個星期六早上﹐我便走到了ST STEPHEN'GREEN去。那兒有一間似乎很像樣的理髮店。才二十六塊歐羅。(比倫敦平一半。)ADRIAN幫襯過。他說﹐應該是那個價錢裡面最好的一間。他們全程都只用剪刀。
不過﹐當我走了入店後﹐我感覺到後悔。原來﹐裡面的理髮師大部份都是東歐人。才得一個愛爾蘭人。假如我是信得過這些從東歐來的女人﹐我早就到了住所附近那間店﹐讓她們為我剪髮。她們才要我五塊。每天黃昏﹐那間店外面都有一條長龍等候。只是當看到從店裡面走出來的顧客﹐我寧願多花一點錢。
可是﹐當你花了二十六塊﹐才發覺那些東歐女人﹐原來真的只懂得ROY KEANE的髮型後﹐你會暗罵自己的笨﹕竟然用五倍的價錢去買來人家賣五塊的貨物。
我說﹐她們只懂得ROY KEANE的髮型﹐因為我覺得那根本不用什麼技術。
我怕﹐她們不懂得如何理髮。眼前的這個這個東歐女人竟然一邊剪﹐一邊問我如何剪法。天﹗我怎知道如何剪法?我是習慣一走入理髮店﹐洗好頭後﹐就坐著墮進夢鄉。我從來不干涉。從來﹐我都只有一個要求﹕剪短﹐不過又不可太短。假如有新的創意﹐都是理髮師跟我介紹。現在﹐她卻問我如何剪法﹐還要不斷的問﹐而CUT IT SHORT BUT NOT SKIN HEAD竟然不是一個答案。我實在不能不投降。怎麼可能落剪前﹐還未知道怎樣個剪法﹖
我於是改變了想法。我不要她幫我剪短頭髮了。我說﹐還是長長的罷。不好短了。
我怕﹐我最後會變成ROY KEANE。
況且﹐聖誕前﹐我也會到倫敦一趟。有些錢﹐是不能不花的。
走在街上﹐望到玻璃窗上的倒影﹐我明白到﹐何解早陣子J會因為一頭剪得很差的髮型弄得心情很差。雖然MARIA似乎很欣賞我這個新的髮型。
Wednesday, November 22, 2006
在外地住了半年﹐發覺了一個現象﹕假如一個中國女人能夠讓西方的男人深深著迷﹐她們一定是比豬排跟豬排的豬排。或者﹐我應該精確一點。我這兒的「西方」,指的是都柏林和倫敦。我以為﹐意大利的男人應該不可能這樣BAD TASTE。從他們穿衣服的口味來看﹐我深信他們不可能這樣BAD TASTE。
早前﹐《餃子》在倫敦和都柏林上演。電影海報上面寫的是「BAI LING STARRING」。完全找不到楊千嬅的名字。雖然MIRIAM也不是一個漂亮的女生﹐但至少比那隻白姓怪物好得多罷。
走在街頭﹐看到那一雙一雙的異國鴦侶﹐實在要很多謝那些外國的男生。真的辛苦了他們。他們的確吞掉了很大部份的中國怪物。假如我們依然發覺﹐中國大陸裡面有很多怪物橫走﹐那是因為數量實在太多。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得了。
早前﹐劉少奇遺孀辭世。倫敦時報有這樣的一段悼念文字﹕
In her heydays as the wife of Liu Shaoqi, her country's President, Wang Guangmei was China's most elegant and erudite First Lady. On trips abroad at her husband's side she was always the acme of feminine taste and elegance when women were expected to wear a Mao suit and have their hair cut into a stark bob. Meanwhile, the tall, slim and well-dressed Wang had attracted the wrath and envy of Mao's wife Jiang Qing, because she wore pearl necklaces at a time when fashion, make-up and women's accessories were considered as marks of bourgeois decadence.
文化大革命至今﹐也不過五十年。當年﹐那群給污染了的無辜小女孩﹐年紀最小的﹐現在也只是四十有多。在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依然有著過多的怪物,讓西方國家的男生吞掉不了﹐實在不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
正如陶傑所說﹐本來「異國情鴛的愛情﹐比一般的愛情更蕩氣迴腸﹐更具戲劇張力﹐因為多了種族國家的層面﹐愛情面臨的挑戰更加艱巨。其背景除了棕櫚樹﹐還有一場發生在遠方的戰爭。在流彈硝煙裡﹐一場傾城之戀悲壯地形成﹐在社會﹑種族﹑政治各種壓力下﹐又悲壯地殞滅」。只是隨著時代的變遷﹐這樣的浪漫神話已經逐漸褪色。
看著那些怪物拖著金髮白種男孩從身邊經過﹐我實在無從想像得到白流蘇和范柳原。
也許﹐是西方的男生跟我們的審美觀完全不同。也幸好他們的審美觀跟我們完全不同。
所以﹐香港的女生﹐莫要以釣到一個西方情郎做自己一生的目標。因為那可能是自己一生的悲哀。
早前﹐《餃子》在倫敦和都柏林上演。電影海報上面寫的是「BAI LING STARRING」。完全找不到楊千嬅的名字。雖然MIRIAM也不是一個漂亮的女生﹐但至少比那隻白姓怪物好得多罷。
走在街頭﹐看到那一雙一雙的異國鴦侶﹐實在要很多謝那些外國的男生。真的辛苦了他們。他們的確吞掉了很大部份的中國怪物。假如我們依然發覺﹐中國大陸裡面有很多怪物橫走﹐那是因為數量實在太多。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得了。
早前﹐劉少奇遺孀辭世。倫敦時報有這樣的一段悼念文字﹕
In her heydays as the wife of Liu Shaoqi, her country's President, Wang Guangmei was China's most elegant and erudite First Lady. On trips abroad at her husband's side she was always the acme of feminine taste and elegance when women were expected to wear a Mao suit and have their hair cut into a stark bob. Meanwhile, the tall, slim and well-dressed Wang had attracted the wrath and envy of Mao's wife Jiang Qing, because she wore pearl necklaces at a time when fashion, make-up and women's accessories were considered as marks of bourgeois decadence.
文化大革命至今﹐也不過五十年。當年﹐那群給污染了的無辜小女孩﹐年紀最小的﹐現在也只是四十有多。在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依然有著過多的怪物,讓西方國家的男生吞掉不了﹐實在不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
正如陶傑所說﹐本來「異國情鴛的愛情﹐比一般的愛情更蕩氣迴腸﹐更具戲劇張力﹐因為多了種族國家的層面﹐愛情面臨的挑戰更加艱巨。其背景除了棕櫚樹﹐還有一場發生在遠方的戰爭。在流彈硝煙裡﹐一場傾城之戀悲壯地形成﹐在社會﹑種族﹑政治各種壓力下﹐又悲壯地殞滅」。只是隨著時代的變遷﹐這樣的浪漫神話已經逐漸褪色。
看著那些怪物拖著金髮白種男孩從身邊經過﹐我實在無從想像得到白流蘇和范柳原。
也許﹐是西方的男生跟我們的審美觀完全不同。也幸好他們的審美觀跟我們完全不同。
所以﹐香港的女生﹐莫要以釣到一個西方情郎做自己一生的目標。因為那可能是自己一生的悲哀。
Tuesday, November 21, 2006
英國上議院提議讓一些轟動案件的審訊情形在電視廣播。
對於英國人來說﹐這當然很新鮮。不過﹐對於美國人來說﹐一點也不覺得新奇。因為很早的時候﹐他們已能夠在電視看到一些法庭審訊。最使人印象難忘的﹐莫過於十年前的那宗謀殺案。傳媒說﹐In the United States, criminal trials are regularly televised, with the cable channel Court TV broadcasting the country's most newsworthy and controversial legal proceedings. The most high-profile broadcasting of a trial was that of OJ Simpson, the former footballer and actor, acquitted of murder charges live on television。
當年﹐數以百萬觀眾﹐親眼看著OJ如何困難地把自己巨大的手﹐擠進那對細小染血的手套裡面。那是整個審訊的轉戾點。辯護律師那一句「IF IT DOESN'T FIT,YOU MUST ACQUITT」,經已成為了經典。
重溫著這宗舊聞﹐心裡湧起了很多想法。
我想﹐似乎那個事實將永遠再沒有第三者知曉。不過﹐這樣巨大的秘密究竟能夠藏在心裡多久﹖要讓這樣一個重大事實﹐孤獨地留在自己心裡面﹐是非常痛苦和辛苦的。因為你可以欺騙整個國家的人﹐你甚至可以瞞著全個世界的人。但無論如何﹐你就是騙不到自己﹗就是瞞不到自己﹗本來﹐世人皆醉我獨醒﹐已經是一個很難過的事情。在這樣無助的環境底下﹐還要收藏著一個巨大的秘密﹐真的只有鐵人才能抵受得了。至少﹐午夜夢迴的時候﹐定必一身冷汗。假如關了燈躺在床上﹐還能夠好好地墮進夢鄉的話。
我也想起了佐拉(ÉMILE ZOLA)的那本小說THÉRÈSE RAQUIN。故事裡面﹐男女主角為了能夠走在一起﹐於是殺死了那個丈夫。可是﹐殺了人後﹐他們因為驚慌惶恐﹐反而都失去了對對方的愛。沒有一個晚上﹐他們能夠靜靜地在黑暗裡沉入夢鄉。
也許﹐上帝以為﹐這樣的懲罰比較適合罷﹖
想不到過了幾天﹐便知道原來OJ SIMPSON準備出書。書裡面寫的是﹐他如何把自己妻子和她的朋友殺掉。當然﹐他加了這樣很重要的一句CONDITIONAL SENTENCE︰假如我的確做了(IF I WERE THE ONE RESPONSIBLE FOR THE CRIME)。書的名字﹐的確是IF I DID IT。
有書評人經已讀過了這本書。他們的評語是﹕SO DETAILED AND CHILLINGLY REALISTIC - WITH OJ AS THE CENTRAL FIGURE - THAT IT LEAVES NO DOUBT IT IS A CONFESSION OF WHAT REALLY HAPPENED。
OJ也上了電視節目做宣傳。在訪問裡﹐OJ被問及何解會寫道「我一生裡面都沒有見過那樣多血」(I HAVE NEVER SEEN SO MUCH BLOOD IN MY LIFE)。這位美式足球明星回答說﹐我想﹐當殺死了兩個人後﹐沒有人能夠不滿身鮮血。
我想﹐他是開始崩潰了。始終﹐他都不是一個鐵人。
當大家以為辯論已經落幕的時候﹐原來新的一輪才剛剛開始。
究竟他是不是就是那個兇手呢﹖
對於英國人來說﹐這當然很新鮮。不過﹐對於美國人來說﹐一點也不覺得新奇。因為很早的時候﹐他們已能夠在電視看到一些法庭審訊。最使人印象難忘的﹐莫過於十年前的那宗謀殺案。傳媒說﹐In the United States, criminal trials are regularly televised, with the cable channel Court TV broadcasting the country's most newsworthy and controversial legal proceedings. The most high-profile broadcasting of a trial was that of OJ Simpson, the former footballer and actor, acquitted of murder charges live on television。
當年﹐數以百萬觀眾﹐親眼看著OJ如何困難地把自己巨大的手﹐擠進那對細小染血的手套裡面。那是整個審訊的轉戾點。辯護律師那一句「IF IT DOESN'T FIT,YOU MUST ACQUITT」,經已成為了經典。
重溫著這宗舊聞﹐心裡湧起了很多想法。
我想﹐似乎那個事實將永遠再沒有第三者知曉。不過﹐這樣巨大的秘密究竟能夠藏在心裡多久﹖要讓這樣一個重大事實﹐孤獨地留在自己心裡面﹐是非常痛苦和辛苦的。因為你可以欺騙整個國家的人﹐你甚至可以瞞著全個世界的人。但無論如何﹐你就是騙不到自己﹗就是瞞不到自己﹗本來﹐世人皆醉我獨醒﹐已經是一個很難過的事情。在這樣無助的環境底下﹐還要收藏著一個巨大的秘密﹐真的只有鐵人才能抵受得了。至少﹐午夜夢迴的時候﹐定必一身冷汗。假如關了燈躺在床上﹐還能夠好好地墮進夢鄉的話。
我也想起了佐拉(ÉMILE ZOLA)的那本小說THÉRÈSE RAQUIN。故事裡面﹐男女主角為了能夠走在一起﹐於是殺死了那個丈夫。可是﹐殺了人後﹐他們因為驚慌惶恐﹐反而都失去了對對方的愛。沒有一個晚上﹐他們能夠靜靜地在黑暗裡沉入夢鄉。
也許﹐上帝以為﹐這樣的懲罰比較適合罷﹖
想不到過了幾天﹐便知道原來OJ SIMPSON準備出書。書裡面寫的是﹐他如何把自己妻子和她的朋友殺掉。當然﹐他加了這樣很重要的一句CONDITIONAL SENTENCE︰假如我的確做了(IF I WERE THE ONE RESPONSIBLE FOR THE CRIME)。書的名字﹐的確是IF I DID IT。
有書評人經已讀過了這本書。他們的評語是﹕SO DETAILED AND CHILLINGLY REALISTIC - WITH OJ AS THE CENTRAL FIGURE - THAT IT LEAVES NO DOUBT IT IS A CONFESSION OF WHAT REALLY HAPPENED。
OJ也上了電視節目做宣傳。在訪問裡﹐OJ被問及何解會寫道「我一生裡面都沒有見過那樣多血」(I HAVE NEVER SEEN SO MUCH BLOOD IN MY LIFE)。這位美式足球明星回答說﹐我想﹐當殺死了兩個人後﹐沒有人能夠不滿身鮮血。
我想﹐他是開始崩潰了。始終﹐他都不是一個鐵人。
當大家以為辯論已經落幕的時候﹐原來新的一輪才剛剛開始。
究竟他是不是就是那個兇手呢﹖
Monday, November 20, 2006
我趕上了星期天最後一班開往都柏林的快車。
當然能夠趕得上﹐因為四時多我便已來到了貝爾法斯特的中央火車站﹐而火車倒是在五點半才在月臺開出。
確實曾經想過早一點到火車站等候。因為都沒有劃位。我怕所有HOLIDAY MAKERS都爭相乘搭這一班快車。假如由於沒有位子而上不了車﹐原來兩個鐘頭的車程便要多加一個小時。我實在很不願意乘搭那一班八時半在北愛爾蘭首府開出的那一班普通慢車。不過﹐可沒有想過早一句鐘有多開始候車。只是﹐天氣實在太惡劣﹐根本不能再到什麼地方逛逛。到火車站的咖啡店﹐一邊喝著熱朱古力﹐一邊翻閱著小說﹐似乎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冬天的確不是到英國﹑愛爾蘭等地方旅遊的季節。當然﹐假如你喜歡在凜冽寒風暴雨下在街外漫遊﹐那另作別論。
在貝爾法斯特的兩天兩夜裡﹐伴隨我們的﹐除了是陰霾密雲的天空外﹐便是狂風和大雨。我不知道英國本土的情形。不過﹐我知道﹐這是愛爾蘭傳統的冬天天氣。也許﹐在溫室效應下﹐全球氣候是出現了許多變化﹐只是這個島嶼的冬季依然未有受到很大影響。
我們是為了一遊GIANT'S CAUSEWAY,方來到貝爾法斯特。
GIANT'S CAUSEWAY是世界八大奇觀之一。那是在北愛爾蘭北面的石柱。是愛爾蘭島上最接近北極的一個地方。在動蕩的時候﹐遊客冒著生命危險還要到北愛爾蘭遊覽﹐為的便是要看看這些海岸線上﹐由熔岩冷卻而成的一條條岩石柱體。
我們乘八時十五分的火車﹐從貝爾法斯特到COLERAINE,然後再轉搭巴士到GIANT'S CAUSEWAY。到達目的地也差不多是中午的時候。我們知道天空三﹑四點便開始變黑﹐所以抓緊了時間﹐先去了解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後有空才再理會生理上的需要。
這是我首次如此接近愛爾蘭的自然海岸線。
因為長年累月受著海濤的衝擊磨洗﹐那些岩石柱體的表面都很光滑。在天雨底下﹐在強風之下﹐爬上那些石柱的確有點難度。對女孩子來說﹐更加是一項挑戰。因為柱體和柱體的高差﹐可以超過半米﹐而每條柱體的切面﹐僅僅是一隻腳的大小。
經過多年的研究﹐對於這些佈滿愛爾蘭海岸線上面﹐或五角﹑或六角﹑或八角﹑以至十角的多邊形柱體﹐地質學家是有了一套科學的解釋。不過﹐我喜歡的﹐還是那個傳統的愛爾蘭故事。他們說﹐愛爾蘭的那個巨人為了跟住在蘇格蘭的愛人見面﹐於是便從山上搬來一條一條的石柱﹐在海上面興建起一條路﹐接駁愛爾蘭和蘇格蘭。GIANT'S CAUSEWAY的名字便是由此而來。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這條石路的遺跡。當然﹐蘇格蘭西岸也有這樣的石柱。
從那些岩石柱體走回旅客中心的時候﹐我們發覺手指都有點不聽使。都變得很僵硬。迎面而來的雨點﹐都像一塊塊冰雹。在冰冷的氣溫底下﹐腦海裡想像得到的便只有熱騰騰的食物和飲料。
或者﹐夏天的時候﹐到GIANT'S CAUSEWAY攀爬那些石柱﹐會是另外一番光景。至少﹐會比較容易。不過﹐在冬天的時候來到這兒遊覽﹐也不是一個差的選擇。在惡劣的天氣底下﹐你是更能體驗大自然的神奇。在凜冽寒風暴雨下﹐在接近零度的空氣裡﹐攀到那些石柱上面﹐遠眺那廣闊神秘的北冰洋﹐縱然不大好受﹐也依然很值得。因為都沒有很多遊客。況且﹐想到之後可以到附近那間叫NOOK的酒館﹐圍著火爐﹐喝著一杯熱朱古力﹐享受著愛爾蘭的傳統食物﹐一切原來又不是太很困難。
當然能夠趕得上﹐因為四時多我便已來到了貝爾法斯特的中央火車站﹐而火車倒是在五點半才在月臺開出。
確實曾經想過早一點到火車站等候。因為都沒有劃位。我怕所有HOLIDAY MAKERS都爭相乘搭這一班快車。假如由於沒有位子而上不了車﹐原來兩個鐘頭的車程便要多加一個小時。我實在很不願意乘搭那一班八時半在北愛爾蘭首府開出的那一班普通慢車。不過﹐可沒有想過早一句鐘有多開始候車。只是﹐天氣實在太惡劣﹐根本不能再到什麼地方逛逛。到火車站的咖啡店﹐一邊喝著熱朱古力﹐一邊翻閱著小說﹐似乎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冬天的確不是到英國﹑愛爾蘭等地方旅遊的季節。當然﹐假如你喜歡在凜冽寒風暴雨下在街外漫遊﹐那另作別論。
在貝爾法斯特的兩天兩夜裡﹐伴隨我們的﹐除了是陰霾密雲的天空外﹐便是狂風和大雨。我不知道英國本土的情形。不過﹐我知道﹐這是愛爾蘭傳統的冬天天氣。也許﹐在溫室效應下﹐全球氣候是出現了許多變化﹐只是這個島嶼的冬季依然未有受到很大影響。
我們是為了一遊GIANT'S CAUSEWAY,方來到貝爾法斯特。
GIANT'S CAUSEWAY是世界八大奇觀之一。那是在北愛爾蘭北面的石柱。是愛爾蘭島上最接近北極的一個地方。在動蕩的時候﹐遊客冒著生命危險還要到北愛爾蘭遊覽﹐為的便是要看看這些海岸線上﹐由熔岩冷卻而成的一條條岩石柱體。
我們乘八時十五分的火車﹐從貝爾法斯特到COLERAINE,然後再轉搭巴士到GIANT'S CAUSEWAY。到達目的地也差不多是中午的時候。我們知道天空三﹑四點便開始變黑﹐所以抓緊了時間﹐先去了解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後有空才再理會生理上的需要。
這是我首次如此接近愛爾蘭的自然海岸線。
因為長年累月受著海濤的衝擊磨洗﹐那些岩石柱體的表面都很光滑。在天雨底下﹐在強風之下﹐爬上那些石柱的確有點難度。對女孩子來說﹐更加是一項挑戰。因為柱體和柱體的高差﹐可以超過半米﹐而每條柱體的切面﹐僅僅是一隻腳的大小。
經過多年的研究﹐對於這些佈滿愛爾蘭海岸線上面﹐或五角﹑或六角﹑或八角﹑以至十角的多邊形柱體﹐地質學家是有了一套科學的解釋。不過﹐我喜歡的﹐還是那個傳統的愛爾蘭故事。他們說﹐愛爾蘭的那個巨人為了跟住在蘇格蘭的愛人見面﹐於是便從山上搬來一條一條的石柱﹐在海上面興建起一條路﹐接駁愛爾蘭和蘇格蘭。GIANT'S CAUSEWAY的名字便是由此而來。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這條石路的遺跡。當然﹐蘇格蘭西岸也有這樣的石柱。
從那些岩石柱體走回旅客中心的時候﹐我們發覺手指都有點不聽使。都變得很僵硬。迎面而來的雨點﹐都像一塊塊冰雹。在冰冷的氣溫底下﹐腦海裡想像得到的便只有熱騰騰的食物和飲料。
或者﹐夏天的時候﹐到GIANT'S CAUSEWAY攀爬那些石柱﹐會是另外一番光景。至少﹐會比較容易。不過﹐在冬天的時候來到這兒遊覽﹐也不是一個差的選擇。在惡劣的天氣底下﹐你是更能體驗大自然的神奇。在凜冽寒風暴雨下﹐在接近零度的空氣裡﹐攀到那些石柱上面﹐遠眺那廣闊神秘的北冰洋﹐縱然不大好受﹐也依然很值得。因為都沒有很多遊客。況且﹐想到之後可以到附近那間叫NOOK的酒館﹐圍著火爐﹐喝著一杯熱朱古力﹐享受著愛爾蘭的傳統食物﹐一切原來又不是太很困難。
Friday, November 17, 2006
每天上班﹐我都會在火車站買份倫敦時報上車。
首先讀的﹐當然是體育版。然後﹐便由頭版開始翻閱下去。我的閱讀速度很慢﹐半小時的車程當然未能啃完整份報紙﹐唯有下班的時候繼續。那時候﹐我會從象棋那一版開始讀起。經過了一天的辛勞﹐我想找點樂趣﹐娛樂一下自己。
經過了一個月來的訓練﹐我開始解答得到那些WINNING MOVE的難題﹐我開始不用看答案也找到尾局取勝的方法。果然﹐PRACTICE MAKES PERFECT。當然﹐我也不排除﹐可能是最近的問題比較容易。
象棋專欄旁﹐是ANNIVERSARY SECTION,類似當年今日。
最近﹐我發覺﹐很多歷史名人都是在十一月出生。尤其十一月七日。
也許﹐你會覺得我有語病。因為每一個月都有很多歷史名人出生﹐只在乎如何替「歷史名人」這個詞語下註腳。
我以為﹐這一個月是很多歷史名人的生辰。因為我都認識他們。至少﹐我這樣無知﹐也聽過他們的名字。他們不可能不是歷史的名人。都是鼎鼎大名的人。
原來﹐居里夫人就是在十一月七日出生。那是1867年的事情。十二年後﹐便到俄國革命領袖托斯基(LEON TROTSKY)來到人間。人家說什麼托派﹐指的便是TROTSKY的思想。再三十四年後﹐在非洲黑色的土地上面﹐人們迎接了大文豪卡謬的誕生。《異鄉人》這部小說﹐便是沒有讀過﹐也不可能沒有聽過。
我經常說﹐愛爾蘭孕育了不少出色的作家。JAMES JOYCE、BERNARD SHAW、OSCAR WILDE等等都是我常掛在口邊的名字。也許﹐你對BRAM STOKER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不過﹐他的一個小說角色﹐你一定認識。那個角色的名字叫德古拉伯爵。羅馬尼亞也是因為這一個角色﹐賺了不少旅客的金錢。MR STOKER便是1847年11月8日在都柏林出生。
還有一個我喜歡的作家在這一個月來到世界。那是俄國小說家屠格涅夫。他比居里夫人大五歲。我記得﹐是董橋介紹他給我認識。董橋說﹐《初戀》裡面的文字﹐就像初戀一樣清純。那是父與子愛上了同一個女生的故事。中學的時候﹐中文書裡面有一篇翻譯文章﹐名叫少年筆耕。那便是屠格涅夫的作品。他在十一月九日出生。
啊﹗竟然也是十一月的第九天。屠格涅夫竟然也是在那天出生。二十六年前﹐其中一個在我生命裡很重要的女孩﹐便是在那天跑到來這個世界﹐跟我見面。
陶傑說﹐「十一月是很個人很私隱的月份,有一絲淡淡的哀愁,但因為聖誕和新年也近了,也充滿一腔甜濃的期待。十一月出生的男人,曖昧而低調,隱秘得有點迷人,屬於天蠍座,在季節和曆法之間,隱隱有一點道理。」
對於這個說法﹐我無從稽考。不過﹐看看身邊的朋友﹐我不知道我是否很敢認同。
註﹕筆者外遊貝爾法斯特關係﹐此專欄將暫停兩天。星期一再續。希望大家見諒。
首先讀的﹐當然是體育版。然後﹐便由頭版開始翻閱下去。我的閱讀速度很慢﹐半小時的車程當然未能啃完整份報紙﹐唯有下班的時候繼續。那時候﹐我會從象棋那一版開始讀起。經過了一天的辛勞﹐我想找點樂趣﹐娛樂一下自己。
經過了一個月來的訓練﹐我開始解答得到那些WINNING MOVE的難題﹐我開始不用看答案也找到尾局取勝的方法。果然﹐PRACTICE MAKES PERFECT。當然﹐我也不排除﹐可能是最近的問題比較容易。
象棋專欄旁﹐是ANNIVERSARY SECTION,類似當年今日。
最近﹐我發覺﹐很多歷史名人都是在十一月出生。尤其十一月七日。
也許﹐你會覺得我有語病。因為每一個月都有很多歷史名人出生﹐只在乎如何替「歷史名人」這個詞語下註腳。
我以為﹐這一個月是很多歷史名人的生辰。因為我都認識他們。至少﹐我這樣無知﹐也聽過他們的名字。他們不可能不是歷史的名人。都是鼎鼎大名的人。
原來﹐居里夫人就是在十一月七日出生。那是1867年的事情。十二年後﹐便到俄國革命領袖托斯基(LEON TROTSKY)來到人間。人家說什麼托派﹐指的便是TROTSKY的思想。再三十四年後﹐在非洲黑色的土地上面﹐人們迎接了大文豪卡謬的誕生。《異鄉人》這部小說﹐便是沒有讀過﹐也不可能沒有聽過。
我經常說﹐愛爾蘭孕育了不少出色的作家。JAMES JOYCE、BERNARD SHAW、OSCAR WILDE等等都是我常掛在口邊的名字。也許﹐你對BRAM STOKER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不過﹐他的一個小說角色﹐你一定認識。那個角色的名字叫德古拉伯爵。羅馬尼亞也是因為這一個角色﹐賺了不少旅客的金錢。MR STOKER便是1847年11月8日在都柏林出生。
還有一個我喜歡的作家在這一個月來到世界。那是俄國小說家屠格涅夫。他比居里夫人大五歲。我記得﹐是董橋介紹他給我認識。董橋說﹐《初戀》裡面的文字﹐就像初戀一樣清純。那是父與子愛上了同一個女生的故事。中學的時候﹐中文書裡面有一篇翻譯文章﹐名叫少年筆耕。那便是屠格涅夫的作品。他在十一月九日出生。
啊﹗竟然也是十一月的第九天。屠格涅夫竟然也是在那天出生。二十六年前﹐其中一個在我生命裡很重要的女孩﹐便是在那天跑到來這個世界﹐跟我見面。
陶傑說﹐「十一月是很個人很私隱的月份,有一絲淡淡的哀愁,但因為聖誕和新年也近了,也充滿一腔甜濃的期待。十一月出生的男人,曖昧而低調,隱秘得有點迷人,屬於天蠍座,在季節和曆法之間,隱隱有一點道理。」
對於這個說法﹐我無從稽考。不過﹐看看身邊的朋友﹐我不知道我是否很敢認同。
註﹕筆者外遊貝爾法斯特關係﹐此專欄將暫停兩天。星期一再續。希望大家見諒。
Thursday, November 16, 2006
才講了不夠兩個星期﹐不幸地﹐我的胡言亂語竟然得到了證實。
兩天前﹐陶傑在《黃金冒險號》裡面說﹕
天星碼頭要搬遷﹐舊鐘樓要拆掉﹐許多人捨不得。記者問起心情,都說覺得「很無奈」。什麼叫做「很無奈」?這是弱者的反應。這是弱者的心聲。從沙士死了三百人,高官不必負責;沒得普選,每一屆的特首候選人只有一名,到地鐵誤點十五分鐘,上班延誤,事無大小,電台訪問市民,都說「好無奈」。於是﹐「覺得好無奈咯,我ED小市民,可以做到咩唧?」,成為了二零零六年許多「危機 」的標準Sound-bite。
我想﹐這就是龍應臺《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的香港變奏。
那是《野火集》的首篇文章。原文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中國時報副刊人間刊載。裡面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在台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壞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睛﹐假裝睡眠。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社會裡﹐人是有權利生氣的。受折磨的你首先應該雙手插腰﹐很憤怒地對那些霸佔你騎樓的攤販說﹐請你滾蛋﹗他們不走﹐就請警察來。若發覺警察與小販有勾結﹐這一團怒火更應該往上燒﹐燒到警察肅清紀律為止﹐燒到攤販離開你家為止。
同年十二月六日﹐龍應臺再次投稿人間副刊。文章名字叫《生氣﹐沒有用嗎﹖》。
她說﹕寫過《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之後﹐有些人帶著憐憫的眼光﹐搖著頭對我說﹐生氣﹐沒有用的﹗算了罷﹗
這不正正等於「覺得好無奈咯,我ED小市民,可以做到咩唧」﹖
陶傑說﹕如果如此愛惜這幢「古蹟」,只要有十萬人圍在舊鐘樓前面,變成國際新聞,香港政府是不敢把舊鐘樓強行拆掉的。因為曾蔭權爵士會在最後一分鐘「贏盡民意」。龍應臺也說﹕如果打電話到環保局的不只我一個﹐而是一天有兩白通電話﹑三百封信﹐你說環保局還能支吾其事嗎﹖如果對分局局長抗議的不只我一個﹐而是每一個不甘心受氣的市民﹐他還能執迷不悟地說「中國國情如此」嗎﹖
的確﹐對於一切不公正的行為,人人都止於「無奈」,這個世界就會陷入黑暗時代。集體「無奈」是沒有用的,只會延續一個民族的痛苦和悲哀。因為你不生氣﹑你忍耐﹑你退讓﹐所以攤販把你的家搞得像個破落大雜院﹐所以市內交通一團烏煙瘴氣﹐所以河流是條爛腸子。今天﹐你不生氣﹐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我並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我只是希望你不再迷信逆來順受。
從來﹐我都以為﹐縱然龍應臺寫的都是發生在台灣的事情﹐只是把文章裡面的「台灣」改為「香港」﹐以至「中國」﹐也一樣合適。也許﹐因為台灣﹑香港與中國﹐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
不過﹐可不好忘記﹐那是二十有二年前的文章。二十年過去了﹐那些文章竟然依舊很有見地﹐依然適用現今社會狀況。你還感到無奈嗎﹖
今天﹐讀這個專欄﹐發現我左抄右貼﹐你便應該要很憤怒﹗
兩天前﹐陶傑在《黃金冒險號》裡面說﹕
天星碼頭要搬遷﹐舊鐘樓要拆掉﹐許多人捨不得。記者問起心情,都說覺得「很無奈」。什麼叫做「很無奈」?這是弱者的反應。這是弱者的心聲。從沙士死了三百人,高官不必負責;沒得普選,每一屆的特首候選人只有一名,到地鐵誤點十五分鐘,上班延誤,事無大小,電台訪問市民,都說「好無奈」。於是﹐「覺得好無奈咯,我ED小市民,可以做到咩唧?」,成為了二零零六年許多「危機 」的標準Sound-bite。
我想﹐這就是龍應臺《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的香港變奏。
那是《野火集》的首篇文章。原文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中國時報副刊人間刊載。裡面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在台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壞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睛﹐假裝睡眠。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社會裡﹐人是有權利生氣的。受折磨的你首先應該雙手插腰﹐很憤怒地對那些霸佔你騎樓的攤販說﹐請你滾蛋﹗他們不走﹐就請警察來。若發覺警察與小販有勾結﹐這一團怒火更應該往上燒﹐燒到警察肅清紀律為止﹐燒到攤販離開你家為止。
同年十二月六日﹐龍應臺再次投稿人間副刊。文章名字叫《生氣﹐沒有用嗎﹖》。
她說﹕寫過《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之後﹐有些人帶著憐憫的眼光﹐搖著頭對我說﹐生氣﹐沒有用的﹗算了罷﹗
這不正正等於「覺得好無奈咯,我ED小市民,可以做到咩唧」﹖
陶傑說﹕如果如此愛惜這幢「古蹟」,只要有十萬人圍在舊鐘樓前面,變成國際新聞,香港政府是不敢把舊鐘樓強行拆掉的。因為曾蔭權爵士會在最後一分鐘「贏盡民意」。龍應臺也說﹕如果打電話到環保局的不只我一個﹐而是一天有兩白通電話﹑三百封信﹐你說環保局還能支吾其事嗎﹖如果對分局局長抗議的不只我一個﹐而是每一個不甘心受氣的市民﹐他還能執迷不悟地說「中國國情如此」嗎﹖
的確﹐對於一切不公正的行為,人人都止於「無奈」,這個世界就會陷入黑暗時代。集體「無奈」是沒有用的,只會延續一個民族的痛苦和悲哀。因為你不生氣﹑你忍耐﹑你退讓﹐所以攤販把你的家搞得像個破落大雜院﹐所以市內交通一團烏煙瘴氣﹐所以河流是條爛腸子。今天﹐你不生氣﹐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我並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我只是希望你不再迷信逆來順受。
從來﹐我都以為﹐縱然龍應臺寫的都是發生在台灣的事情﹐只是把文章裡面的「台灣」改為「香港」﹐以至「中國」﹐也一樣合適。也許﹐因為台灣﹑香港與中國﹐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
不過﹐可不好忘記﹐那是二十有二年前的文章。二十年過去了﹐那些文章竟然依舊很有見地﹐依然適用現今社會狀況。你還感到無奈嗎﹖
今天﹐讀這個專欄﹐發現我左抄右貼﹐你便應該要很憤怒﹗
Wednesday, November 15, 2006
很久以前﹐也許還是明報的時候﹐陶傑在《黃金冒險號》裡寫過這樣的一段文字﹕
「天星小輪創業白年﹐從前由一個波斯人興辦的小輪公司﹐今天發展成香港旅遊事業的一個歷史標記。綠白相間的船身﹐穿梭在風波千檣的維多利亞港﹐尖沙嘴的舊鐘樓在騰起的華廈間憔悴﹐中環大會堂也在玻璃幕牆中矮下去﹐唯有天星本色不變的輪隊﹐滿載著一世紀的雲水。」
的確﹐不變的只有天星小輪的船隊。
偶然到了YAHOO﹗的香港網頁瀏覽。失落地發現﹐原來中環的天星碼頭經已停止使用。聽說﹐碼頭的一切都會給移平﹐那地方又將會變成高矗的商業大廈。
預計到會有很多人﹐都想搭最後一班從那個碼頭開出的小輪。於是﹐有人辦了一個慈善活動﹐把最後幾班小輪船票的收入捐給慈善團體。希望藉此既做善事﹐也好使善忘的香港人集體地來一次歷史回憶。網頁說﹐慈善乘搭小輪的票早就售罄。不單只是最後的那一班﹐便是早幾班的小輪也很早滿了座。我不知道﹐那是香港人的善心﹐還是他們很想重溫以往光輝的日子﹖
關門前的幾天﹐也有很多人爭相趕往碼頭拍照留念。他們說﹐天星碼頭帶給他們太多美好的回憶。
天星碼頭的確是香港歷史的最好見證。
在波濤衝擊下﹐它看著香港的每天變化。從小小的漁港﹐變成一個輕工業的重鎮﹔從繁忙的轉口港﹐起飛到國際金融中心﹔從自強不息的英國殖民地﹐淪為紅色中國的經濟奴隸。
其實﹐不難明白為何特區政府要努力地﹐把一幢又一幢的歷史建築拆掉。不是因為他們不尊重歷史﹐也不是因為他們太輕視舊時發生的一切。相反﹐便是因為他們太把歷史看重﹐便是因為他們太重視以前的所有事情﹐所以都要把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毀滅。政府要我們都拋掉舊時繁盛的包袱﹐要我們都跟以往花樣的年華講聲再見。沒有了那些集體回憶﹐我們最終會忘卻以往那些好日子。沒有了那些歷史見證﹐我們將無從跟過往比較。情形跟北京看待天安門大屠殺相似﹕讓人民慢慢把事情忘掉。
始終﹐做奴才的都要按著主子辦事的方法做事。
誰說﹐那時候﹐我們不乞求別人﹐不望阿公打救﹐只是咬著牙關﹐努力不懈﹐渡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誰說﹐那時候﹐我們就是國際大都會﹑世界金融中心﹖都是道聽途說罷。從來沒有那些事情。你看﹐我們不是從零三年的谷底﹐每年在爬升了嗎﹖我們是越來越好﹐越來越繁榮啊﹗我們開始跟國際接上了軌。
為了有這樣的一天﹐因此﹐實在很有必要把所有見證過香港繁榮的歷史建築一一拆掉。
我想﹐在海運大廈附近那幾幢商業樓宇改建完畢後﹐也就是我們跟尖沙嘴天星碼頭說再見的時候。
當我返回香港的時候﹐究竟那還是不是我的香港﹖她也許還能認得到我﹐只是我還能夠認得出她嗎﹖
「天星小輪創業白年﹐從前由一個波斯人興辦的小輪公司﹐今天發展成香港旅遊事業的一個歷史標記。綠白相間的船身﹐穿梭在風波千檣的維多利亞港﹐尖沙嘴的舊鐘樓在騰起的華廈間憔悴﹐中環大會堂也在玻璃幕牆中矮下去﹐唯有天星本色不變的輪隊﹐滿載著一世紀的雲水。」
的確﹐不變的只有天星小輪的船隊。
偶然到了YAHOO﹗的香港網頁瀏覽。失落地發現﹐原來中環的天星碼頭經已停止使用。聽說﹐碼頭的一切都會給移平﹐那地方又將會變成高矗的商業大廈。
預計到會有很多人﹐都想搭最後一班從那個碼頭開出的小輪。於是﹐有人辦了一個慈善活動﹐把最後幾班小輪船票的收入捐給慈善團體。希望藉此既做善事﹐也好使善忘的香港人集體地來一次歷史回憶。網頁說﹐慈善乘搭小輪的票早就售罄。不單只是最後的那一班﹐便是早幾班的小輪也很早滿了座。我不知道﹐那是香港人的善心﹐還是他們很想重溫以往光輝的日子﹖
關門前的幾天﹐也有很多人爭相趕往碼頭拍照留念。他們說﹐天星碼頭帶給他們太多美好的回憶。
天星碼頭的確是香港歷史的最好見證。
在波濤衝擊下﹐它看著香港的每天變化。從小小的漁港﹐變成一個輕工業的重鎮﹔從繁忙的轉口港﹐起飛到國際金融中心﹔從自強不息的英國殖民地﹐淪為紅色中國的經濟奴隸。
其實﹐不難明白為何特區政府要努力地﹐把一幢又一幢的歷史建築拆掉。不是因為他們不尊重歷史﹐也不是因為他們太輕視舊時發生的一切。相反﹐便是因為他們太把歷史看重﹐便是因為他們太重視以前的所有事情﹐所以都要把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毀滅。政府要我們都拋掉舊時繁盛的包袱﹐要我們都跟以往花樣的年華講聲再見。沒有了那些集體回憶﹐我們最終會忘卻以往那些好日子。沒有了那些歷史見證﹐我們將無從跟過往比較。情形跟北京看待天安門大屠殺相似﹕讓人民慢慢把事情忘掉。
始終﹐做奴才的都要按著主子辦事的方法做事。
誰說﹐那時候﹐我們不乞求別人﹐不望阿公打救﹐只是咬著牙關﹐努力不懈﹐渡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誰說﹐那時候﹐我們就是國際大都會﹑世界金融中心﹖都是道聽途說罷。從來沒有那些事情。你看﹐我們不是從零三年的谷底﹐每年在爬升了嗎﹖我們是越來越好﹐越來越繁榮啊﹗我們開始跟國際接上了軌。
為了有這樣的一天﹐因此﹐實在很有必要把所有見證過香港繁榮的歷史建築一一拆掉。
我想﹐在海運大廈附近那幾幢商業樓宇改建完畢後﹐也就是我們跟尖沙嘴天星碼頭說再見的時候。
當我返回香港的時候﹐究竟那還是不是我的香港﹖她也許還能認得到我﹐只是我還能夠認得出她嗎﹖
Tuesday, November 14, 2006
因為旅行在即﹐MARIA顯得很是興奮。
有些事情找她商量。才來到她的座位﹐便看到了她滿面笑容﹐精神煥發。早幾天﹐因為患上重感冒﹐她還一臉倦容﹐不時在公司刷鼻子。放了病假一天﹐依然未有完全痊癒﹐說話仍然帶著很重的鼻音。也許﹐旅行的確是很好的藥方。只要想到旅行﹐人便會不其然地興奮起來。一興奮﹐就百病不侵﹐有病自癒。
我問﹐很期待下班的鐘聲罷﹖
小妮子點著頭笑道﹐實在不能夠不興奮。都很好天﹐馬德里連續三天都是大晴天。
還未待我再開口﹐她便領我到了天文臺的網頁。在熒光屏上﹐我看到﹐除了這個週末和星期一外﹐所有日子都是黑雲有雨。我笑著說﹐你是偷走了愛爾蘭的陽光去罷﹖我記得﹐天氣預告說﹐這個週末﹐都柏林多雲間中有雨。
MARIA問﹐這個週末你也是留在DUBLIN嗎﹖
還能到哪兒去﹖
可以到GALWAY去啊﹗GALWAY是愛爾蘭西邊的一個漁港﹐盛產生蠔。
我記得﹐她和AOIFE多次向我提及愛爾蘭其他地方。她們說﹐到愛爾蘭不能不到郊外。因為到過郊外的地方﹐才能真正領略愛爾蘭的真面目。MAIRA甚至說﹐愛爾蘭就是大自然。她們是分不開﹐也不應該給分開。上次往CO WICKLOW開會途中﹐她倆便曾給我介紹過WICKLOW MOUNTAIN。印象中﹐詩人THOMAS MOORE好像這樣說過﹐THERE IS NOT IN THE WIDE WORLD A VALLEY SO SWEET AS THAT VALE IN WHOSE BOSOM THE BRIGHT WATERS MEET。
下班後﹐跟ADRIAN去了飲酒吃晚飯。
幾PINT下肚﹐我跟他講到小妮子的提議。
他回應道﹐也要等明年春天罷﹖我想﹐這樣的天氣不太適合到郊外去。
我同意他的看法。因為便是在市中心﹐冷風也刮得很猛﹑很大。想像不到空曠的郊外會是什麼樣的情形。
不過﹐我更有另外一個看法。
我才在這兒住上了半年﹐實在不想太快便把整個愛爾蘭島嶼遊過一遍。我要繼續讓自己對這兒的一切充滿好奇。正如家裡現存的DVD碟,我都未有完整地看過任何一部電影﹐以至一套電視劇。因為我不想還能夠在生活裡找到樂趣的時候﹐提早把那些DVD碟看畢一次。我要把它們留到往後的日子。我記得﹐有朋友跟我說過﹐獨自一人在外地生活﹐不能撐得很久。起初的時候﹐的確如同旅行一樣。那是WORKING HOLIDAY的另一個版本。過了一年之後﹐當一切開始自我重覆﹐你將會感到寂寞難受。因為你已對身邊所有事情沒有好奇﹐因為所有事情對你都已沒有新意。
所以﹐在我還能夠愉快地在都柏林渡過週末的時候﹐我實在不想到愛爾蘭的其他郡去。我不想一切太快地變得了無新意。
況且﹐還有那個心照不宣的原因。都心照不宣罷。
於是﹐週末放假的日子﹐我不選擇留在都柏林﹐還能到哪兒去﹖
有些事情找她商量。才來到她的座位﹐便看到了她滿面笑容﹐精神煥發。早幾天﹐因為患上重感冒﹐她還一臉倦容﹐不時在公司刷鼻子。放了病假一天﹐依然未有完全痊癒﹐說話仍然帶著很重的鼻音。也許﹐旅行的確是很好的藥方。只要想到旅行﹐人便會不其然地興奮起來。一興奮﹐就百病不侵﹐有病自癒。
我問﹐很期待下班的鐘聲罷﹖
小妮子點著頭笑道﹐實在不能夠不興奮。都很好天﹐馬德里連續三天都是大晴天。
還未待我再開口﹐她便領我到了天文臺的網頁。在熒光屏上﹐我看到﹐除了這個週末和星期一外﹐所有日子都是黑雲有雨。我笑著說﹐你是偷走了愛爾蘭的陽光去罷﹖我記得﹐天氣預告說﹐這個週末﹐都柏林多雲間中有雨。
MARIA問﹐這個週末你也是留在DUBLIN嗎﹖
還能到哪兒去﹖
可以到GALWAY去啊﹗GALWAY是愛爾蘭西邊的一個漁港﹐盛產生蠔。
我記得﹐她和AOIFE多次向我提及愛爾蘭其他地方。她們說﹐到愛爾蘭不能不到郊外。因為到過郊外的地方﹐才能真正領略愛爾蘭的真面目。MAIRA甚至說﹐愛爾蘭就是大自然。她們是分不開﹐也不應該給分開。上次往CO WICKLOW開會途中﹐她倆便曾給我介紹過WICKLOW MOUNTAIN。印象中﹐詩人THOMAS MOORE好像這樣說過﹐THERE IS NOT IN THE WIDE WORLD A VALLEY SO SWEET AS THAT VALE IN WHOSE BOSOM THE BRIGHT WATERS MEET。
下班後﹐跟ADRIAN去了飲酒吃晚飯。
幾PINT下肚﹐我跟他講到小妮子的提議。
他回應道﹐也要等明年春天罷﹖我想﹐這樣的天氣不太適合到郊外去。
我同意他的看法。因為便是在市中心﹐冷風也刮得很猛﹑很大。想像不到空曠的郊外會是什麼樣的情形。
不過﹐我更有另外一個看法。
我才在這兒住上了半年﹐實在不想太快便把整個愛爾蘭島嶼遊過一遍。我要繼續讓自己對這兒的一切充滿好奇。正如家裡現存的DVD碟,我都未有完整地看過任何一部電影﹐以至一套電視劇。因為我不想還能夠在生活裡找到樂趣的時候﹐提早把那些DVD碟看畢一次。我要把它們留到往後的日子。我記得﹐有朋友跟我說過﹐獨自一人在外地生活﹐不能撐得很久。起初的時候﹐的確如同旅行一樣。那是WORKING HOLIDAY的另一個版本。過了一年之後﹐當一切開始自我重覆﹐你將會感到寂寞難受。因為你已對身邊所有事情沒有好奇﹐因為所有事情對你都已沒有新意。
所以﹐在我還能夠愉快地在都柏林渡過週末的時候﹐我實在不想到愛爾蘭的其他郡去。我不想一切太快地變得了無新意。
況且﹐還有那個心照不宣的原因。都心照不宣罷。
於是﹐週末放假的日子﹐我不選擇留在都柏林﹐還能到哪兒去﹖
Monday, November 13, 2006
早陣子﹐有朋友寫信來告訴我﹐電影THE PRESTIGE實在很好看﹐叫我不容錯過。她說﹐那是今年度她最喜歡的一部。我相信她的介紹﹐因為我知道她的口味。她喜歡的﹐我應該都會歡喜。於是﹐當電影上映後﹐我便急不及待買票入場觀看。
果然很吸引﹗
我常發覺﹐帶著很高期望到電影院去﹐走出來的時候都只有一堆又一堆的失望。我想﹐你應該都會有同樣感覺。也許﹐是因為我們都會不其然地﹐把別人以為最好的﹐再無限倍地伸張到不設實際的境地。所以﹐我曾經很希望報章對這部電影的評價都只是一般﹐好使能夠壓抑到自己的無謂想像。我不想後悔地離開戲院﹐我不想告訴她﹐電影沒有想像中吸引。因為我知道﹐她將會很失望。當然﹐我可以假裝很喜歡這部電影﹐只是我想不到原因為何要弄假。
不過﹐走出電影院的時候﹐我知道THE PRESTIGE是一個例外。
今次﹐我沒有選擇錯誤。雖然是沒有太多選擇。因為這個時候﹐是聖誕前的一個月﹐的確沒有什麼很吸引人的電影。
跟上星期一樣﹐我又做了一隻早起的鳥兒。
跟上星期不一樣﹐我是意外地早起了。便查看一下﹐究竟電影院有沒有安排早場。果然給我發現了一場十時零五分。我看還有一個多小時。於是﹐梳洗完畢﹐吃過早餐﹐方施施然走向戲院。況且﹐我知道﹐十時零五分是開始播放廣告的時間。之後﹐還有一堆預告片。最早也要十時二十分才是正場。
劇本的確很用心經營。每一幕都跟電影裡的其他每一幕﹐都互相緊扣著。片長兩個多小時﹐只是少了任何一幕都會使到電影大為失色。因為那電影的張力會因此消失﹐會完全凝聚不到觀眾的投入氣氛。除了BATMAN BEGINS外﹐導演CHRISTOPHER NOLAN的前作MEMENTO與INSOMNIA,我都看過。THE PRESTIGE是最得我心的一部。
故事實在很引人入勝。從來﹐我都很喜歡雙雄鬥法的故事。在這傳統的架構裡面﹐編劇是花了心思把它包裝得很峰迴路轉。未到最後一刻也不知道誰勝﹑誰負。(其實﹐電影改編CHRISTOPHER PRIEST的同名小說。)於是﹐那一百三十分鐘便像流水般地﹐很快便過去了。
來到愛爾蘭後﹐我也看了不下十部電影。我想﹐THE PRESTIGE是我喜歡的其中一部。僅次於THE QUEEN罷。跟VOLVER不分上下。
曾經﹐我以為﹐看電影是一個人的事情﹐可是到電影院卻是兩個人的事。至今﹐我依然如此想法。
只是﹐奈何實在沒有太多早起的鳥兒。
看著大熒幕上的ROBERT ANGIER,忽然發覺原來你也曉得TRANSPORTED MAN的秘密。
在電影院裡﹐我好像看到了你的複製來到。
果然很吸引﹗
我常發覺﹐帶著很高期望到電影院去﹐走出來的時候都只有一堆又一堆的失望。我想﹐你應該都會有同樣感覺。也許﹐是因為我們都會不其然地﹐把別人以為最好的﹐再無限倍地伸張到不設實際的境地。所以﹐我曾經很希望報章對這部電影的評價都只是一般﹐好使能夠壓抑到自己的無謂想像。我不想後悔地離開戲院﹐我不想告訴她﹐電影沒有想像中吸引。因為我知道﹐她將會很失望。當然﹐我可以假裝很喜歡這部電影﹐只是我想不到原因為何要弄假。
不過﹐走出電影院的時候﹐我知道THE PRESTIGE是一個例外。
今次﹐我沒有選擇錯誤。雖然是沒有太多選擇。因為這個時候﹐是聖誕前的一個月﹐的確沒有什麼很吸引人的電影。
跟上星期一樣﹐我又做了一隻早起的鳥兒。
跟上星期不一樣﹐我是意外地早起了。便查看一下﹐究竟電影院有沒有安排早場。果然給我發現了一場十時零五分。我看還有一個多小時。於是﹐梳洗完畢﹐吃過早餐﹐方施施然走向戲院。況且﹐我知道﹐十時零五分是開始播放廣告的時間。之後﹐還有一堆預告片。最早也要十時二十分才是正場。
劇本的確很用心經營。每一幕都跟電影裡的其他每一幕﹐都互相緊扣著。片長兩個多小時﹐只是少了任何一幕都會使到電影大為失色。因為那電影的張力會因此消失﹐會完全凝聚不到觀眾的投入氣氛。除了BATMAN BEGINS外﹐導演CHRISTOPHER NOLAN的前作MEMENTO與INSOMNIA,我都看過。THE PRESTIGE是最得我心的一部。
故事實在很引人入勝。從來﹐我都很喜歡雙雄鬥法的故事。在這傳統的架構裡面﹐編劇是花了心思把它包裝得很峰迴路轉。未到最後一刻也不知道誰勝﹑誰負。(其實﹐電影改編CHRISTOPHER PRIEST的同名小說。)於是﹐那一百三十分鐘便像流水般地﹐很快便過去了。
來到愛爾蘭後﹐我也看了不下十部電影。我想﹐THE PRESTIGE是我喜歡的其中一部。僅次於THE QUEEN罷。跟VOLVER不分上下。
曾經﹐我以為﹐看電影是一個人的事情﹐可是到電影院卻是兩個人的事。至今﹐我依然如此想法。
只是﹐奈何實在沒有太多早起的鳥兒。
看著大熒幕上的ROBERT ANGIER,忽然發覺原來你也曉得TRANSPORTED MAN的秘密。
在電影院裡﹐我好像看到了你的複製來到。
Sunday, November 12, 2006
不知怎地﹐有些說話總能夠永遠藏你的心坎裡面。縱然說話的人不是什麼名人﹐也不是跟你很親密的人。而且﹐更多的時候﹐是你早已記不起究竟是誰跟你說那句話。還記得的﹐只是說話的內容。因為它不時在腦海裡出現。
讀報紙的時候﹐我總時常記起了這句話﹕
「十來二十歲的年青人讀報紙﹐第一版翻到的一定是體育版﹔後來﹐在社會打滾了幾年﹐到了三四十歲﹐首先讀的就是財經版﹔人到老年﹐經已退休享福﹐早上閑來無事﹐最先翻閱的卻是訃聞。」
我時常記起這句話。因為我覺得此言真的不虛。
中學的時候﹐每天的第一堂﹐我都不會怎樣留心上課。因為我正在書檯底下翻閱南華早報的體育版。零三年七一遊行後﹐我開始每天在報攤買一份信報上班。也放棄了SCMP,改投FINANCIAL TIMES的行列。三盤經已兩勝﹐實在不能不驚訝首先講這句話的人的觀察力﹐雖然我是早了點加入財經版。當然﹐那是客觀環境下造成的「早熟」。不計南華早報﹐在我離開香港﹐遠走他方的時候﹐最好的體育版竟然在信報裡面。其他的華文報紙﹐早已放棄了體育版。他們有的是波經。
來到愛爾蘭﹐我每天都在車站﹐買份倫敦時報上火車。我首先讀的是體育版。因為我依然年青。
我曾經「早熟」過﹐知道首先讀財經版的人是什麼心態。不過﹐第一版便翻到訃聞的人究竟心裡想著什麼﹐我真的未能夠體會。
印象中﹐曾經有人解釋過那一句話。他說﹐人到老年﹐首先翻閱訃聞﹐為的便是看看有什麼老友﹐早過自己撒手塵寰﹐也讓自己好好計算一下時間。(當然﹐我也記不起是誰的解釋。)
我想﹐看著一個個老友﹑至愛和親朋﹐早自己一步離開人世﹐心裡一定並不好受。
英國有一份雙週報﹐叫《私眼》(PRIVATE EYE),是一份專挖政治人物劣行﹑諷刺時弊的刊物。
《私眼》是一份很出色的刊物。林行止在英倫采風裡面便屢次提及。陶傑也曾多翻介紹。我記得﹐董橋也是PRIVATE EYE的讀者。似乎﹐只要曾經在英國生活過﹐你便不可能不喜歡這份雙週報。也許﹐因為在香港﹐假如以前沒有辦法辦一份這樣的刊物﹐在沒有普選的將來﹐我們也沒有可能有這樣的一份可愛讀物。
雙週報的創刊編輯英格林(R.INGRAMS)便在這十年來﹐看著一個個老友﹑至愛和親朋離開。他說﹐Now I would have to walk alone. I always depended on being one of a gang, I suppose. Not acting on my own。的確﹐很讓人心酸。
下一個夏天﹐英格林便會過他的第七十個生日。
十年前﹐找他到《私眼》當編輯的雙週報創辦人PETER COOK離開了。接著﹐是雙週報的畫家WILLIE RUSHTON。接下來的三年﹐《私眼》裡面的另外兩個好友JOHN WELLS和AUBERON WAUGH亦先後辭世。兩年前﹐輪到他的同窗PAUL FOOT。便是為英格林寫傳記的HARRY THOMPSON也在去年死掉。當然﹐最難過的莫過於女兒JUBBY的死。2004年﹐她死於過量吸食海洛英。INGRAMS的小兒ARTHUR則在過不了八歲生辰。
面對著接踵而來的死訊﹐難得英格林依然保持幽默。他會笑著說﹐I spend a lot of time thinking about dead people, but that's old age in a way. An awful lot of people you know are dead. I just feel lucky to have known them。
假如有天﹐你比我早一點離開人世﹐我會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曾經跟你認識過。假如有天﹐我比你早一步回歸天國﹑或者走到地獄﹐只盼望你也會FEEL THE SAME。
讀報紙的時候﹐我總時常記起了這句話﹕
「十來二十歲的年青人讀報紙﹐第一版翻到的一定是體育版﹔後來﹐在社會打滾了幾年﹐到了三四十歲﹐首先讀的就是財經版﹔人到老年﹐經已退休享福﹐早上閑來無事﹐最先翻閱的卻是訃聞。」
我時常記起這句話。因為我覺得此言真的不虛。
中學的時候﹐每天的第一堂﹐我都不會怎樣留心上課。因為我正在書檯底下翻閱南華早報的體育版。零三年七一遊行後﹐我開始每天在報攤買一份信報上班。也放棄了SCMP,改投FINANCIAL TIMES的行列。三盤經已兩勝﹐實在不能不驚訝首先講這句話的人的觀察力﹐雖然我是早了點加入財經版。當然﹐那是客觀環境下造成的「早熟」。不計南華早報﹐在我離開香港﹐遠走他方的時候﹐最好的體育版竟然在信報裡面。其他的華文報紙﹐早已放棄了體育版。他們有的是波經。
來到愛爾蘭﹐我每天都在車站﹐買份倫敦時報上火車。我首先讀的是體育版。因為我依然年青。
我曾經「早熟」過﹐知道首先讀財經版的人是什麼心態。不過﹐第一版便翻到訃聞的人究竟心裡想著什麼﹐我真的未能夠體會。
印象中﹐曾經有人解釋過那一句話。他說﹐人到老年﹐首先翻閱訃聞﹐為的便是看看有什麼老友﹐早過自己撒手塵寰﹐也讓自己好好計算一下時間。(當然﹐我也記不起是誰的解釋。)
我想﹐看著一個個老友﹑至愛和親朋﹐早自己一步離開人世﹐心裡一定並不好受。
英國有一份雙週報﹐叫《私眼》(PRIVATE EYE),是一份專挖政治人物劣行﹑諷刺時弊的刊物。
《私眼》是一份很出色的刊物。林行止在英倫采風裡面便屢次提及。陶傑也曾多翻介紹。我記得﹐董橋也是PRIVATE EYE的讀者。似乎﹐只要曾經在英國生活過﹐你便不可能不喜歡這份雙週報。也許﹐因為在香港﹐假如以前沒有辦法辦一份這樣的刊物﹐在沒有普選的將來﹐我們也沒有可能有這樣的一份可愛讀物。
雙週報的創刊編輯英格林(R.INGRAMS)便在這十年來﹐看著一個個老友﹑至愛和親朋離開。他說﹐Now I would have to walk alone. I always depended on being one of a gang, I suppose. Not acting on my own。的確﹐很讓人心酸。
下一個夏天﹐英格林便會過他的第七十個生日。
十年前﹐找他到《私眼》當編輯的雙週報創辦人PETER COOK離開了。接著﹐是雙週報的畫家WILLIE RUSHTON。接下來的三年﹐《私眼》裡面的另外兩個好友JOHN WELLS和AUBERON WAUGH亦先後辭世。兩年前﹐輪到他的同窗PAUL FOOT。便是為英格林寫傳記的HARRY THOMPSON也在去年死掉。當然﹐最難過的莫過於女兒JUBBY的死。2004年﹐她死於過量吸食海洛英。INGRAMS的小兒ARTHUR則在過不了八歲生辰。
面對著接踵而來的死訊﹐難得英格林依然保持幽默。他會笑著說﹐I spend a lot of time thinking about dead people, but that's old age in a way. An awful lot of people you know are dead. I just feel lucky to have known them。
假如有天﹐你比我早一點離開人世﹐我會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曾經跟你認識過。假如有天﹐我比你早一步回歸天國﹑或者走到地獄﹐只盼望你也會FEEL THE SAME。
Saturday, November 11, 2006
去年﹐香港樂壇裡面多了一個不是靠外表走紅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側田。是英文名字JUSTIN的廣東話直接翻譯。今年年初﹐離開香港遠走愛爾蘭的時候﹐他依然很受歡迎。在紅磡體育館開了兩場演唱會。都滿了座。本來﹐我是買了票。只是臨時有重要約會﹐於是未能在現場聽聽他是否唱得比我好。
那時候﹐他剛推出了新的大碟。其實裡面有很多首歌﹐不是互相很相似﹐便是跟他的首張唱片裡面的歌很相似。假如他下一張碟也是如此﹐我想﹐他應該要開始專心多搞一些緋聞。要不﹐他實在不用再想在紅館開演唱會。搞緋聞向來都是PARKO的拿手好戲。不過﹐要側田弄出緋聞﹐的確很高難度。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天才是沒有價值的。沒有人會相信香港娛樂圈裡面的女生﹐會只因為男人的才華而愛上他。無奈﹐很表面地﹐除了才華外﹐側田也沒有什麼﹐可以讓人相信那些女生會愛上他。
側田的第二張唱片裡面﹐我最喜歡的是《走音》。記得有朋友說過﹐喜歡上一首歌﹐很多時候﹐都是因為裡面的歌詞感動了你的每一條神經﹐都是因為歌中的意思竟然對你有點似曾相識。
也許﹐他是對的。
猶記得﹐那幾次的晚飯約會。回頭只見到你﹐對著電話聽語講。
也有一首歌﹐單字一個《運》。裡面有一句是這樣的﹕怎麼叫運﹐視乎你心理。
早陣子﹐收到一個朋友的電郵﹐知道以前公司又有一些大變動。都說是為了迎合市場改變。想不到「英皇娛樂」也有發圍的一天。曾幾何時﹐我們自己也以為自己是整個集團的負擔。「溝女王」退休後﹐「機關槍」跳級上場擔大旗﹐公司業務便蒸蒸日上。閑談之間﹐我們講到了運。朋友說﹐HE IS VERY LUCKY。
不能否認﹐的確有點時來運到。幾年前﹐香港市場一片死水。因為政府實在不肯花錢。除了馬路部那幾個大項目外﹐什麼也不能上馬。幾年後﹐死水卻變成了活水。朋友說﹐突然﹐香港一切都以水為主。
從來﹐我都相信﹐幹什麼事情﹐也需要一點點運氣。因為沒有運﹐什麼也幹不成。
沒有運﹐你遇不到一個欣賞你的上司﹐你也遇不到一個風生水起﹑甚得公司讚賞的上司﹔沒有運﹐你便不能避開那些本來應該避不開的劫﹐你只會頭頭碰著黑﹔沒有運﹐你找不到與你互相扶持的好友﹐遇不到在背後默默支持你的那個心上人。這一切一切﹐實在都是運氣。
不過﹐單靠運氣﹐也是什麼也幹不成。因為運氣只是成功的其中一個因素。那個方程式裡面﹐其實還有很多很多VARIABLES。
只是﹐很多時候﹐我們都以為別人比我們幸運﹐所以才比我們成功。我們往往忽略了方程式裡面其他的VARIABLES。我相信﹐「機關槍」在運氣來之前﹐他曾經下過很多的苦工。當然﹐那些都是沒有人知的秘密。不過﹐假如沒有那些苦工﹐便是運氣來了﹐他也不能如魚得水﹐盡享一切好運帶來給他的好處。
有人說過﹐我們要經常準備運氣的到來。
我想﹐那不是要我們守株待兔﹐什麼也不幹﹐靜候自己的時來運到。相反﹐那是要我們不斷的努力﹐好好裝備自己﹐好讓我們能夠享盡一旦運氣來臨時帶來的好處。我總以為﹐好運不常。假如我們不能好好迎接突如其來的運氣﹐我們將後悔一輩子。
我一邊在電腦前寫著這篇文章﹐一邊聽著MEDIA PLAYER播放的MP3。我聽到側田的歌聲﹕捱盡黑夜便可看得到晨曦。極運滯日子都不要忘記﹐還在呼吸心跳我未被遺棄。
愛爾蘭冬天的黑夜的確很漫長。只是﹐我知道﹐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我要好好迎接春天的探訪。
那時候﹐他剛推出了新的大碟。其實裡面有很多首歌﹐不是互相很相似﹐便是跟他的首張唱片裡面的歌很相似。假如他下一張碟也是如此﹐我想﹐他應該要開始專心多搞一些緋聞。要不﹐他實在不用再想在紅館開演唱會。搞緋聞向來都是PARKO的拿手好戲。不過﹐要側田弄出緋聞﹐的確很高難度。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天才是沒有價值的。沒有人會相信香港娛樂圈裡面的女生﹐會只因為男人的才華而愛上他。無奈﹐很表面地﹐除了才華外﹐側田也沒有什麼﹐可以讓人相信那些女生會愛上他。
側田的第二張唱片裡面﹐我最喜歡的是《走音》。記得有朋友說過﹐喜歡上一首歌﹐很多時候﹐都是因為裡面的歌詞感動了你的每一條神經﹐都是因為歌中的意思竟然對你有點似曾相識。
也許﹐他是對的。
猶記得﹐那幾次的晚飯約會。回頭只見到你﹐對著電話聽語講。
也有一首歌﹐單字一個《運》。裡面有一句是這樣的﹕怎麼叫運﹐視乎你心理。
早陣子﹐收到一個朋友的電郵﹐知道以前公司又有一些大變動。都說是為了迎合市場改變。想不到「英皇娛樂」也有發圍的一天。曾幾何時﹐我們自己也以為自己是整個集團的負擔。「溝女王」退休後﹐「機關槍」跳級上場擔大旗﹐公司業務便蒸蒸日上。閑談之間﹐我們講到了運。朋友說﹐HE IS VERY LUCKY。
不能否認﹐的確有點時來運到。幾年前﹐香港市場一片死水。因為政府實在不肯花錢。除了馬路部那幾個大項目外﹐什麼也不能上馬。幾年後﹐死水卻變成了活水。朋友說﹐突然﹐香港一切都以水為主。
從來﹐我都相信﹐幹什麼事情﹐也需要一點點運氣。因為沒有運﹐什麼也幹不成。
沒有運﹐你遇不到一個欣賞你的上司﹐你也遇不到一個風生水起﹑甚得公司讚賞的上司﹔沒有運﹐你便不能避開那些本來應該避不開的劫﹐你只會頭頭碰著黑﹔沒有運﹐你找不到與你互相扶持的好友﹐遇不到在背後默默支持你的那個心上人。這一切一切﹐實在都是運氣。
不過﹐單靠運氣﹐也是什麼也幹不成。因為運氣只是成功的其中一個因素。那個方程式裡面﹐其實還有很多很多VARIABLES。
只是﹐很多時候﹐我們都以為別人比我們幸運﹐所以才比我們成功。我們往往忽略了方程式裡面其他的VARIABLES。我相信﹐「機關槍」在運氣來之前﹐他曾經下過很多的苦工。當然﹐那些都是沒有人知的秘密。不過﹐假如沒有那些苦工﹐便是運氣來了﹐他也不能如魚得水﹐盡享一切好運帶來給他的好處。
有人說過﹐我們要經常準備運氣的到來。
我想﹐那不是要我們守株待兔﹐什麼也不幹﹐靜候自己的時來運到。相反﹐那是要我們不斷的努力﹐好好裝備自己﹐好讓我們能夠享盡一旦運氣來臨時帶來的好處。我總以為﹐好運不常。假如我們不能好好迎接突如其來的運氣﹐我們將後悔一輩子。
我一邊在電腦前寫著這篇文章﹐一邊聽著MEDIA PLAYER播放的MP3。我聽到側田的歌聲﹕捱盡黑夜便可看得到晨曦。極運滯日子都不要忘記﹐還在呼吸心跳我未被遺棄。
愛爾蘭冬天的黑夜的確很漫長。只是﹐我知道﹐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我要好好迎接春天的探訪。
Friday, November 10, 2006
給時鐘調校回正常的時間後﹐天空在四時開始便變得黑暗。一直到第二朝早七點﹐太陽才會再次露面。
似乎﹐我的生活習慣要有點改變。
平時上班下班﹐其實也沒有太大影響。至多是要靠著街燈的照耀﹐方能從公司步行到火車站。香港冬天的時候﹐假如遲了離開公司﹐也是一樣的光景。況且﹐校了時間後﹐朝早起床的時候﹐可以見到陽光﹐感覺比較好。還記得校鐘前的兩個星期﹐每天都要辛苦地在黑暗裡爬到洗手間。沒有晨光﹐的確很難離開溫暖的被窩。
要改變的﹐是週末放假的日子。
以前放假的時候﹐我總習慣睡到早上十時許。有時﹐還會超過十一點。現在﹐日照時間短了﹐假如我還多待在床上﹐我怕我會整天看不到陽光。對於我這個從亞熱帶來的人﹐我依然不能沒有陽光。所以﹐我決定便是放假﹐也早點起床。
上星期天﹐我更做了一隻早起的鳥兒。
我九點半便從睡夢中醒了過來。匆匆梳洗過後﹐便更衣出門。因為我知道﹐住所附近那間戲院有早場優惠﹕十二點前的票只需五塊歐羅。前一天﹐我查過放映時間﹐知道他們十時五分會播映BORAT。 早前﹐看過它的預告片﹐發覺很好笑﹐所以實在很期待。
電影名字很長。BORAT只是大家的簡稱。全名是﹐BORAT︰CUTURAL LEARNINGS OF AMERICA FOR MAKE BENEFIT GLORIOUS NATION OF KAZAKHSTAN。
單看電影名字﹐你應該可以猜到故事內容的大概。的確﹐那是大鄉里出城的故事。
跟以往一樣。太高的期望﹐換來的只是一大堆的失望。原來﹐最好笑的﹐都在預告片裡出現了。
我很後悔沒有選MARIE ANTOINETTE。那是SOFIA COPPOLA的新作﹐講的是那個「幹麼不吃麵包」的瑪麗皇后。而且﹐SOFIA的前作LOST IN TRANSLATION很得我歡喜。我是知道﹐戲院安排了一個十點四十分場。只是﹐我想笑一頓。我以為﹐對於星期天早上來說﹐MARIE ANTOINETTE是HEAVY了點兒。
原本﹐我很慶幸做了一隻早起的鳥兒。因為我也只是花了五塊錢。要知道﹐十二點打後的其他場次﹐一律九塊二。只是﹐從戲院走回家﹐途徑HMV,因為減價﹐便走了入去逛逛。我見到THE SHINING和THE CLOCKWORK ORANGE的DVD都只是賣七塊。羅柭迪尼路的《的士司機》更不過五塊。花了五塊看一部搣我笑的BORAT,的確是太昂貴了。
不過﹐因為家裡多了一疊DVD,都是從妹妹倫敦的家搬過來﹐還未有時間看。所以﹐我還是按住了手﹐沒有把它們買下。
我想﹐現在家裡的DVD存貨應該可以捱得過這個冬天。之前﹐所有朋友寄來的碟也沒有看便是這個原因。
似乎﹐我的生活習慣要有點改變。
平時上班下班﹐其實也沒有太大影響。至多是要靠著街燈的照耀﹐方能從公司步行到火車站。香港冬天的時候﹐假如遲了離開公司﹐也是一樣的光景。況且﹐校了時間後﹐朝早起床的時候﹐可以見到陽光﹐感覺比較好。還記得校鐘前的兩個星期﹐每天都要辛苦地在黑暗裡爬到洗手間。沒有晨光﹐的確很難離開溫暖的被窩。
要改變的﹐是週末放假的日子。
以前放假的時候﹐我總習慣睡到早上十時許。有時﹐還會超過十一點。現在﹐日照時間短了﹐假如我還多待在床上﹐我怕我會整天看不到陽光。對於我這個從亞熱帶來的人﹐我依然不能沒有陽光。所以﹐我決定便是放假﹐也早點起床。
上星期天﹐我更做了一隻早起的鳥兒。
我九點半便從睡夢中醒了過來。匆匆梳洗過後﹐便更衣出門。因為我知道﹐住所附近那間戲院有早場優惠﹕十二點前的票只需五塊歐羅。前一天﹐我查過放映時間﹐知道他們十時五分會播映BORAT。 早前﹐看過它的預告片﹐發覺很好笑﹐所以實在很期待。
電影名字很長。BORAT只是大家的簡稱。全名是﹐BORAT︰CUTURAL LEARNINGS OF AMERICA FOR MAKE BENEFIT GLORIOUS NATION OF KAZAKHSTAN。
單看電影名字﹐你應該可以猜到故事內容的大概。的確﹐那是大鄉里出城的故事。
跟以往一樣。太高的期望﹐換來的只是一大堆的失望。原來﹐最好笑的﹐都在預告片裡出現了。
我很後悔沒有選MARIE ANTOINETTE。那是SOFIA COPPOLA的新作﹐講的是那個「幹麼不吃麵包」的瑪麗皇后。而且﹐SOFIA的前作LOST IN TRANSLATION很得我歡喜。我是知道﹐戲院安排了一個十點四十分場。只是﹐我想笑一頓。我以為﹐對於星期天早上來說﹐MARIE ANTOINETTE是HEAVY了點兒。
原本﹐我很慶幸做了一隻早起的鳥兒。因為我也只是花了五塊錢。要知道﹐十二點打後的其他場次﹐一律九塊二。只是﹐從戲院走回家﹐途徑HMV,因為減價﹐便走了入去逛逛。我見到THE SHINING和THE CLOCKWORK ORANGE的DVD都只是賣七塊。羅柭迪尼路的《的士司機》更不過五塊。花了五塊看一部搣我笑的BORAT,的確是太昂貴了。
不過﹐因為家裡多了一疊DVD,都是從妹妹倫敦的家搬過來﹐還未有時間看。所以﹐我還是按住了手﹐沒有把它們買下。
我想﹐現在家裡的DVD存貨應該可以捱得過這個冬天。之前﹐所有朋友寄來的碟也沒有看便是這個原因。
Thursday, November 09, 2006
歷史書告訴我們﹐布拉格的一切﹐都是從山上那個城堡開始。於是﹐我們的行程也由PARGUE CASTLE做起點。
我們在國家劇院搭23號電車上山。
穿梭於大小街巷﹐看到很多漂亮的建築。可能沉迷於那些一幢又一幢的歷史建築物﹐也可能太喜歡那悠閑的電車旅程﹐我們竟然忘記了下車。當我們記得下車的時候﹐電車已經到了終站前的最後一個車站。不過﹐旅遊書說﹐從那兒也可以走到布拉格城堡﹐只是沒有詳細指出如何走法。於是﹐我們便拿出地圖﹐希望找到那一條路。
我們一邊走﹐一邊看地圖。突然﹐後邊有一把聲音叫停了我們。
是一個老頭﹐大約有六十歲罷。個子不高﹐依然很壯健。至少﹐聲音還很雄壯。他用英文問我們到哪兒去。聽到我們的目的地後﹐他跟我們說﹐我們是走錯了路。城堡可是在相反方向。原來﹐我們正朝著學生和軍人宿舍那邊走。他想﹐那邊是應該不會有外國人到的地方﹐故此叫停了我們。他怕我們走錯了路。
的而且確﹐我們是走錯了路。
老頭很詳細地跟我們講解如何走法。他說﹐從這兒一直走﹐你們便會看到我們那個著名的城堡。不消半個小時﹐就可到達。途中﹐你們會經過LORETA。我建議你們到那兒逛逛。
接著﹐他又很細心地介紹那個充滿不少神秘故事的建築。當然﹐還有那顆鑽石。LORETO TREASURY。旅遊書說﹐LORETA是當年費地蘭二世使捷克回復天主教的重要地方。
正要跟老頭講再見的時候﹐他忽然問我們究竟從哪兒來。幸運地和不幸地﹐他猜到我們是中國人。猶記得﹐陶傑說過﹐旅行的時候﹐給人誤認作日本人是一種福份。我們縱然跟那些大陸人很不同﹐畢竟沒有日本人那樣DECENT。
知道我們來自香港後﹐他又問我們知不知道北方的中國。原來﹐年青的時候﹐老頭在北京住過十五年。我想﹐那是共產國際的年代。
當我們說也聽得懂一點點國語後﹐他竟然改用了國語來跟我們交談。有點慚愧﹐他說的普通話比我好。(他以為自己說的是國語(MANDARIN),其實那不過是普通話(PUTONGHUA)罷了。他在中國的時候﹐我們的祖國應該已經變了紅色。)
似乎﹐他依然很懷念年青的日子。那些青蔥歲月。對於中國的一切﹐他還很有興趣。他希望跟我們交換一些香港錢幣。於是﹐同行友人便跟他兌換了一些。對於他那個要求﹐我真的幫不了忙。我身上的港幣﹐才只得一張一百塊。
他有點興奮地望著那些硬幣。他應該很開心。
跟老頭分手後﹐我們是到了LORETA。不過﹐我們並沒有到裡面參觀。因為正是中飯時間。關了門。
我們在國家劇院搭23號電車上山。
穿梭於大小街巷﹐看到很多漂亮的建築。可能沉迷於那些一幢又一幢的歷史建築物﹐也可能太喜歡那悠閑的電車旅程﹐我們竟然忘記了下車。當我們記得下車的時候﹐電車已經到了終站前的最後一個車站。不過﹐旅遊書說﹐從那兒也可以走到布拉格城堡﹐只是沒有詳細指出如何走法。於是﹐我們便拿出地圖﹐希望找到那一條路。
我們一邊走﹐一邊看地圖。突然﹐後邊有一把聲音叫停了我們。
是一個老頭﹐大約有六十歲罷。個子不高﹐依然很壯健。至少﹐聲音還很雄壯。他用英文問我們到哪兒去。聽到我們的目的地後﹐他跟我們說﹐我們是走錯了路。城堡可是在相反方向。原來﹐我們正朝著學生和軍人宿舍那邊走。他想﹐那邊是應該不會有外國人到的地方﹐故此叫停了我們。他怕我們走錯了路。
的而且確﹐我們是走錯了路。
老頭很詳細地跟我們講解如何走法。他說﹐從這兒一直走﹐你們便會看到我們那個著名的城堡。不消半個小時﹐就可到達。途中﹐你們會經過LORETA。我建議你們到那兒逛逛。
接著﹐他又很細心地介紹那個充滿不少神秘故事的建築。當然﹐還有那顆鑽石。LORETO TREASURY。旅遊書說﹐LORETA是當年費地蘭二世使捷克回復天主教的重要地方。
正要跟老頭講再見的時候﹐他忽然問我們究竟從哪兒來。幸運地和不幸地﹐他猜到我們是中國人。猶記得﹐陶傑說過﹐旅行的時候﹐給人誤認作日本人是一種福份。我們縱然跟那些大陸人很不同﹐畢竟沒有日本人那樣DECENT。
知道我們來自香港後﹐他又問我們知不知道北方的中國。原來﹐年青的時候﹐老頭在北京住過十五年。我想﹐那是共產國際的年代。
當我們說也聽得懂一點點國語後﹐他竟然改用了國語來跟我們交談。有點慚愧﹐他說的普通話比我好。(他以為自己說的是國語(MANDARIN),其實那不過是普通話(PUTONGHUA)罷了。他在中國的時候﹐我們的祖國應該已經變了紅色。)
似乎﹐他依然很懷念年青的日子。那些青蔥歲月。對於中國的一切﹐他還很有興趣。他希望跟我們交換一些香港錢幣。於是﹐同行友人便跟他兌換了一些。對於他那個要求﹐我真的幫不了忙。我身上的港幣﹐才只得一張一百塊。
他有點興奮地望著那些硬幣。他應該很開心。
跟老頭分手後﹐我們是到了LORETA。不過﹐我們並沒有到裡面參觀。因為正是中飯時間。關了門。
Wednesday, November 08, 2006
自五十年前的蘇彝士運河危機開始﹐英國便跟在美國的背後走。
最近﹐那個一度是下一任美國總統的戈爾竟然成為了英國政治圈子裡面的大忙人。執政的工黨與在野的保守黨紛紛拉攏他為自己站台助威。因為環境保護成為了政治圈中的重要話題。當不成美國總統後,AL GORE跑了去當環保專家﹐既寫書﹐又拍電影﹐跟大家講溫室效應。AN INCONVENIENT TRUTH便是他的作品。有人說﹐那是戈爾的宣傳伎倆。他希望再次競選美國總統。
九月的時候﹐英國三大政黨都會舉行黨會議。每個會議都為期一個星期﹐討論新一屆政治季度﹐自己政黨應走的方向。不過﹐便只有保守黨方能提出一些較為實在的政策方向。因為其餘兩個政黨都受著其他事情干擾。自由民主黨忙於應付前主席酗酒問題﹐工黨則不到花心血在貝利雅和白高敦個人鬥爭上面。
於是﹐下任英國首相大熱門金馬倫便悄悄地替政府定下了AGENDA。環境保護成為了最新潮的政治議題﹐成為全民關心的事情。民意調查發現﹐超過三成的英國人認為DAVID CAMERON關注ENVIRONMENTAL PROTECTION,才僅過兩成相信GORDON BROWN關心污染問題。
黨會議期間﹐DAVID CAMERON面對著廣大英國市面大聲疾呼﹕Government must show leadership by setting the right framework. Binding targets for carbon reduction, year on yearm that would create a price for carbon in our economy. We have asked Tony Blair to put a Climate Change Bill in the Queen's Speech. If he does, we will back it. So come on Prime Minister, it's your last few months in office, use it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environment.
兩個月後﹐在經濟學家SIR NICHOLAS STERN發表他的環境經濟報告的當天﹐TONY BLAIR和GORDON BROWN便一同走出來﹐宣佈一系列的環保政策﹐包括加重航空稅項﹐特別是那些乘搭BUDGET AIRLINE的旅客。因為乘飛機,就像吸一枝上帝型的大雪茄,呼出來的二手廢氣,是環保的浩劫。政府說﹐所有詳情都會在明年三月財政預算公佈。他們叫那些做綠色稅(GREEN TAX)。
近日﹐MTV電視臺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音樂頒獎禮。主題也是環境保護。所有明星歌手都在提醒大家要節約用電﹑節約用水。他們都在重複著SIR NICHOLAS報告裡的一個重點﹕IF WE ACT NOW,WE CAN AVOID THE VERY WORST。報告總結說﹐假如從現在開始﹐每年花GDP的一個巴仙在環境保護上面﹐這個世紀末﹐我們將可以節省國民生產總值的5-20%。
只有在那些落後地方﹐政治才會把人悶得個鳥來。來來去去講的都是什麼愛國不愛國﹑保皇不保皇﹑北京祝福不祝福。這些話題年年月月日日﹐不斷地重複﹐完全沒有新意。最悲哀的是﹐每年每月每天見到的都是那些一模一樣的臉孔﹐看著他們從年青容光煥發﹐變到衰老皺皮無神﹐可是卻依然講著那些十年如一日的說話。
猶記得﹐孔少林曾經寫道﹕
所謂「香港政黨發展不足,從政人才不夠」實是廢話,這根本就是雞與雞蛋的問題。如果確定2012年普選,政黨有機會變成執政黨,它們自然會大力推廣及發展。如果知道從政可以出頭,香港不少「醒目仔」新血自然會投身政界,哪怕沒有人才?
政治本是關於人的事情﹐而人本是不斷進步的動物。假如我們的政治人物﹐年年月月日日都只在講那幾個課題﹐你能說我們在不斷進步嗎﹖
在別人不斷進步的同時﹐我們卻原地踏步﹐那便是退步。假如我們不是正在大步大步向後退。
也許﹐這正是北京對香港的政策﹕把所有關心政治的人都悶死﹐以後便再沒有人跟他們唱對臺戲。
只希望那時候﹐香港依然能夠經濟繁榮。
最近﹐那個一度是下一任美國總統的戈爾竟然成為了英國政治圈子裡面的大忙人。執政的工黨與在野的保守黨紛紛拉攏他為自己站台助威。因為環境保護成為了政治圈中的重要話題。當不成美國總統後,AL GORE跑了去當環保專家﹐既寫書﹐又拍電影﹐跟大家講溫室效應。AN INCONVENIENT TRUTH便是他的作品。有人說﹐那是戈爾的宣傳伎倆。他希望再次競選美國總統。
九月的時候﹐英國三大政黨都會舉行黨會議。每個會議都為期一個星期﹐討論新一屆政治季度﹐自己政黨應走的方向。不過﹐便只有保守黨方能提出一些較為實在的政策方向。因為其餘兩個政黨都受著其他事情干擾。自由民主黨忙於應付前主席酗酒問題﹐工黨則不到花心血在貝利雅和白高敦個人鬥爭上面。
於是﹐下任英國首相大熱門金馬倫便悄悄地替政府定下了AGENDA。環境保護成為了最新潮的政治議題﹐成為全民關心的事情。民意調查發現﹐超過三成的英國人認為DAVID CAMERON關注ENVIRONMENTAL PROTECTION,才僅過兩成相信GORDON BROWN關心污染問題。
黨會議期間﹐DAVID CAMERON面對著廣大英國市面大聲疾呼﹕Government must show leadership by setting the right framework. Binding targets for carbon reduction, year on yearm that would create a price for carbon in our economy. We have asked Tony Blair to put a Climate Change Bill in the Queen's Speech. If he does, we will back it. So come on Prime Minister, it's your last few months in office, use it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environment.
兩個月後﹐在經濟學家SIR NICHOLAS STERN發表他的環境經濟報告的當天﹐TONY BLAIR和GORDON BROWN便一同走出來﹐宣佈一系列的環保政策﹐包括加重航空稅項﹐特別是那些乘搭BUDGET AIRLINE的旅客。因為乘飛機,就像吸一枝上帝型的大雪茄,呼出來的二手廢氣,是環保的浩劫。政府說﹐所有詳情都會在明年三月財政預算公佈。他們叫那些做綠色稅(GREEN TAX)。
近日﹐MTV電視臺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音樂頒獎禮。主題也是環境保護。所有明星歌手都在提醒大家要節約用電﹑節約用水。他們都在重複著SIR NICHOLAS報告裡的一個重點﹕IF WE ACT NOW,WE CAN AVOID THE VERY WORST。報告總結說﹐假如從現在開始﹐每年花GDP的一個巴仙在環境保護上面﹐這個世紀末﹐我們將可以節省國民生產總值的5-20%。
只有在那些落後地方﹐政治才會把人悶得個鳥來。來來去去講的都是什麼愛國不愛國﹑保皇不保皇﹑北京祝福不祝福。這些話題年年月月日日﹐不斷地重複﹐完全沒有新意。最悲哀的是﹐每年每月每天見到的都是那些一模一樣的臉孔﹐看著他們從年青容光煥發﹐變到衰老皺皮無神﹐可是卻依然講著那些十年如一日的說話。
猶記得﹐孔少林曾經寫道﹕
所謂「香港政黨發展不足,從政人才不夠」實是廢話,這根本就是雞與雞蛋的問題。如果確定2012年普選,政黨有機會變成執政黨,它們自然會大力推廣及發展。如果知道從政可以出頭,香港不少「醒目仔」新血自然會投身政界,哪怕沒有人才?
政治本是關於人的事情﹐而人本是不斷進步的動物。假如我們的政治人物﹐年年月月日日都只在講那幾個課題﹐你能說我們在不斷進步嗎﹖
在別人不斷進步的同時﹐我們卻原地踏步﹐那便是退步。假如我們不是正在大步大步向後退。
也許﹐這正是北京對香港的政策﹕把所有關心政治的人都悶死﹐以後便再沒有人跟他們唱對臺戲。
只希望那時候﹐香港依然能夠經濟繁榮。
Tuesday, November 07, 2006
OASIS是一隊我喜歡的ROCK N'ROLL BAND。十年前﹐偶然在電視機裡看到了DON'T LOOK BACK IN ANGER的MTV,便深深地愛上了他們的音樂。那一張大碟(WHAT'S THE STORY)MORNING GLORY至今依然是我的至愛。
今年開始﹐OASIS亦是一間香港廉價航空公司的名字。跟歐洲的BUDGET AIRLINE不同﹐OASIS的航線竟然是LONG HAUL FLIGHT。公司起步階段﹐他們只有香港直航到倫敦這個航班。世界上其中一條最繁忙的航道。他們的CEO STEVE MILLER說﹐公司的目標是向遠東一帶地方﹐提供廉價的長程直航到歐洲以至北美大陸。
只是﹐落筆打三更。因為俄羅斯那邊沒有批出領空飛行權﹐OASIS的首航被逼延期。經多翻交涉後﹐第一班航機終於在上星期五從倫敦GATWICK飛抵香港。
我當然希望OASIS能夠成功。因為那樣子﹐只要假期許可﹐回香港一趟也再不是一件太過艱難的事情。廣告說﹐單程機票最低可以到75英鎊。(知道有舊同學成功用這個價錢買了一張飛返香港的機票。)
實在想不透他們的BUSINESS MODEL。
RYANAIR能夠成功﹐因為他們把飛機看待成巴士一樣。才剛降落﹐便又立即載同另外一批乘客到另一個地方。一架飛機一天可以飛七﹑八轉。也因為他們飛的都是歐洲短途航線﹐於是他們可以把飛機停留機場的時間縮短至半個小時以內﹐節省了不少開支,大大減低了成本。因此﹐可以提供低過一塊歐羅的飛行,深受歐洲人的歡迎。這一間愛爾蘭公司﹐現在已是全球最賺錢的航空公司。
不過﹐OASIS提供的可是LONG HAUL FLIGHT。而且還有免費餐飲﹑椅背電視和枕頭被鋪。跟RYANAIR倒是大大的不同。真的不明白他們如何控制成本。
況且﹐在環境保護的聲音越來越強烈的時候﹐我怕BUDGET AIRLINE再不是一門容易賺錢的生意。
兩個多月前﹐陶傑竟然像未卜先知一樣﹐在黃金冒險號裡面說道﹐
「歐美的潮流人士,正在醞釀一種新的文化理論:坐飛機之不道德與虛妄,與吸煙相同。因為乘飛機,就像吸一枝上帝型的大雪茄,呼出來的二手廢氣,是環保的浩劫。從澳洲悉尼乘單程飛機去倫敦,約二十二小時,飛機排放的二氧化碳超過五噸。」
最近﹐英國財相白高敦便宣佈準備加重飛行稅﹐尤其那些廉價航空。目的當然是為了減少飛行﹐減少排放二氧化碳。BUDGET AIRLINE的出現﹐的確方便了不少旅客﹐使更多人放假出外旅行。據估計﹐飛機排出的CO2佔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知道政府的行動後﹐SIR RICHARD BRANSON便呼籲業界一起開會﹐商討應付辦法。
曾經﹐乘飛機是一樣富豪般的活動。那時候﹐不少人都以搭過飛機自豪。只是﹐當環境保護越來越受關注之際﹐也許﹐乘飛機將會再是一樣昂貴的消費。
近來﹐讀了這一個廣告。是一間叫EOS的航空公司。他們說﹐他們的飛機只得四十八個乘客﹐縱然本來可以容納二百二十個乘客。因為他們要每個乘客都有至少21平方尺的空間﹐也有一張六尺六寸長的床。他們提供的﹐只有頭等服務。
或者﹐OASIS是走錯了路。
今年開始﹐OASIS亦是一間香港廉價航空公司的名字。跟歐洲的BUDGET AIRLINE不同﹐OASIS的航線竟然是LONG HAUL FLIGHT。公司起步階段﹐他們只有香港直航到倫敦這個航班。世界上其中一條最繁忙的航道。他們的CEO STEVE MILLER說﹐公司的目標是向遠東一帶地方﹐提供廉價的長程直航到歐洲以至北美大陸。
只是﹐落筆打三更。因為俄羅斯那邊沒有批出領空飛行權﹐OASIS的首航被逼延期。經多翻交涉後﹐第一班航機終於在上星期五從倫敦GATWICK飛抵香港。
我當然希望OASIS能夠成功。因為那樣子﹐只要假期許可﹐回香港一趟也再不是一件太過艱難的事情。廣告說﹐單程機票最低可以到75英鎊。(知道有舊同學成功用這個價錢買了一張飛返香港的機票。)
實在想不透他們的BUSINESS MODEL。
RYANAIR能夠成功﹐因為他們把飛機看待成巴士一樣。才剛降落﹐便又立即載同另外一批乘客到另一個地方。一架飛機一天可以飛七﹑八轉。也因為他們飛的都是歐洲短途航線﹐於是他們可以把飛機停留機場的時間縮短至半個小時以內﹐節省了不少開支,大大減低了成本。因此﹐可以提供低過一塊歐羅的飛行,深受歐洲人的歡迎。這一間愛爾蘭公司﹐現在已是全球最賺錢的航空公司。
不過﹐OASIS提供的可是LONG HAUL FLIGHT。而且還有免費餐飲﹑椅背電視和枕頭被鋪。跟RYANAIR倒是大大的不同。真的不明白他們如何控制成本。
況且﹐在環境保護的聲音越來越強烈的時候﹐我怕BUDGET AIRLINE再不是一門容易賺錢的生意。
兩個多月前﹐陶傑竟然像未卜先知一樣﹐在黃金冒險號裡面說道﹐
「歐美的潮流人士,正在醞釀一種新的文化理論:坐飛機之不道德與虛妄,與吸煙相同。因為乘飛機,就像吸一枝上帝型的大雪茄,呼出來的二手廢氣,是環保的浩劫。從澳洲悉尼乘單程飛機去倫敦,約二十二小時,飛機排放的二氧化碳超過五噸。」
最近﹐英國財相白高敦便宣佈準備加重飛行稅﹐尤其那些廉價航空。目的當然是為了減少飛行﹐減少排放二氧化碳。BUDGET AIRLINE的出現﹐的確方便了不少旅客﹐使更多人放假出外旅行。據估計﹐飛機排出的CO2佔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知道政府的行動後﹐SIR RICHARD BRANSON便呼籲業界一起開會﹐商討應付辦法。
曾經﹐乘飛機是一樣富豪般的活動。那時候﹐不少人都以搭過飛機自豪。只是﹐當環境保護越來越受關注之際﹐也許﹐乘飛機將會再是一樣昂貴的消費。
近來﹐讀了這一個廣告。是一間叫EOS的航空公司。他們說﹐他們的飛機只得四十八個乘客﹐縱然本來可以容納二百二十個乘客。因為他們要每個乘客都有至少21平方尺的空間﹐也有一張六尺六寸長的床。他們提供的﹐只有頭等服務。
或者﹐OASIS是走錯了路。
Monday, November 06, 2006
在都柏林生活﹐其實可以很悶。因為這兒﹐除了酒館外﹐還是酒館。入夜後﹐還打開門做生意的﹐便只有他們。經濟學人說﹐愛爾蘭是全球消耗啤酒第二多的國家。排首位的﹐是捷克。在那兒﹐所有餐廳都不供應白開水。客人一坐下﹐侍應便會立即遞來啤酒。況且﹐捷克的生活水平始終較低﹐多飲兩PINT,銀包也不覺得有什麼分別。在都柏林﹐一PINT大約要三至四歐羅﹔在布拉格﹐還不過一歐羅啊﹗
剛來到愛爾蘭的時候﹐有朋友知道我喜歡跟同事到酒館去﹐叮囑我不好飲得太多。
不過﹐近來讀了些調查﹐我想﹐我是飲的太少。
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發現﹐那些喜歡到公司附近酒館多飲兩杯的人﹐其收入會比下班後立即趕回家的同事高。當中﹐尤以女性的差別至為明顯。調查說﹐喜歡到公司附近酒館的女性的收入﹐比不去酒館的女性高14%。男性的差別只有10%。
實在很佩服陶傑。他的確很了解西方的世界。尤記得半年前﹐他在《壹周刊》寫了這樣的一段文字﹕
「當然,打鬼佬工,晉陞機會有限,在歐美,亞裔的打工絕對覺得頭上有一塊玻璃天花板——看得見頂,但爬不上去,這是因為亞裔員工的文化隔閡,例如下了班,不可以跟鬼佬同事一起到酒吧泡兩小時。為什麼不可以?因為英語不夠地道,對西方社會的流行文化所知不多,無法深入交心溝通。打好人際關係,不靠辦公室,靠公司樓下不遠的那家酒吧,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他的觀察﹐得到了科學客觀的肯定。
聖荷西州立大學的調查分析說﹐下班後會到公司附近酒館多飲兩杯的人﹐一般都較為外向。他們都喜歡跟人交談﹐所以容易建立那所謂的「社交本錢」。他們亦很懂得運用這種本領﹐跟顧客﹑同事和上司打好關係。現代社會﹐講究的是NETWORKING。在酒館裡﹐捧著酒杯﹐跟萍水相逢的人談天說地﹐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多接觸社會不同人士﹐學習到不同界別的做事方式。
亦有醫學報告說﹐適量的酒精對心臟有益。它能夠防止心臟病﹐或者延遲發病。報告說﹐這是差不多所有醫生都同意的事情。同時﹐他們也發現﹐喜歡飲酒的人﹐除了生活會開心點外﹐更會比較長壽。當然﹐他們也肯定酗酒對身體有害。
讀著這兩個調查﹐我是真的飲得太少了。我想﹐一個星期最多才一次的酒館聚會﹐怎不能說是太少﹖
所以﹐為了自己的健康﹐也為了自己銀行戶口的健康﹐我決定每個星期多飲兩PINT GUINNESS。
剛來到愛爾蘭的時候﹐有朋友知道我喜歡跟同事到酒館去﹐叮囑我不好飲得太多。
不過﹐近來讀了些調查﹐我想﹐我是飲的太少。
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發現﹐那些喜歡到公司附近酒館多飲兩杯的人﹐其收入會比下班後立即趕回家的同事高。當中﹐尤以女性的差別至為明顯。調查說﹐喜歡到公司附近酒館的女性的收入﹐比不去酒館的女性高14%。男性的差別只有10%。
實在很佩服陶傑。他的確很了解西方的世界。尤記得半年前﹐他在《壹周刊》寫了這樣的一段文字﹕
「當然,打鬼佬工,晉陞機會有限,在歐美,亞裔的打工絕對覺得頭上有一塊玻璃天花板——看得見頂,但爬不上去,這是因為亞裔員工的文化隔閡,例如下了班,不可以跟鬼佬同事一起到酒吧泡兩小時。為什麼不可以?因為英語不夠地道,對西方社會的流行文化所知不多,無法深入交心溝通。打好人際關係,不靠辦公室,靠公司樓下不遠的那家酒吧,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他的觀察﹐得到了科學客觀的肯定。
聖荷西州立大學的調查分析說﹐下班後會到公司附近酒館多飲兩杯的人﹐一般都較為外向。他們都喜歡跟人交談﹐所以容易建立那所謂的「社交本錢」。他們亦很懂得運用這種本領﹐跟顧客﹑同事和上司打好關係。現代社會﹐講究的是NETWORKING。在酒館裡﹐捧著酒杯﹐跟萍水相逢的人談天說地﹐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多接觸社會不同人士﹐學習到不同界別的做事方式。
亦有醫學報告說﹐適量的酒精對心臟有益。它能夠防止心臟病﹐或者延遲發病。報告說﹐這是差不多所有醫生都同意的事情。同時﹐他們也發現﹐喜歡飲酒的人﹐除了生活會開心點外﹐更會比較長壽。當然﹐他們也肯定酗酒對身體有害。
讀著這兩個調查﹐我是真的飲得太少了。我想﹐一個星期最多才一次的酒館聚會﹐怎不能說是太少﹖
所以﹐為了自己的健康﹐也為了自己銀行戶口的健康﹐我決定每個星期多飲兩PINT GUINNESS。
Sunday, November 05, 2006
萬聖節關係﹐同事搞了個化妝派對﹐廣邀大家參加。在MERRION SQUARE附近的一間酒館舉行。
因為不大喜歡扮鬼扮馬﹐也沒有太多心思放在那些特別服裝上面﹐老早打算不出席。NICHOLA知道後﹐跟我說﹐你可以和我一樣遲些時候才出現。EILEEN也說﹐應該也有一些人不化妝的﹗不外是為了跳跳舞舞﹑飲飲酒酒﹐希望有一個瘋狂愉快的星期五晚上。
說的倒是實話。實在想不到有什麼活動﹐不是為了飲酒舉行。便是結婚﹐也是為了跟一眾朋友飲酒慶祝罷﹖酒﹐在愛爾蘭﹐永遠排第一位。
跟另外幾個同事在TEMPLE BAR飲了幾PINT後﹐有人便提議到MERRION SQUARE趕下一場。望望手錶﹐才十一點半﹐時間還很早﹐於是便和他們一起走去THE GINGER MAN PUB,參加那個化妝派對。
酒館有兩層。我們包起了頂層。
在樓梯轉角﹐我又碰見那個從立陶宛來的同事。才剛認識。很奇怪﹐整個星期﹐無論搭那一班火車上班﹑那一班火車回家﹐我都會在車廂裡面遇見他。ADRIAN戲言﹐你是被人跟蹤罷﹖誠然﹐我們都覺得這個立陶宛人行為有點古怪。或者﹐都是我們的錯覺。因為在火車上﹐他也跟我講了一些關於立陶宛的得意事情。都是很好的故事題材。
跟我打了個照面﹐便匆匆和老婆一起離開了酒館。
也遇到了一位貓女郎。我猜不到那是誰﹐只知道是一個男人來。他說﹐我聽過你的名字。A F**KING FUNNY MAN。我笑著回答﹐漂亮的女孩啊﹗才一半正確﹗我恐怕﹐他們介紹我給你認識的時候﹐不會說我是一個有趣的人。說畢﹐我們都相擁而笑。我當然也按了一下貓女郎的胸。碰巧﹐JENNIFER經過。她指著我說﹐看看你在做什麼﹖她是三樓的同事﹐沒有什麼妝扮。JENNIFER不是特別漂亮﹐不過很有一點獨特的女人味。上次到CO CARLOW旅行﹐我見到她跟ENDA打得很滾熱。
當然﹐也見到ENDA。他是派對的搞手。他以聰明笨伯的形像走來走去。我們一見面﹐少不免JAM一JAM OASIS的歌。突然﹐有一隻大熊跑來襲擊我。一時反應不及﹐中了他兩記勾拳。他戴著那個密不透風的毛茸茸頭罩﹐實在沒有可能知道是誰。多說幾句話﹐方猜到是BRENDON。他也是一個OASIS的歌迷。ENDA也介紹了幾個女孩給我認識。他依然是那一句開場白﹕DO YOU KNOW THIS MAN?HE'S A LEGEND!THAT'S MAN.
忽然聽到AIDAN叫喚﹐只見到一個科學怪人向我招手。原來﹐AIDAN要跟我介紹一個超級愛華頓擁躉。是他的朋友。因為實在太吵﹐聽不清楚他的名字。姑且叫做E罷。
E很奇怪﹐我竟然會是EVERTON的球迷。我說﹐自1986年起了。那時候﹐我們還是英國冠軍。AIDAN立即說﹐怎麼你們曾經是英國冠軍﹖也不用我開口﹐E已經搶著道﹐也跟你的皇家馬德里一樣罷。都曾經是國內聯賽冠軍。我們當然談了很多足球的事情。我跟他們說﹐上星期到EMIRATES STADIUM的經歷。E提議說﹐你應該到GOODISON去。上季﹐我們一行五人﹐便走了去看EVERTON v CHARLTON。
AIDAN曾經跟我說過那次旅程。他說﹐也可以到BOX OFFICE買票。不過﹐只能是那些次一級球隊的賽事。我說﹐我最想看的倒是MERSEYSIDE DERBY。
奈何你們不能面對REAL MADRID。AIDAN扮作感嘆道。
我和E即時異口同聲說﹐留待明年﹗我還補充了一句﹕IN THE CHAMPIONS LEAGUE FINAL。
突然傳來一陣掌聲。原來﹐貓女郎贏得了化妝大獎。當他上前拿去獎項的時候﹐我方知道﹐他是結構部的頭目KENNY MASON。
之後﹐大家繼續跳舞飲酒。
到上床睡覺﹐已經過了四點鐘罷﹖
因為不大喜歡扮鬼扮馬﹐也沒有太多心思放在那些特別服裝上面﹐老早打算不出席。NICHOLA知道後﹐跟我說﹐你可以和我一樣遲些時候才出現。EILEEN也說﹐應該也有一些人不化妝的﹗不外是為了跳跳舞舞﹑飲飲酒酒﹐希望有一個瘋狂愉快的星期五晚上。
說的倒是實話。實在想不到有什麼活動﹐不是為了飲酒舉行。便是結婚﹐也是為了跟一眾朋友飲酒慶祝罷﹖酒﹐在愛爾蘭﹐永遠排第一位。
跟另外幾個同事在TEMPLE BAR飲了幾PINT後﹐有人便提議到MERRION SQUARE趕下一場。望望手錶﹐才十一點半﹐時間還很早﹐於是便和他們一起走去THE GINGER MAN PUB,參加那個化妝派對。
酒館有兩層。我們包起了頂層。
在樓梯轉角﹐我又碰見那個從立陶宛來的同事。才剛認識。很奇怪﹐整個星期﹐無論搭那一班火車上班﹑那一班火車回家﹐我都會在車廂裡面遇見他。ADRIAN戲言﹐你是被人跟蹤罷﹖誠然﹐我們都覺得這個立陶宛人行為有點古怪。或者﹐都是我們的錯覺。因為在火車上﹐他也跟我講了一些關於立陶宛的得意事情。都是很好的故事題材。
跟我打了個照面﹐便匆匆和老婆一起離開了酒館。
也遇到了一位貓女郎。我猜不到那是誰﹐只知道是一個男人來。他說﹐我聽過你的名字。A F**KING FUNNY MAN。我笑著回答﹐漂亮的女孩啊﹗才一半正確﹗我恐怕﹐他們介紹我給你認識的時候﹐不會說我是一個有趣的人。說畢﹐我們都相擁而笑。我當然也按了一下貓女郎的胸。碰巧﹐JENNIFER經過。她指著我說﹐看看你在做什麼﹖她是三樓的同事﹐沒有什麼妝扮。JENNIFER不是特別漂亮﹐不過很有一點獨特的女人味。上次到CO CARLOW旅行﹐我見到她跟ENDA打得很滾熱。
當然﹐也見到ENDA。他是派對的搞手。他以聰明笨伯的形像走來走去。我們一見面﹐少不免JAM一JAM OASIS的歌。突然﹐有一隻大熊跑來襲擊我。一時反應不及﹐中了他兩記勾拳。他戴著那個密不透風的毛茸茸頭罩﹐實在沒有可能知道是誰。多說幾句話﹐方猜到是BRENDON。他也是一個OASIS的歌迷。ENDA也介紹了幾個女孩給我認識。他依然是那一句開場白﹕DO YOU KNOW THIS MAN?HE'S A LEGEND!THAT'S MAN.
忽然聽到AIDAN叫喚﹐只見到一個科學怪人向我招手。原來﹐AIDAN要跟我介紹一個超級愛華頓擁躉。是他的朋友。因為實在太吵﹐聽不清楚他的名字。姑且叫做E罷。
E很奇怪﹐我竟然會是EVERTON的球迷。我說﹐自1986年起了。那時候﹐我們還是英國冠軍。AIDAN立即說﹐怎麼你們曾經是英國冠軍﹖也不用我開口﹐E已經搶著道﹐也跟你的皇家馬德里一樣罷。都曾經是國內聯賽冠軍。我們當然談了很多足球的事情。我跟他們說﹐上星期到EMIRATES STADIUM的經歷。E提議說﹐你應該到GOODISON去。上季﹐我們一行五人﹐便走了去看EVERTON v CHARLTON。
AIDAN曾經跟我說過那次旅程。他說﹐也可以到BOX OFFICE買票。不過﹐只能是那些次一級球隊的賽事。我說﹐我最想看的倒是MERSEYSIDE DERBY。
奈何你們不能面對REAL MADRID。AIDAN扮作感嘆道。
我和E即時異口同聲說﹐留待明年﹗我還補充了一句﹕IN THE CHAMPIONS LEAGUE FINAL。
突然傳來一陣掌聲。原來﹐貓女郎贏得了化妝大獎。當他上前拿去獎項的時候﹐我方知道﹐他是結構部的頭目KENNY MASON。
之後﹐大家繼續跳舞飲酒。
到上床睡覺﹐已經過了四點鐘罷﹖
Saturday, November 04, 2006
我相信﹐對於未能在主場擊敗愛華頓﹐阿仙奴的球迷一定很失望。有人開始向THIERRY HENRY柴台﹐他們以為這位阿仙奴隊長應該多點起腳射門。一個星期前﹐他們作客READING,談笑用兵下﹐輕取那隊升班馬四球。他們以為﹐球員在這樣好的狀態下﹐一定可以漂亮地在新球場多添一場勝仗。
假如他們真的這樣想﹐天註定事與願違。要知道﹐實在沒有一隊英國球隊面對EVERTON,可以輕易言勝。
況且﹐我們有一個智多星領隊。
利物浦的領隊喜歡星期美點﹐每一場比賽都會派遣不同球員上陣﹐除了陣式外﹐沒有一樣東西是CONSTANT;DAVID MOYES則剛好相反﹐愛華頓的陣容早已有一條主幹﹐只是面對不同對手﹐有不同陣式。能夠成功運用﹐因為我們的球員都很全面。每一個球員都可以踢不同位置。例如﹐ARTETA便既可做中場指揮﹐也可以擔當右翼。跟LFC完全是兩樣。有評論以為﹐利物浦今屆表現走樣﹐多少是領隊老是要中路大將GERRARD串演右中場有關。
有些事情不是可以隨便學曉。總要一點點本領。
也許﹐上星期六﹐妹妹的那兩個同事還以為阿仙奴未能贏得比賽﹐主要是愛華頓屯重兵在後防﹐完全密不透風﹐使他們的星級前鋒未能突圍。不過﹐只要看看星期三那場歐聯比賽﹐他們應該知道自己的弱點在那裡。便是面對空門﹐他們也未能把球送進球門裡面。不只一次﹐竟然是駭人地兩次。倫敦時報說﹐只有到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akoU8zUoHM)看看那些MISSES OF THE CENTURY,阿仙奴球員方能找到些少安慰。
始終﹐事實勝於雄辯。我實在不用太費唇舌跟他們﹐以至ARSÈNE WEGNER辯論。BBC以至THE TIMES也不用為愛華頓辯護。便讓HENRY繼續自我陶醉地發表他的謬論﹕假如只為聯賽分數踢球﹐我毋寧死(I WOULD RATHER DIE THAN PLAY THAT TYPE OF FOOTBALL)。
聽了這句話後﹐我不知道NICK HORNBY有什麼想法。NICK HORNBY是一個英國作家。他是一個超級阿仙奴擁躉。他寫了一本書﹐叫FEVER PITCH,講的是他做GUNNER的喜怒哀樂。有朋友一邊讀那本書﹐一邊想起了我。她說﹐你跟小說裡的主角﹐竟然是多麼的相似﹗完全是你的倒影。
我沒有讀過那本書﹐只看過改編那部小說的電影。我不能不同意那位朋友的話。跟NICK HORNBY一樣﹐我也把擁護的球會看做自己的生命。
電影終結﹐是阿仙奴如何在球季的最後一秒多入一球﹐使他們以較佳的得失球﹐壓倒LFC捧走聯賽冠軍。那一年﹐的確是英國聯賽最戲劇化的一年。假如當年阿仙奴只踢漂亮足球﹐他們能否反壓利物浦﹐實在是一個疑問。還記得﹐那時候﹐兵工廠另有一個花名﹐叫BORING ARSENAL。
離開球場﹐我們走到了較遠的FINSBURY PARK STATION乘地鐵到LEICESTER SQUARE。因為HOLLOWAY STATION和ARSENAL STATION都擠滿了人。我想起了有一次看完南華的比賽後﹐便由大球場走到灣仔地鐵站。因為銅鑼灣站早已擠得水泄不通。那時候﹐香港聯賽還有兩萬多人入場觀看。
地鐵裡﹐妹妹說﹐現場看球賽果然與別不同﹐很令人難忘。尤其那些阿仙奴球迷﹐他們的確很投入地擁護自己的球隊。坐在我們前面的那個男人﹐便喊到臉紅耳赤﹐聲音也快要失掉。
我沒有說話﹐只是微笑。似乎她已很久未有跟我一起看過球賽了。知道嗎﹖整個下午﹐我都很想跳入那群藍色的人海裡面﹐跟他們一起唱歌跳舞。我也可以為我支持的球隊﹐喊得失掉聲音。
假若要我再次跟敵對球迷一起看球賽﹐我毋寧死(I WOULD RATHER DIE THAN WATCH A FOOTBALL MATCH WITH OPPOSITION FANS)。因為我失去了看球賽最重要的部份。如同失去了自由一樣。
(EMIRATES STADIUM二之二)
假如他們真的這樣想﹐天註定事與願違。要知道﹐實在沒有一隊英國球隊面對EVERTON,可以輕易言勝。
況且﹐我們有一個智多星領隊。
利物浦的領隊喜歡星期美點﹐每一場比賽都會派遣不同球員上陣﹐除了陣式外﹐沒有一樣東西是CONSTANT;DAVID MOYES則剛好相反﹐愛華頓的陣容早已有一條主幹﹐只是面對不同對手﹐有不同陣式。能夠成功運用﹐因為我們的球員都很全面。每一個球員都可以踢不同位置。例如﹐ARTETA便既可做中場指揮﹐也可以擔當右翼。跟LFC完全是兩樣。有評論以為﹐利物浦今屆表現走樣﹐多少是領隊老是要中路大將GERRARD串演右中場有關。
有些事情不是可以隨便學曉。總要一點點本領。
也許﹐上星期六﹐妹妹的那兩個同事還以為阿仙奴未能贏得比賽﹐主要是愛華頓屯重兵在後防﹐完全密不透風﹐使他們的星級前鋒未能突圍。不過﹐只要看看星期三那場歐聯比賽﹐他們應該知道自己的弱點在那裡。便是面對空門﹐他們也未能把球送進球門裡面。不只一次﹐竟然是駭人地兩次。倫敦時報說﹐只有到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akoU8zUoHM)看看那些MISSES OF THE CENTURY,阿仙奴球員方能找到些少安慰。
始終﹐事實勝於雄辯。我實在不用太費唇舌跟他們﹐以至ARSÈNE WEGNER辯論。BBC以至THE TIMES也不用為愛華頓辯護。便讓HENRY繼續自我陶醉地發表他的謬論﹕假如只為聯賽分數踢球﹐我毋寧死(I WOULD RATHER DIE THAN PLAY THAT TYPE OF FOOTBALL)。
聽了這句話後﹐我不知道NICK HORNBY有什麼想法。NICK HORNBY是一個英國作家。他是一個超級阿仙奴擁躉。他寫了一本書﹐叫FEVER PITCH,講的是他做GUNNER的喜怒哀樂。有朋友一邊讀那本書﹐一邊想起了我。她說﹐你跟小說裡的主角﹐竟然是多麼的相似﹗完全是你的倒影。
我沒有讀過那本書﹐只看過改編那部小說的電影。我不能不同意那位朋友的話。跟NICK HORNBY一樣﹐我也把擁護的球會看做自己的生命。
電影終結﹐是阿仙奴如何在球季的最後一秒多入一球﹐使他們以較佳的得失球﹐壓倒LFC捧走聯賽冠軍。那一年﹐的確是英國聯賽最戲劇化的一年。假如當年阿仙奴只踢漂亮足球﹐他們能否反壓利物浦﹐實在是一個疑問。還記得﹐那時候﹐兵工廠另有一個花名﹐叫BORING ARSENAL。
離開球場﹐我們走到了較遠的FINSBURY PARK STATION乘地鐵到LEICESTER SQUARE。因為HOLLOWAY STATION和ARSENAL STATION都擠滿了人。我想起了有一次看完南華的比賽後﹐便由大球場走到灣仔地鐵站。因為銅鑼灣站早已擠得水泄不通。那時候﹐香港聯賽還有兩萬多人入場觀看。
地鐵裡﹐妹妹說﹐現場看球賽果然與別不同﹐很令人難忘。尤其那些阿仙奴球迷﹐他們的確很投入地擁護自己的球隊。坐在我們前面的那個男人﹐便喊到臉紅耳赤﹐聲音也快要失掉。
我沒有說話﹐只是微笑。似乎她已很久未有跟我一起看過球賽了。知道嗎﹖整個下午﹐我都很想跳入那群藍色的人海裡面﹐跟他們一起唱歌跳舞。我也可以為我支持的球隊﹐喊得失掉聲音。
假若要我再次跟敵對球迷一起看球賽﹐我毋寧死(I WOULD RATHER DIE THAN WATCH A FOOTBALL MATCH WITH OPPOSITION FANS)。因為我失去了看球賽最重要的部份。如同失去了自由一樣。
(EMIRATES STADIUM二之二)
Friday, November 03, 2006
未能在EMIRATES STADIUM首次全場滿座下贏得比賽,阿仙奴領隊ARSÈNE WEGNER竟然把對自己球隊的不滿﹐發泄在對手身上。在賽後的記者招待會裡﹐他說﹐望著愛華頓的消極打法﹐便如同把一部古老電影看完又看﹐看完又看﹐實在極為沉悶。
上星期六﹐愛華頓第一次踏足ARSENAL的新主場﹐成功地瓦解了兵工廠的多翻攻勢﹐奪得了一分。也許﹐正如WEGNER所想﹐我們應該高興﹐因為我們能夠在客場搶走阿仙奴一分。不過﹐老實說﹐看完比賽後﹐我有點失望。因為我們如此輕易丟了兩分。
是銀行假期﹐我如常到了倫敦。本來﹐我是打算去利物浦。我很想很想到GOODISON PARK欣賞愛華頓的比賽。只是﹐英國足總並沒有考慮過我這個都柏林的EVERTONIAN,竟然在愛爾蘭的BANK HOLIDAY安排了他們到首都比賽。查清楚開賽時間後﹐我立即要妹妹幫忙。我希望她能夠幫我找到兩張門票﹐讓我到EMIRATES STADIUM支持愛華頓。很容易也很不容易下﹐我們花了九十英鎊﹐透過她的同事﹐從阿仙奴球迷會得來兩張入場券。
她那個同事是兵工廠的忠實擁躉﹐是季票持有人。那兩張門票是他向其他SEASON TICKET HOLDERS買的。縱然持有季票﹐也不是每一場比賽都有空到球場去的。
我原本準備穿愛華頓的球衣到球場。只是最後還是聽聽妹妹的勸告﹐改穿了其他衣服。因為我們坐的位置﹐是季票持有人的座位。她說﹐我早跟你問清楚我的同事。他們忠告﹐最好避免做萬紅中的一點藍。因為那些超級球迷的行徑﹐都不是一般人想像得到。
其實﹐有什麼超級球迷的行徑﹐我會想像不到。我本身便是一個超級球迷。只是﹐考慮了片刻﹐我想﹐我還是無謂把自己放到一個困難的境地。於是﹐我便把那件愛華頓球衣折好﹐輕吻了一下胸前的那個會徽﹐才出門口去。我希望我能夠帶給愛華頓好運。妹妹約了她的同事在HOLLOWAY STATION等候。只是﹐可能人多關係﹐警察把那個地鐵站封了。我們最後還是要從ARSENAL STATION走到球場。EMIRATES STADIUM其實在這兩個站中間。
不難想像﹐整個球場都是一片紅海。除了球門後面那一小撮藍色的人群。
我們很早便打開了記錄。是TIM CAHILL的敏銳射門觸覺。場刊是這樣介紹這個澳洲人﹕EXCELLENT AT STEALING INTO THE BOX UNNOTICED,HE IS ALSO OUTSTANDING IN THE AIR。
縱然落後一球﹐阿仙奴的球迷依然很有信心。他們不斷地唱歌﹐不斷地叫喊﹐似乎記不起﹐兩季前﹐我們是1︰0的專家。那一年﹐我們最後在聯賽排行第四。
望著愛華頓很有組織的防守﹐我知道﹐我們很有機會成為第一隊在EMIRATES STADIUM贏ARSENAL的球隊。那些穿著紅衣的球員只能夠在禁區外面漂亮地左交右傳﹐鮮有一次直接的攻門。印象中﹐TIM HOWARD只需要扑救兩球。隨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附近的阿仙奴球迷開始焦急起來。他們開始針對著球門後面那一群愛華頓球迷。他們開始指罵著那堆藍色人群。
我們最後未能全取三分。因為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全場比賽唯一的一個錯誤﹕我們排人牆時﹐竟然空了中間一個位置。便是那個空位﹐讓兵工廠的那個直接罰球成為入球。
離開球場的時候﹐妹妹的同事跟我說﹐你應該很滿意這場比賽罷﹖
我搖頭道﹐很失望地失掉了寶貴的兩分。這很影響我們爭取冠軍。
我看到他有點氣。他回答說﹐只是你們根本沒有射門。全場比賽﹐都是我們的天下。
整個九十分鐘﹐也沒有出過聲音﹐我當然不甘示弱。假如足球比賽是計算控球﹐那麼我會承認你們是贏得了這場比賽。只是﹐我們一次的攻門﹐你們也抵擋不住啊﹗
(Emirates Stadium 二之一)
上星期六﹐愛華頓第一次踏足ARSENAL的新主場﹐成功地瓦解了兵工廠的多翻攻勢﹐奪得了一分。也許﹐正如WEGNER所想﹐我們應該高興﹐因為我們能夠在客場搶走阿仙奴一分。不過﹐老實說﹐看完比賽後﹐我有點失望。因為我們如此輕易丟了兩分。
是銀行假期﹐我如常到了倫敦。本來﹐我是打算去利物浦。我很想很想到GOODISON PARK欣賞愛華頓的比賽。只是﹐英國足總並沒有考慮過我這個都柏林的EVERTONIAN,竟然在愛爾蘭的BANK HOLIDAY安排了他們到首都比賽。查清楚開賽時間後﹐我立即要妹妹幫忙。我希望她能夠幫我找到兩張門票﹐讓我到EMIRATES STADIUM支持愛華頓。很容易也很不容易下﹐我們花了九十英鎊﹐透過她的同事﹐從阿仙奴球迷會得來兩張入場券。
她那個同事是兵工廠的忠實擁躉﹐是季票持有人。那兩張門票是他向其他SEASON TICKET HOLDERS買的。縱然持有季票﹐也不是每一場比賽都有空到球場去的。
我原本準備穿愛華頓的球衣到球場。只是最後還是聽聽妹妹的勸告﹐改穿了其他衣服。因為我們坐的位置﹐是季票持有人的座位。她說﹐我早跟你問清楚我的同事。他們忠告﹐最好避免做萬紅中的一點藍。因為那些超級球迷的行徑﹐都不是一般人想像得到。
其實﹐有什麼超級球迷的行徑﹐我會想像不到。我本身便是一個超級球迷。只是﹐考慮了片刻﹐我想﹐我還是無謂把自己放到一個困難的境地。於是﹐我便把那件愛華頓球衣折好﹐輕吻了一下胸前的那個會徽﹐才出門口去。我希望我能夠帶給愛華頓好運。妹妹約了她的同事在HOLLOWAY STATION等候。只是﹐可能人多關係﹐警察把那個地鐵站封了。我們最後還是要從ARSENAL STATION走到球場。EMIRATES STADIUM其實在這兩個站中間。
不難想像﹐整個球場都是一片紅海。除了球門後面那一小撮藍色的人群。
我們很早便打開了記錄。是TIM CAHILL的敏銳射門觸覺。場刊是這樣介紹這個澳洲人﹕EXCELLENT AT STEALING INTO THE BOX UNNOTICED,HE IS ALSO OUTSTANDING IN THE AIR。
縱然落後一球﹐阿仙奴的球迷依然很有信心。他們不斷地唱歌﹐不斷地叫喊﹐似乎記不起﹐兩季前﹐我們是1︰0的專家。那一年﹐我們最後在聯賽排行第四。
望著愛華頓很有組織的防守﹐我知道﹐我們很有機會成為第一隊在EMIRATES STADIUM贏ARSENAL的球隊。那些穿著紅衣的球員只能夠在禁區外面漂亮地左交右傳﹐鮮有一次直接的攻門。印象中﹐TIM HOWARD只需要扑救兩球。隨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附近的阿仙奴球迷開始焦急起來。他們開始針對著球門後面那一群愛華頓球迷。他們開始指罵著那堆藍色人群。
我們最後未能全取三分。因為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全場比賽唯一的一個錯誤﹕我們排人牆時﹐竟然空了中間一個位置。便是那個空位﹐讓兵工廠的那個直接罰球成為入球。
離開球場的時候﹐妹妹的同事跟我說﹐你應該很滿意這場比賽罷﹖
我搖頭道﹐很失望地失掉了寶貴的兩分。這很影響我們爭取冠軍。
我看到他有點氣。他回答說﹐只是你們根本沒有射門。全場比賽﹐都是我們的天下。
整個九十分鐘﹐也沒有出過聲音﹐我當然不甘示弱。假如足球比賽是計算控球﹐那麼我會承認你們是贏得了這場比賽。只是﹐我們一次的攻門﹐你們也抵擋不住啊﹗
(Emirates Stadium 二之一)
Thursday, November 02, 2006
不經不覺﹐原來已經在愛爾蘭住上了半年﹐經歷了三個季節。
我不敢說﹐這六個月﹐我的得比失的多。假如我說「得比失多」﹐那是騙人的話。不過﹐假如我說「失比得多」﹐那也是騙人的話。因為這一段日子﹐我都只在都柏林生活﹐根本無從跟香港的生活比較。我不會知道假若這六個月我留在香港﹐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從來﹐歷史就沒有什麼WHAT IFS。
所以﹐每當聽到中國領導人一而再﹐再而三說﹐「要不是當年平息了天安門的風波﹐中國的經濟就不能這樣欣欣向榮」的論調時﹐我都感到作嘔。
因為那顯然是騙人的話。
你怎可能知道﹐假如沒有天安門屠殺﹐中國的經濟就不能比現在更欣欣向榮﹖你怎可能知道﹐假如那場政治上的風波沒有給武力平息﹐中國就不能比現在更發達﹐貧富懸殊就沒有現在這麼嚴重﹖
我們讀理科出生的領導﹐請你說說﹐你究竟憑什麼知道﹖你的邏輯是什麼﹖
無奈地﹐也反智地﹐「要不是當年平息了天安門的風波﹐中國的經濟就不能這樣欣欣向榮」這個理論﹐很受現在那些已得利益者的認同。
在《誰﹐不是天安門母親》一文裡面﹐龍應台寫下了這樣的一個經歷﹕早前﹐她在香港出席了一個高貴的晚宴﹐碰上了一個剛從美國留學歸來的上海女性。在香港一間公司任經理。她姿態優雅地用英語跟龍應台道﹕「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的過程裡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的確﹐中國的繁榮很清楚地在這群已得利益者身上呈現出來。中國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與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也許﹐他們並不是一無所知。因為對於自己國家屠殺人民的事情﹐怎不可能一無所知﹖然而﹐在物質追逐的遊戲裡面﹐他們早已接受了這一個邏輯﹕沒有鎮壓﹐便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
只是﹐這樣下去﹐對於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將不再存在﹐天安門屠殺就從來沒有發生。
只是﹐這樣下去﹐跟日本刪改歷史教科書有什麼分別﹖我們一方面要日本尊重歷史﹐一方面卻又左閃右躲﹐逃避那個自己一手做成的傷口。我們怎能名正言順地要日本認真對待他們侵華的歷史﹖我們又怎能強而有力地譴責他們無故刪改歷史教科書﹖
對於自己民族的歷史也不尊重﹐我們又如何能要求別人尊重我們﹖
假如有一天﹐我們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要從外國小朋友的歷史書裡面﹐方能得知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國北京天安門發生了什麼事情﹐便是有著越來越多的高樓﹑塞滿了汽車的公路﹑人頭湧湧的商場﹑飛彈戰機都精良耀眼﹑奧運世博國威赫赫﹐我們又有什麼值得自豪﹖
假如真的有這一天。
我不敢說﹐這六個月﹐我的得比失的多。假如我說「得比失多」﹐那是騙人的話。不過﹐假如我說「失比得多」﹐那也是騙人的話。因為這一段日子﹐我都只在都柏林生活﹐根本無從跟香港的生活比較。我不會知道假若這六個月我留在香港﹐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從來﹐歷史就沒有什麼WHAT IFS。
所以﹐每當聽到中國領導人一而再﹐再而三說﹐「要不是當年平息了天安門的風波﹐中國的經濟就不能這樣欣欣向榮」的論調時﹐我都感到作嘔。
因為那顯然是騙人的話。
你怎可能知道﹐假如沒有天安門屠殺﹐中國的經濟就不能比現在更欣欣向榮﹖你怎可能知道﹐假如那場政治上的風波沒有給武力平息﹐中國就不能比現在更發達﹐貧富懸殊就沒有現在這麼嚴重﹖
我們讀理科出生的領導﹐請你說說﹐你究竟憑什麼知道﹖你的邏輯是什麼﹖
無奈地﹐也反智地﹐「要不是當年平息了天安門的風波﹐中國的經濟就不能這樣欣欣向榮」這個理論﹐很受現在那些已得利益者的認同。
在《誰﹐不是天安門母親》一文裡面﹐龍應台寫下了這樣的一個經歷﹕早前﹐她在香港出席了一個高貴的晚宴﹐碰上了一個剛從美國留學歸來的上海女性。在香港一間公司任經理。她姿態優雅地用英語跟龍應台道﹕「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的過程裡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的確﹐中國的繁榮很清楚地在這群已得利益者身上呈現出來。中國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與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也許﹐他們並不是一無所知。因為對於自己國家屠殺人民的事情﹐怎不可能一無所知﹖然而﹐在物質追逐的遊戲裡面﹐他們早已接受了這一個邏輯﹕沒有鎮壓﹐便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
只是﹐這樣下去﹐對於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將不再存在﹐天安門屠殺就從來沒有發生。
只是﹐這樣下去﹐跟日本刪改歷史教科書有什麼分別﹖我們一方面要日本尊重歷史﹐一方面卻又左閃右躲﹐逃避那個自己一手做成的傷口。我們怎能名正言順地要日本認真對待他們侵華的歷史﹖我們又怎能強而有力地譴責他們無故刪改歷史教科書﹖
對於自己民族的歷史也不尊重﹐我們又如何能要求別人尊重我們﹖
假如有一天﹐我們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要從外國小朋友的歷史書裡面﹐方能得知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國北京天安門發生了什麼事情﹐便是有著越來越多的高樓﹑塞滿了汽車的公路﹑人頭湧湧的商場﹑飛彈戰機都精良耀眼﹑奧運世博國威赫赫﹐我們又有什麼值得自豪﹖
假如真的有這一天。
Wednesday, November 01, 2006
大老闆看中了FINGAL COUNTY的一個供水改善計劃﹐希望能夠獲得這個顧問合約。於是﹐近幾天﹐上司AOIFE便跟我一起努力準備那份SUBMISSION,好讓COUNTY COUNCIL考慮我們的初步建議。可能人口密集的關係﹐縱然那麼小﹐CO DUBLIN也細分了幾個COUNTY COUNCILS。FINGAL COUNTY便是北面的那個區域。除了機場和幾個小鎮(如HOWTH,SWORD和MALAHIDE)外﹐那兒都是鄉郊的地方﹐只得一些農場與村莊。
要做一個供水改善計劃的SUBMISSION,當然首先要了解現在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也要知道將來發展藍圖﹐好讓新的計劃能夠配合﹐使未來二十年有充足食水供應。
我負責未來需求那個部份。於是﹐便找來一些人口調查﹑發展報告之類的東西來讀﹐以評估將來的用水量。在那個未來二十年的發展大綱裡面﹐FINGAL COUNTY定下了一些發展理念。他們估計FINGAL COUNTY的人口在2021年將會暴升三倍。他們說﹐那些綠油油的鄉村農莊都要保留。因為都是古老特色的建築。尤其那些十八世紀興建的村屋﹐它們週邊的一切都不能破壞﹐要保持原有風貌。要興建新的住宅屋苑﹐都只能在那幾個人口開始稠密的鎮。
翻閱翻閱著﹐我不其然想起了北京的衚衕和上海的里弄。同樣是將來的發展﹐都柏林跟北京走的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
為了零八年的奧運﹐大量大量的衚衕和四合院正在拆卸。兩年後﹐這個中國的首都﹐再不會是一個歷史古城。當世人把焦點都對準了這座名城﹐他們會發現這是一個很現代化的城市。有很多很多設計新穎的摩天大廈﹐有很多很多先進的集體運輸交通工具。都處都是現代人成就的驕傲表現﹐四週都是高科技﹑超現實的都市景觀。跟想像中的鐵幕國家完全扯不上一絲關係。也許﹐這是很多人都覺得自豪的地方。因為中國人終於站起來。
的確﹐我們終於站起來。
我們似乎真的跟國際越來越近。經過了二十年的努力﹐北京人終於可以擺脫衚衕的落後﹐搬到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居住。那兒有抽水馬桶﹐有衛生的食水﹐有電暖爐。中國人終於可以過現代人的生活。猶記得﹐那個回歸後突然轉呔的前民主派人士﹐便在《信報》為清拆衚衕和四合院﹐替北京辯護。他寫道﹐堅持保留衚衕和四合院的人﹐都很自私。因為他們粗暴地把自己一己的浪漫思想﹐強加到那些生活在衛生環境欠佳的人身上。因為興建在百多年前﹐很多四合院都沒有抽水馬桶。現在清拆了﹐好讓那些居民都能夠上樓﹐實在是一大德政。
假如反對清拆衚衕和四合院﹐都是自私的行為﹐那麼﹐我不得不承認﹐我是一個極度自私的人。
假如一幢幢的高樓大廈方是現代化的象征﹐那麼﹐愛爾蘭以至整個歐洲都是太落後了。
那天晚上﹐下班回家﹐臨睡的時候﹐再次重溫了龍應台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裡面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傳統的氣質氛圍﹐並不是一種膚淺的懷舊情懷。當人的成就像氫氣球一樣向不可知的無限高空飛展﹐傳統便是綁著氫氣球的那根粗繩﹐緊連著土地。它使你仍舊樸實地面對生老病死﹐它使你仍舊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腳仍舊踩得著泥土。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
越先進的國家﹐越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傳統﹔傳統保護得越好﹐對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後的國家﹐傳統的流失或支離破碎就越厲害﹐對自己的定位與前景越是手足無措﹐進退失據」。
也許﹐中國人是站起來了。只是﹐他們不知道的是﹐他們正站在一個沒有根基的地面上面。泥土下面﹐都給淘空了。
要做一個供水改善計劃的SUBMISSION,當然首先要了解現在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也要知道將來發展藍圖﹐好讓新的計劃能夠配合﹐使未來二十年有充足食水供應。
我負責未來需求那個部份。於是﹐便找來一些人口調查﹑發展報告之類的東西來讀﹐以評估將來的用水量。在那個未來二十年的發展大綱裡面﹐FINGAL COUNTY定下了一些發展理念。他們估計FINGAL COUNTY的人口在2021年將會暴升三倍。他們說﹐那些綠油油的鄉村農莊都要保留。因為都是古老特色的建築。尤其那些十八世紀興建的村屋﹐它們週邊的一切都不能破壞﹐要保持原有風貌。要興建新的住宅屋苑﹐都只能在那幾個人口開始稠密的鎮。
翻閱翻閱著﹐我不其然想起了北京的衚衕和上海的里弄。同樣是將來的發展﹐都柏林跟北京走的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
為了零八年的奧運﹐大量大量的衚衕和四合院正在拆卸。兩年後﹐這個中國的首都﹐再不會是一個歷史古城。當世人把焦點都對準了這座名城﹐他們會發現這是一個很現代化的城市。有很多很多設計新穎的摩天大廈﹐有很多很多先進的集體運輸交通工具。都處都是現代人成就的驕傲表現﹐四週都是高科技﹑超現實的都市景觀。跟想像中的鐵幕國家完全扯不上一絲關係。也許﹐這是很多人都覺得自豪的地方。因為中國人終於站起來。
的確﹐我們終於站起來。
我們似乎真的跟國際越來越近。經過了二十年的努力﹐北京人終於可以擺脫衚衕的落後﹐搬到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居住。那兒有抽水馬桶﹐有衛生的食水﹐有電暖爐。中國人終於可以過現代人的生活。猶記得﹐那個回歸後突然轉呔的前民主派人士﹐便在《信報》為清拆衚衕和四合院﹐替北京辯護。他寫道﹐堅持保留衚衕和四合院的人﹐都很自私。因為他們粗暴地把自己一己的浪漫思想﹐強加到那些生活在衛生環境欠佳的人身上。因為興建在百多年前﹐很多四合院都沒有抽水馬桶。現在清拆了﹐好讓那些居民都能夠上樓﹐實在是一大德政。
假如反對清拆衚衕和四合院﹐都是自私的行為﹐那麼﹐我不得不承認﹐我是一個極度自私的人。
假如一幢幢的高樓大廈方是現代化的象征﹐那麼﹐愛爾蘭以至整個歐洲都是太落後了。
那天晚上﹐下班回家﹐臨睡的時候﹐再次重溫了龍應台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裡面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傳統的氣質氛圍﹐並不是一種膚淺的懷舊情懷。當人的成就像氫氣球一樣向不可知的無限高空飛展﹐傳統便是綁著氫氣球的那根粗繩﹐緊連著土地。它使你仍舊樸實地面對生老病死﹐它使你仍舊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腳仍舊踩得著泥土。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
越先進的國家﹐越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傳統﹔傳統保護得越好﹐對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後的國家﹐傳統的流失或支離破碎就越厲害﹐對自己的定位與前景越是手足無措﹐進退失據」。
也許﹐中國人是站起來了。只是﹐他們不知道的是﹐他們正站在一個沒有根基的地面上面。泥土下面﹐都給淘空了。
Tuesday, October 31, 2006
朋友到歐洲遊玩﹐順道經都柏林來探訪﹐竟然還帶來了不少禮物﹐實在有點意料不及。至少﹐那些即食麵可以吃到明年今日。
他們也給我買了幾本中文書。有林行止先生的最新出版。也有一本散文集﹐叫《香港﹐有幾香﹖》﹐作者是張專。我不知道她是誰。朋友說﹐她就是舊時民建聯白頭佬的現任老婆。聽到民建聯三個字﹐便對這本書有點生厭。不過﹐大便的時候﹐翻閱過幾篇﹐倒覺得有趣。都是中國大陸人寫自己在香港的生活。於是﹐幾次大便後﹐竟然也把整本書讀完。
最興奮的﹐當然是收到龍應台的新書《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朋友的女朋友把書交給我道﹐我不認識她。不過﹐他說﹐她是你喜歡的作家。她指著她自己的男朋友。
想不到﹐他還記得我喜歡的作家。那天﹐我跟他逛過旺角所有樓上書店﹐便是為了找《野火集》。
《野火集》是龍應台的成名作。出版於一九八五年。那時候﹐台灣還在戒嚴﹐還實行報禁。一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的個人投書﹐成為了一股燎原野火。藉著口碑﹑影印本和大字報﹐龍應台成為了推動社會說真話的能量來源。《野火集》出版後不夠一個月﹐便再版了二十四次。有人說﹐《野火集》是一個時代的共同符號。
離開香港到愛爾蘭生活﹐我只在書櫃裡帶走了兩本書隨身。一中一英。一本是TRUMAN CAPOTE的IN COLD BLOOD,另一本便是《野火集》。
香港的作家﹐我喜歡的是陶傑。台灣那邊﹐我喜歡的就是龍應台。以前﹐我也喜歡李敖。不過﹐自從他跟中國共產黨互拋媚眼後﹐我發覺﹐他已再沒有我喜歡的地方。他已變成了共產黨中宣部的一員。從來﹐我都很討厭走狗。
翻閱著龍女士的文章﹐縱然她寫的都是發生在台灣的事情﹐我總覺得﹐把文章裡面的「台灣」改為「香港」﹐或者「中國」﹐也一樣合適。也許﹐因為台灣﹑香港與中國﹐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
「你怎麼能夠不生氣﹖你怎麼還有良心躲在角落裡做沉默的大多數﹖你以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為你不生氣﹑你忍耐﹑你退讓﹐所以攤販把你的家搞得像個破落大雜院﹐所以市內交通一團烏煙瘴氣﹐所以河流是條爛腸子。今天﹐你不生氣﹐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完全把道理說到我的心坎裡。從小﹐我便知道﹐不平則鳴。
MARIA也是這樣的人。
最近﹐小妮子發覺都柏林一間購物中心的禮券﹐要每個月收三歐羅行政費﹐都在那張禮券來扣除。那表示﹐假如你今年一月買了一張價值三十六塊的禮券﹐到聖誕的時候﹐那張禮券已變得毫無價值。因為三十六塊全部都用來做了行政費。於是﹐除了用電郵廣告全公司外﹐她還把消息發放予電臺﹐要他們幫忙跟進。她很勞氣地說﹐完全沒有理由啊﹗
聽著她的投訴﹐我又想起了兩個月前﹐她跟IT部爭論傳真機位置的事情。那天﹐她要公司安全部主管﹐親自來命令IT部轉換FAX MACHINE的位置。因為擺放得太高了﹐生得矮小的員工根本不能輕易用到﹐這樣實在危害到他們的安全。
他們也給我買了幾本中文書。有林行止先生的最新出版。也有一本散文集﹐叫《香港﹐有幾香﹖》﹐作者是張專。我不知道她是誰。朋友說﹐她就是舊時民建聯白頭佬的現任老婆。聽到民建聯三個字﹐便對這本書有點生厭。不過﹐大便的時候﹐翻閱過幾篇﹐倒覺得有趣。都是中國大陸人寫自己在香港的生活。於是﹐幾次大便後﹐竟然也把整本書讀完。
最興奮的﹐當然是收到龍應台的新書《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朋友的女朋友把書交給我道﹐我不認識她。不過﹐他說﹐她是你喜歡的作家。她指著她自己的男朋友。
想不到﹐他還記得我喜歡的作家。那天﹐我跟他逛過旺角所有樓上書店﹐便是為了找《野火集》。
《野火集》是龍應台的成名作。出版於一九八五年。那時候﹐台灣還在戒嚴﹐還實行報禁。一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的個人投書﹐成為了一股燎原野火。藉著口碑﹑影印本和大字報﹐龍應台成為了推動社會說真話的能量來源。《野火集》出版後不夠一個月﹐便再版了二十四次。有人說﹐《野火集》是一個時代的共同符號。
離開香港到愛爾蘭生活﹐我只在書櫃裡帶走了兩本書隨身。一中一英。一本是TRUMAN CAPOTE的IN COLD BLOOD,另一本便是《野火集》。
香港的作家﹐我喜歡的是陶傑。台灣那邊﹐我喜歡的就是龍應台。以前﹐我也喜歡李敖。不過﹐自從他跟中國共產黨互拋媚眼後﹐我發覺﹐他已再沒有我喜歡的地方。他已變成了共產黨中宣部的一員。從來﹐我都很討厭走狗。
翻閱著龍女士的文章﹐縱然她寫的都是發生在台灣的事情﹐我總覺得﹐把文章裡面的「台灣」改為「香港」﹐或者「中國」﹐也一樣合適。也許﹐因為台灣﹑香港與中國﹐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
「你怎麼能夠不生氣﹖你怎麼還有良心躲在角落裡做沉默的大多數﹖你以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為你不生氣﹑你忍耐﹑你退讓﹐所以攤販把你的家搞得像個破落大雜院﹐所以市內交通一團烏煙瘴氣﹐所以河流是條爛腸子。今天﹐你不生氣﹐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完全把道理說到我的心坎裡。從小﹐我便知道﹐不平則鳴。
MARIA也是這樣的人。
最近﹐小妮子發覺都柏林一間購物中心的禮券﹐要每個月收三歐羅行政費﹐都在那張禮券來扣除。那表示﹐假如你今年一月買了一張價值三十六塊的禮券﹐到聖誕的時候﹐那張禮券已變得毫無價值。因為三十六塊全部都用來做了行政費。於是﹐除了用電郵廣告全公司外﹐她還把消息發放予電臺﹐要他們幫忙跟進。她很勞氣地說﹐完全沒有理由啊﹗
聽著她的投訴﹐我又想起了兩個月前﹐她跟IT部爭論傳真機位置的事情。那天﹐她要公司安全部主管﹐親自來命令IT部轉換FAX MACHINE的位置。因為擺放得太高了﹐生得矮小的員工根本不能輕易用到﹐這樣實在危害到他們的安全。
Sunday, October 29, 2006
陶傑說﹐「飛機、電郵、手提電話,為人類的速度建立了新的定義。寫一封信,用口水黏好信封,到郵局去排隊,買一張郵票,貼好,親自投進信箱。一星期後,對方收到信,曾經,那一份驛馬悠悠的等待,就叫做誠意。」
假如那麼簡單的事情便是「誠意」﹐那麼﹐來了愛爾蘭後﹐我終於發現有人欣賞我的誠意。我當然也不會讓欣賞我的誠意的人失望。因為我很明白那一種失望。
曾幾何時﹐還在香港的時候﹐很喜歡把身邊的一些事情﹑心裡的一些想法﹐寫在一些紙上﹐然後投寄出去。只是﹐她似乎並不欣賞我這種作風。可能為了不鼓勵我繼續給她寄信﹐我從未有收過她的一封回覆。有一次晚飯的時候﹐她跟我說﹐曾經很想給你寫些東西。不過﹐實在太懶。況且﹐為何不見面時講﹖不在電話裡講啊﹖
為什麼﹖為什麼你會問我為什麼﹖那時候﹐我心裡就湧上了幾十萬個為什麼。
因為有些東西只適合在紙上談啊﹗有些時候﹐有些事情﹐太方便地傾訴﹐會失去了其本身的情感和意義。唯有在朦朧底下﹐我們方能感受到那獨特的氣味。沒有了那驛馬悠悠的等待﹐一切不是太過平凡了點兒嗎﹖我們的生活為何不能多一丁點趣味﹖
我想﹐沒有人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變得有趣。因為大家都不喜歡苦悶的生活。她只是不喜歡我帶給她的趣味罷了。對於她來說﹐另外一些人做另外一些的事情﹐比我寫著那些無聊的書信更有趣。我跟她對「趣味」的定義有點不同。
在PD JAMAES的DEVICES AND DESIRES裡面﹐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And did he want to be read? Certainly he wanted some people to read him, one person in particular, and having read the poems he wanted her to approve. Humiliating but true.
裡面的HE,便是偵探小說女王筆下的名探ADAM DALGLIESH。小說講到﹐他剛出版了一本詩集。
我不是一個詩人﹐不懂得寫詩。不過﹐我每天都會在這兒發表一篇又一篇又長又無聊的廢話。曾經﹐我是多麼渴望她會每天都來讀一讀我的隨筆。只是﹐有天跟她通了一趟電話﹐知道她從未有到過TOFFEELAND。那時候﹐的確有點灰心。對於生活﹐我們的看法實在很不相同。
只是想不到﹐離開香港半年後﹐我竟然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裡面有很多種字體﹐也用了很多顏色。其中﹐竟然有紅色。我沒有很用心地細讀她的話。因為我決定狠心地讓她感受一下失望。假若她會因此失望。
至於TOFFEELAND,我倒寧願她不好到這兒來。因為她本來就不屬於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只有我認識了很久的朋友和一些在這兒認識的新朋友。況且﹐便是我現在身在世界的那一個角落也不清楚﹐還談什麼TOFFEELAND啊﹗
在電話裡﹐我跟她講﹐我現在生活的地方叫都柏林。不過﹐我知道﹐她依然搞不清方向。
假如那麼簡單的事情便是「誠意」﹐那麼﹐來了愛爾蘭後﹐我終於發現有人欣賞我的誠意。我當然也不會讓欣賞我的誠意的人失望。因為我很明白那一種失望。
曾幾何時﹐還在香港的時候﹐很喜歡把身邊的一些事情﹑心裡的一些想法﹐寫在一些紙上﹐然後投寄出去。只是﹐她似乎並不欣賞我這種作風。可能為了不鼓勵我繼續給她寄信﹐我從未有收過她的一封回覆。有一次晚飯的時候﹐她跟我說﹐曾經很想給你寫些東西。不過﹐實在太懶。況且﹐為何不見面時講﹖不在電話裡講啊﹖
為什麼﹖為什麼你會問我為什麼﹖那時候﹐我心裡就湧上了幾十萬個為什麼。
因為有些東西只適合在紙上談啊﹗有些時候﹐有些事情﹐太方便地傾訴﹐會失去了其本身的情感和意義。唯有在朦朧底下﹐我們方能感受到那獨特的氣味。沒有了那驛馬悠悠的等待﹐一切不是太過平凡了點兒嗎﹖我們的生活為何不能多一丁點趣味﹖
我想﹐沒有人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變得有趣。因為大家都不喜歡苦悶的生活。她只是不喜歡我帶給她的趣味罷了。對於她來說﹐另外一些人做另外一些的事情﹐比我寫著那些無聊的書信更有趣。我跟她對「趣味」的定義有點不同。
在PD JAMAES的DEVICES AND DESIRES裡面﹐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And did he want to be read? Certainly he wanted some people to read him, one person in particular, and having read the poems he wanted her to approve. Humiliating but true.
裡面的HE,便是偵探小說女王筆下的名探ADAM DALGLIESH。小說講到﹐他剛出版了一本詩集。
我不是一個詩人﹐不懂得寫詩。不過﹐我每天都會在這兒發表一篇又一篇又長又無聊的廢話。曾經﹐我是多麼渴望她會每天都來讀一讀我的隨筆。只是﹐有天跟她通了一趟電話﹐知道她從未有到過TOFFEELAND。那時候﹐的確有點灰心。對於生活﹐我們的看法實在很不相同。
只是想不到﹐離開香港半年後﹐我竟然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裡面有很多種字體﹐也用了很多顏色。其中﹐竟然有紅色。我沒有很用心地細讀她的話。因為我決定狠心地讓她感受一下失望。假若她會因此失望。
至於TOFFEELAND,我倒寧願她不好到這兒來。因為她本來就不屬於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只有我認識了很久的朋友和一些在這兒認識的新朋友。況且﹐便是我現在身在世界的那一個角落也不清楚﹐還談什麼TOFFEELAND啊﹗
在電話裡﹐我跟她講﹐我現在生活的地方叫都柏林。不過﹐我知道﹐她依然搞不清方向。
Saturday, October 28, 2006
我想﹐冬天是正式來臨了。
早陣子﹐我已發覺越來越不願意起床上班。因為天空實在很陰沉。七點鐘的時候﹐太陽才懶洋洋地從遠處探出個頭來。閑來﹐跟MARIA談起這件事。我發現﹐原來﹐也不只是我這一個NEW DUBLINER有這個難題。她說﹐較了鐘後﹐應該會好一點。
過多兩天﹐我們將會進入冬季時間。時鐘會給較慢一個小時。現在的七點鐘﹐即是未來幾個月的六點鐘。於是﹐愛爾蘭跟香港的時差將加多一個鐘。
也許﹐那時候﹐起床會較為容易。因為太陽應該已露出半個臉來。這幾天早上﹐步行到火車站的時候﹐街燈才慢慢熄滅。我是習慣乘八時零五分那一班火車上班。
有天﹐ADRIAN問我一個問題。假如我們乘的飛機在較鐘後的那一個小時抵達﹐究竟航程說的是什麼時間呢﹖
我當然不知道如何回答。對於較鐘這一件事﹐我依然有點疑惑。只記得EDW早前說過﹐一朝醒來﹐時間便走慢了一句鐘﹐生命便多了一個小時。就是如此罷了。這是他對較鐘的解釋。EDW是我的一個朋友。在我離開香港前十個月﹐他獨自到了英國生活。
今天﹐在公司廚房碰見了FIONNUOLA﹐便跟她閑談了一會兒。好像也有一段時間沒有跟她聊過天。
坐在落地玻璃前﹐眺望著外面的IRISH SEA,我們竟然不其然談到了日落日出。
我投訴說﹐今早實在很黑﹐如同半夜醒來一樣。實在跟半夜十二點沒有分別。要不是鬧鐘還懂得響﹐我會以為自己才剛剛睡到床上。FIONNUOLA點著頭道﹐始終來到這個時候了。況且﹐今天下著大雨嘛﹗天空不陰陰沉沉才怪﹗
我回答說﹐星期天便較鐘。MARIA跟我講過﹐那時後﹐早上的天空會比較光亮。
只見FIONNUOLA有點疑惑﹐似乎我是講錯了些什麼。碰巧﹐德國人WOLFRAM經過。他也一起討論較鐘這個話題。他說﹐較鐘倒是為了方便農夫。好讓他們有多點陽光照耀的時間。
似乎﹐有點道理。不過﹐那也表示天空四點多便會日落啊﹗日照的時間其實是沒有變的罷。是從八點到五點﹐還是從七點到四點的分別。
聽到我的論點﹐FIONNUOLA竟然問道﹐怎麼﹖星期天﹐我們是向後調校一個鐘頭麼﹖我還以為是向前走一個小時。
我實在不知道如何回應。她是一個在愛爾蘭長大的女生。怎麼可能不曉得冬天的時間比夏天慢一個小時啊﹖
也許﹐有些事情見得多了﹐反而會變得有點不認識。因為我們會開始盲目。一切都那麼自然。我們又為何要去牢記﹖
我依然不知道﹐為何冬天的時間比夏天慢一個小時﹖
早陣子﹐我已發覺越來越不願意起床上班。因為天空實在很陰沉。七點鐘的時候﹐太陽才懶洋洋地從遠處探出個頭來。閑來﹐跟MARIA談起這件事。我發現﹐原來﹐也不只是我這一個NEW DUBLINER有這個難題。她說﹐較了鐘後﹐應該會好一點。
過多兩天﹐我們將會進入冬季時間。時鐘會給較慢一個小時。現在的七點鐘﹐即是未來幾個月的六點鐘。於是﹐愛爾蘭跟香港的時差將加多一個鐘。
也許﹐那時候﹐起床會較為容易。因為太陽應該已露出半個臉來。這幾天早上﹐步行到火車站的時候﹐街燈才慢慢熄滅。我是習慣乘八時零五分那一班火車上班。
有天﹐ADRIAN問我一個問題。假如我們乘的飛機在較鐘後的那一個小時抵達﹐究竟航程說的是什麼時間呢﹖
我當然不知道如何回答。對於較鐘這一件事﹐我依然有點疑惑。只記得EDW早前說過﹐一朝醒來﹐時間便走慢了一句鐘﹐生命便多了一個小時。就是如此罷了。這是他對較鐘的解釋。EDW是我的一個朋友。在我離開香港前十個月﹐他獨自到了英國生活。
今天﹐在公司廚房碰見了FIONNUOLA﹐便跟她閑談了一會兒。好像也有一段時間沒有跟她聊過天。
坐在落地玻璃前﹐眺望著外面的IRISH SEA,我們竟然不其然談到了日落日出。
我投訴說﹐今早實在很黑﹐如同半夜醒來一樣。實在跟半夜十二點沒有分別。要不是鬧鐘還懂得響﹐我會以為自己才剛剛睡到床上。FIONNUOLA點著頭道﹐始終來到這個時候了。況且﹐今天下著大雨嘛﹗天空不陰陰沉沉才怪﹗
我回答說﹐星期天便較鐘。MARIA跟我講過﹐那時後﹐早上的天空會比較光亮。
只見FIONNUOLA有點疑惑﹐似乎我是講錯了些什麼。碰巧﹐德國人WOLFRAM經過。他也一起討論較鐘這個話題。他說﹐較鐘倒是為了方便農夫。好讓他們有多點陽光照耀的時間。
似乎﹐有點道理。不過﹐那也表示天空四點多便會日落啊﹗日照的時間其實是沒有變的罷。是從八點到五點﹐還是從七點到四點的分別。
聽到我的論點﹐FIONNUOLA竟然問道﹐怎麼﹖星期天﹐我們是向後調校一個鐘頭麼﹖我還以為是向前走一個小時。
我實在不知道如何回應。她是一個在愛爾蘭長大的女生。怎麼可能不曉得冬天的時間比夏天慢一個小時啊﹖
也許﹐有些事情見得多了﹐反而會變得有點不認識。因為我們會開始盲目。一切都那麼自然。我們又為何要去牢記﹖
我依然不知道﹐為何冬天的時間比夏天慢一個小時﹖
Friday, October 27, 2006
那年﹐J-LEAGUE正式成立。香港球壇也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南華再不是香港聯賽的霸主。
因為東方不敗出現了。
其實﹐早於一季前﹐東方已經是南華拿取聯賽冠軍的最大障礙。那一年﹐我們多翻追趕﹐直到最後階段﹐還落後他們兩分。那時候﹐大家還只剩餘兩場比賽。不過﹐幸好有一場是我們互相對壘。那表示﹐贏取冠軍的鑰匙還在我們自己的手裡。只要能夠在那場關鍵比賽全取三分﹐我們便可以一分反壓東方﹐進入最後一輪。
奇怪地﹐足總並沒有安排那場比賽在星期天舉行。
我記得﹐那是四月的一個星期四晚上。那表示﹐我是不能夠到球場支持自己心愛的球隊。上學的日子,是不可能到球場看球賽。因為從球場回到家﹐將要是十一點。對於一個初中生來說﹐那是太晚了。
那時候﹐政府大球場還在重建。這樣重要的比賽便只能安排在細小的旺角球場。不過﹐也因為這樣﹐門票售罄了﹐電臺於是可以直播整場比賽。那是香港電臺第一臺。商業電臺老早不做足球廣播。我也因此放棄了手頭上的功課﹐專心一致去為南華打氣。要知道﹐功課做不完﹐還可以早點回學校抄別人。要是南華因為缺少我的支持﹐而失掉了聯賽冠軍﹐那便是如何也改變不了的事實﹐我將會後悔一輩子。東方只要贏得那場比賽﹐便會成為冠軍。是他們創會以來的首次。
結果﹐我們能夠贏得那場比賽﹐繼而奪得當年的聯賽冠軍﹐並未有讓東方偷走了我們的光榮。我記得﹐聽畢電臺轉播後﹐我興奮得擁抱著父親。母親說﹐從未見過我這樣興奮。這個當然。因為自我成為擁南躉後﹐南華從未試過在這樣大的壓力下贏得冠軍。
不過﹐好景不常。接下來的一季﹐我們每逢對著東方﹐都要慘敗而回。聯賽首戰﹐我們便輸了0-5。到銀牌決賽﹐我們也以0-4敗下陣來。似乎﹐那一隊東方真的所向披靡。報紙雜誌都在談論他們取代南華﹐成為香港足球霸主﹐囊括所有冠軍。他們說﹐東方的球員正踏入黃金時期﹐將要稱霸一段時候。不過﹐也有分析說﹐這是政府大球場重建的關係。所有球賽都到了旺角球場舉行。東方的戰術就很適合在那樣細小的場地。況且﹐一向以來﹐南華在旺角球場的表現﹐都比大球場差。所以有大球場是南華福地的說法。
那年﹐總督杯決賽﹐又是南華對東方。因為完成了首期重建﹐以方便七人欖球賽舉行﹐足總也決定把那場決賽移師到政府大球場去﹐希望能夠帶來多些收入。因為便是坐滿了﹐旺角球場也只能容納八千人。首期重建後﹐大球場可以坐兩萬多人。
經過一輪換血﹐南華的表現開始穩定下來。自銀牌決賽後﹐已沒有再嚐敗勣。我們極渴望能夠在福地報仇成功。況且﹐在聯賽冠軍無望後﹐我們很希望拿回一個獎項。既挫一挫東方的威風﹐也可以使他們不能成為另一支囊括所有冠軍的球隊。只是﹐看過全季東方的表現﹐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件很艱難的任務。因為東方整季賽事甚至未失掉過一球。心理上﹐無疑我們是輸掉了。之前兩次對壘﹐我們竟然失掉了九球﹐而未能打進一球。
走向球場的時候﹐望著那些穿起綠色球衣的東方球迷﹐我的確很擔心會很失望而回。因為很奇怪﹐加路連山道上好像都擠滿了東方的球迷。都是綠色的人海。不過﹐我告訴自己﹐有著我在球場全力打氣﹐南華是無敵的。
那天﹐羅偉志和基保成為了我們的英雄。我們贏3-0。
忽然間﹐整個香港都是興奮的擁南躉。他們包圍了加山。每當球員從球場更衣室走回南華會的時候﹐都有震徹雲霄的歡呼聲在他身邊響起來。我們終於能一掃整個球季的冤悶。直到今天﹐我依然記得那天的興奮場面。那是一生一世的。
我以為﹐這兩場比賽﹐就是做擁南躉最開心的時候。
因為東方不敗出現了。
其實﹐早於一季前﹐東方已經是南華拿取聯賽冠軍的最大障礙。那一年﹐我們多翻追趕﹐直到最後階段﹐還落後他們兩分。那時候﹐大家還只剩餘兩場比賽。不過﹐幸好有一場是我們互相對壘。那表示﹐贏取冠軍的鑰匙還在我們自己的手裡。只要能夠在那場關鍵比賽全取三分﹐我們便可以一分反壓東方﹐進入最後一輪。
奇怪地﹐足總並沒有安排那場比賽在星期天舉行。
我記得﹐那是四月的一個星期四晚上。那表示﹐我是不能夠到球場支持自己心愛的球隊。上學的日子,是不可能到球場看球賽。因為從球場回到家﹐將要是十一點。對於一個初中生來說﹐那是太晚了。
那時候﹐政府大球場還在重建。這樣重要的比賽便只能安排在細小的旺角球場。不過﹐也因為這樣﹐門票售罄了﹐電臺於是可以直播整場比賽。那是香港電臺第一臺。商業電臺老早不做足球廣播。我也因此放棄了手頭上的功課﹐專心一致去為南華打氣。要知道﹐功課做不完﹐還可以早點回學校抄別人。要是南華因為缺少我的支持﹐而失掉了聯賽冠軍﹐那便是如何也改變不了的事實﹐我將會後悔一輩子。東方只要贏得那場比賽﹐便會成為冠軍。是他們創會以來的首次。
結果﹐我們能夠贏得那場比賽﹐繼而奪得當年的聯賽冠軍﹐並未有讓東方偷走了我們的光榮。我記得﹐聽畢電臺轉播後﹐我興奮得擁抱著父親。母親說﹐從未見過我這樣興奮。這個當然。因為自我成為擁南躉後﹐南華從未試過在這樣大的壓力下贏得冠軍。
不過﹐好景不常。接下來的一季﹐我們每逢對著東方﹐都要慘敗而回。聯賽首戰﹐我們便輸了0-5。到銀牌決賽﹐我們也以0-4敗下陣來。似乎﹐那一隊東方真的所向披靡。報紙雜誌都在談論他們取代南華﹐成為香港足球霸主﹐囊括所有冠軍。他們說﹐東方的球員正踏入黃金時期﹐將要稱霸一段時候。不過﹐也有分析說﹐這是政府大球場重建的關係。所有球賽都到了旺角球場舉行。東方的戰術就很適合在那樣細小的場地。況且﹐一向以來﹐南華在旺角球場的表現﹐都比大球場差。所以有大球場是南華福地的說法。
那年﹐總督杯決賽﹐又是南華對東方。因為完成了首期重建﹐以方便七人欖球賽舉行﹐足總也決定把那場決賽移師到政府大球場去﹐希望能夠帶來多些收入。因為便是坐滿了﹐旺角球場也只能容納八千人。首期重建後﹐大球場可以坐兩萬多人。
經過一輪換血﹐南華的表現開始穩定下來。自銀牌決賽後﹐已沒有再嚐敗勣。我們極渴望能夠在福地報仇成功。況且﹐在聯賽冠軍無望後﹐我們很希望拿回一個獎項。既挫一挫東方的威風﹐也可以使他們不能成為另一支囊括所有冠軍的球隊。只是﹐看過全季東方的表現﹐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件很艱難的任務。因為東方整季賽事甚至未失掉過一球。心理上﹐無疑我們是輸掉了。之前兩次對壘﹐我們竟然失掉了九球﹐而未能打進一球。
走向球場的時候﹐望著那些穿起綠色球衣的東方球迷﹐我的確很擔心會很失望而回。因為很奇怪﹐加路連山道上好像都擠滿了東方的球迷。都是綠色的人海。不過﹐我告訴自己﹐有著我在球場全力打氣﹐南華是無敵的。
那天﹐羅偉志和基保成為了我們的英雄。我們贏3-0。
忽然間﹐整個香港都是興奮的擁南躉。他們包圍了加山。每當球員從球場更衣室走回南華會的時候﹐都有震徹雲霄的歡呼聲在他身邊響起來。我們終於能一掃整個球季的冤悶。直到今天﹐我依然記得那天的興奮場面。那是一生一世的。
我以為﹐這兩場比賽﹐就是做擁南躉最開心的時候。
Thursday, October 26, 2006
早前﹐因為WEST HAM UNITED意外地羅致了兩名天才球星﹐讓我想起了一件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學生。
那天是星期六。剛好是我的長週。因為是半日制的學校﹐每隔一個星期﹐我們便要在星期六回校上課。也要參加一些課外活動。
由始至終﹐我也覺得小學時候的那些課外活動實在是為了把你留在學校罷了。因為那些活動都很無謂。老實說﹐除了參加了一年棋會外﹐我實在不記得做過些什麼。只記得那些小組的名稱。什麼文娛小組。什麼興趣小組。單看名字﹐也知道是一個又一個的垃圾。因為都是沒有意義的名字。始終﹐名不正﹐則言不順。
最使人失望的是﹐到我夠年齡參加足球組的時候﹐負責足球隊的那位老師又到了另外一間學校任教﹐學校也因此取消了這項最有意義的課外活動。
那天無聊地多留在學校個多小時後﹐父親便如常接我去打羽毛球。自小學二年級開始﹐每個星期六﹐我都會到窩打老道山的YWCA,參加他們的訓練班。五年級的時候﹐更因為父親友人的介紹﹐我還會在星期天晚上﹐跟前福建省省隊教練學習打羽毛球。直至中學二年級。
那天在父親的車上﹐我跟往常一樣﹐在後座翻閱報紙。當然首先讀的都是體育版。我竟然看到了這樣的一個標題﹕南華兵變。
原來﹐當林建岳未能續任南華足球部主席後﹐他便決定帶領那些跟他自己簽了私人合約的七個球員﹐轉投另外一間球會花花。並以自己家族公司的名義贊助這間從前從不起眼的球隊﹐改名叫麗新花花。
我讀完又再讀那篇報導。因為我不相信那是真的。那七名球員都是當年南華的正選。他們是﹐黃文財﹑張志德﹑賴羅球﹑余國森﹑黃國安﹑黎永昌和巴貝利。自精工退出後﹐南華便一支獨秀﹐經常囊括所有冠軍。因為我們盡收天下兵器以弱諸侯。我以為﹐那時候是做擁南躉最開心的時候。
我很失望地跟父親說﹐來季我們怎麼辦﹖
父親一邊駕車﹐一邊回答說﹐什麼怎麼辦﹖便是繼續贏取所有冠軍啊﹗
可是﹐巴貝利他們都要走了。
那又如何﹖我們一樣可以贏得冠軍的啊﹗要知道﹐以前的冠軍都是南華贏得的。從來都沒有張志德的冠軍﹑巴貝利的冠軍。以後也都是一樣。
我聽得很不明白。那天﹐我的羽毛球打得很差。
兵變後﹐南華跟麗新花花的第一次碰頭﹐是十月的一個星期天。因為晚上要參加羽毛球訓練﹐父親並不批准我到政府大球場看球賽。當然﹐他自己也沒有獨自前往。我們便留在家裡面﹐收聽電臺的直播。不過﹐不記得是香港電臺第一臺﹐還是商業一臺。
當聽到顧錦輝頂入一球時﹐我興奮得在家裡面亂叫亂跳。那時候﹐是下半場末段。我知道﹐我們勝利在望。
當廣播員(或何靜江﹑或林尚義)宣佈南華贏1-0時﹐我實在有點不相信。我真的未有想過這一隊南華﹐能夠戰勝那對所向無敵的南華。那天晚上﹐我竟然也贏了兩場訓練後的比賽。每次訓練後﹐前福建省省隊教練都要我們三個學員互相比賽一下﹐務求學以致用。三個學員裡面﹐我是技術最差的那一個。
那一年﹐南華依然繼續贏得冠軍。以後幾年﹐我們也繼續贏得冠軍。面對著麗新花花﹐或者以後的麗新﹐我們都是贏多輸少。印象中﹐更好像只輸過一次。
我發覺﹐那才是做擁南躉最開心的時候。
直至「東方不敗」的出現。
那天是星期六。剛好是我的長週。因為是半日制的學校﹐每隔一個星期﹐我們便要在星期六回校上課。也要參加一些課外活動。
由始至終﹐我也覺得小學時候的那些課外活動實在是為了把你留在學校罷了。因為那些活動都很無謂。老實說﹐除了參加了一年棋會外﹐我實在不記得做過些什麼。只記得那些小組的名稱。什麼文娛小組。什麼興趣小組。單看名字﹐也知道是一個又一個的垃圾。因為都是沒有意義的名字。始終﹐名不正﹐則言不順。
最使人失望的是﹐到我夠年齡參加足球組的時候﹐負責足球隊的那位老師又到了另外一間學校任教﹐學校也因此取消了這項最有意義的課外活動。
那天無聊地多留在學校個多小時後﹐父親便如常接我去打羽毛球。自小學二年級開始﹐每個星期六﹐我都會到窩打老道山的YWCA,參加他們的訓練班。五年級的時候﹐更因為父親友人的介紹﹐我還會在星期天晚上﹐跟前福建省省隊教練學習打羽毛球。直至中學二年級。
那天在父親的車上﹐我跟往常一樣﹐在後座翻閱報紙。當然首先讀的都是體育版。我竟然看到了這樣的一個標題﹕南華兵變。
原來﹐當林建岳未能續任南華足球部主席後﹐他便決定帶領那些跟他自己簽了私人合約的七個球員﹐轉投另外一間球會花花。並以自己家族公司的名義贊助這間從前從不起眼的球隊﹐改名叫麗新花花。
我讀完又再讀那篇報導。因為我不相信那是真的。那七名球員都是當年南華的正選。他們是﹐黃文財﹑張志德﹑賴羅球﹑余國森﹑黃國安﹑黎永昌和巴貝利。自精工退出後﹐南華便一支獨秀﹐經常囊括所有冠軍。因為我們盡收天下兵器以弱諸侯。我以為﹐那時候是做擁南躉最開心的時候。
我很失望地跟父親說﹐來季我們怎麼辦﹖
父親一邊駕車﹐一邊回答說﹐什麼怎麼辦﹖便是繼續贏取所有冠軍啊﹗
可是﹐巴貝利他們都要走了。
那又如何﹖我們一樣可以贏得冠軍的啊﹗要知道﹐以前的冠軍都是南華贏得的。從來都沒有張志德的冠軍﹑巴貝利的冠軍。以後也都是一樣。
我聽得很不明白。那天﹐我的羽毛球打得很差。
兵變後﹐南華跟麗新花花的第一次碰頭﹐是十月的一個星期天。因為晚上要參加羽毛球訓練﹐父親並不批准我到政府大球場看球賽。當然﹐他自己也沒有獨自前往。我們便留在家裡面﹐收聽電臺的直播。不過﹐不記得是香港電臺第一臺﹐還是商業一臺。
當聽到顧錦輝頂入一球時﹐我興奮得在家裡面亂叫亂跳。那時候﹐是下半場末段。我知道﹐我們勝利在望。
當廣播員(或何靜江﹑或林尚義)宣佈南華贏1-0時﹐我實在有點不相信。我真的未有想過這一隊南華﹐能夠戰勝那對所向無敵的南華。那天晚上﹐我竟然也贏了兩場訓練後的比賽。每次訓練後﹐前福建省省隊教練都要我們三個學員互相比賽一下﹐務求學以致用。三個學員裡面﹐我是技術最差的那一個。
那一年﹐南華依然繼續贏得冠軍。以後幾年﹐我們也繼續贏得冠軍。面對著麗新花花﹐或者以後的麗新﹐我們都是贏多輸少。印象中﹐更好像只輸過一次。
我發覺﹐那才是做擁南躉最開心的時候。
直至「東方不敗」的出現。
Wednesday, October 25, 2006
MAN BOOKER PRIZE是英語創作世界裡一個很重要的獎項。拿下了這個獎﹐便代表你寫了一本那年度最好的英語小說。
今年的MAN BOOKER PRIZE也終於有了結果。是KIRAN DESAI的THE INHERITANCE OF LOSS獲得。她是一個印度人﹐來自一個小說世家。她的母親便是ANITA DESAI。曾獲MAN BOOKER PRIZE提名三次。
評審團主席HERMIONE LEE說﹐這是一部很出色的作品﹐具人性和智慧﹐也有很強的政治批判。LEE是牛津大學英國文學系教授。
那是一個退休法官的故事。背景是喜馬拉雅山。有一天﹐孫女忽然在他面前出現。因為她的父母已不在人世。面對著這個孫女﹐前法官的生命便因此發生了變化。KIRAN是用了八年時間來完成這部小說。她說﹐小說裡講的﹐其實都是她自己的故事。書中不斷重複一個主題﹕UPROOTING AND TRANSPLANTATION。
我讀的書實在太少。今年的六個提名﹐我沒有讀過其中一本。所以﹐實在不知道究竟這是否我的心愛。說不定﹐我會覺得其餘五本比較合我心水。
今年一樣獲得提名的是﹐HISMA MATAR的IN THE COUNTRY OF MEN、KATE GRENVILLE的THE SECRET RIVER、MJ HYLAND的CARRY ME DOWN、EDWARD ST AUBYN的MOTHER'S MILK和SARAH WATERS的THE NIGHT WATCH。
我最有興趣的是THE NIGHT WATCH。之前﹐我翻閱過SARAH WATERS的成名作THE FINGERSMITH。很吸引人﹐讓我想起了狄更斯。
看著KIRAN DESAI的照片﹐我又想起了那個老問題﹕為何同樣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香港便是沒有辦法孕育出一個獲西方認同的英語作家﹖我已經不是講獲BOOKER PRIZE提名了。獲西方認同可以是上得倫敦書評等刊物接受批評﹔獲西方認同可以是紐約時報TOP 50 BEST-SELLERS;獲西方認同也可以是在那些大型連鎖書店找到的作品。可是﹐香港就是沒有出產過這樣的一個人。在殖民地的時候沒有﹐剛回歸的時候沒有。我相信﹐在我們變得越來越像中國大陸的一個華南城市下﹐以後的日子﹐我們也沒有可能有一個。
其實﹐便是說英語作家﹐香港也沒有一個。我們卻竟然稱自己做國際大都會。就像是一隻青蛙﹐望著頭頂的井口﹐便以為那是世界的全部一樣。
從來﹐作家都是一座城市的靈魂。因為那是一座城市的文化代表,是一座城市的代言人。一座沒有靈魂的城市﹐便是政府如何努力在外國搞宣傳﹐便是政府如何努力在外國派發飛龍標誌﹑高喊標語和口號﹐一切其實都是枉然。
倫敦最大書店WATERSTONE'S的小說買手RODNEY TROUBRIDGE說﹐THIS CONTINUES THE FINE TRADITION OF BOOKER WINNERS SET IN INDIA。
本來﹐在中國和西方的文化衝擊下﹐香港實在很有條件去製造一個又一個獲西方認同的英語作家。因為這些故事都很受到西方的注視。
奈何﹐我們是白白讓機會溜走了。
今年的MAN BOOKER PRIZE也終於有了結果。是KIRAN DESAI的THE INHERITANCE OF LOSS獲得。她是一個印度人﹐來自一個小說世家。她的母親便是ANITA DESAI。曾獲MAN BOOKER PRIZE提名三次。
評審團主席HERMIONE LEE說﹐這是一部很出色的作品﹐具人性和智慧﹐也有很強的政治批判。LEE是牛津大學英國文學系教授。
那是一個退休法官的故事。背景是喜馬拉雅山。有一天﹐孫女忽然在他面前出現。因為她的父母已不在人世。面對著這個孫女﹐前法官的生命便因此發生了變化。KIRAN是用了八年時間來完成這部小說。她說﹐小說裡講的﹐其實都是她自己的故事。書中不斷重複一個主題﹕UPROOTING AND TRANSPLANTATION。
我讀的書實在太少。今年的六個提名﹐我沒有讀過其中一本。所以﹐實在不知道究竟這是否我的心愛。說不定﹐我會覺得其餘五本比較合我心水。
今年一樣獲得提名的是﹐HISMA MATAR的IN THE COUNTRY OF MEN、KATE GRENVILLE的THE SECRET RIVER、MJ HYLAND的CARRY ME DOWN、EDWARD ST AUBYN的MOTHER'S MILK和SARAH WATERS的THE NIGHT WATCH。
我最有興趣的是THE NIGHT WATCH。之前﹐我翻閱過SARAH WATERS的成名作THE FINGERSMITH。很吸引人﹐讓我想起了狄更斯。
看著KIRAN DESAI的照片﹐我又想起了那個老問題﹕為何同樣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香港便是沒有辦法孕育出一個獲西方認同的英語作家﹖我已經不是講獲BOOKER PRIZE提名了。獲西方認同可以是上得倫敦書評等刊物接受批評﹔獲西方認同可以是紐約時報TOP 50 BEST-SELLERS;獲西方認同也可以是在那些大型連鎖書店找到的作品。可是﹐香港就是沒有出產過這樣的一個人。在殖民地的時候沒有﹐剛回歸的時候沒有。我相信﹐在我們變得越來越像中國大陸的一個華南城市下﹐以後的日子﹐我們也沒有可能有一個。
其實﹐便是說英語作家﹐香港也沒有一個。我們卻竟然稱自己做國際大都會。就像是一隻青蛙﹐望著頭頂的井口﹐便以為那是世界的全部一樣。
從來﹐作家都是一座城市的靈魂。因為那是一座城市的文化代表,是一座城市的代言人。一座沒有靈魂的城市﹐便是政府如何努力在外國搞宣傳﹐便是政府如何努力在外國派發飛龍標誌﹑高喊標語和口號﹐一切其實都是枉然。
倫敦最大書店WATERSTONE'S的小說買手RODNEY TROUBRIDGE說﹐THIS CONTINUES THE FINE TRADITION OF BOOKER WINNERS SET IN INDIA。
本來﹐在中國和西方的文化衝擊下﹐香港實在很有條件去製造一個又一個獲西方認同的英語作家。因為這些故事都很受到西方的注視。
奈何﹐我們是白白讓機會溜走了。
Tuesday, October 24, 2006
百年歷史裡面﹐便是有著一箱又一箱的黃金放在面前﹐他們也無動于衷。
今年﹐他們終於放棄傳統﹐讓自己的胸口繡上了六個英文字母﹕U-N-I-C-E-F。主席說﹐一間成功的球會﹐不能只在球場上贏得錦標。他們也要為社會多做點事情。於是﹐FC BARCELONA成為了第一間給錢予別人﹐在自己球衣上面賣廣告的歐洲冠軍。
早在去年夏天﹐已經有消息傳出﹐FC BARCELONA準備開放球衣胸前的位置。那時候﹐北京奧委會是爭得這個歷史時刻的大熱門。據說﹐他們開出了一個天價﹐以求利用這間加泰隆尼亞球會的知名度﹐來宣傳北京奧運。面對著這個便是很多大球會都難以抗拒的OFFER,加泰隆尼亞人做了一個很多跨國企業也不敢做的事情。其實﹐向北京說不有幾多難度﹖莫忘記﹐他們曾經對抗過法蘭高將軍。
在展現新球衣的記者招待會裡﹐主席承認﹐我們的確要很小心﹐去選擇第一間在我們球衣上面買廣告的機構。一點隨便不得。FC BARCELONA的名聲不能在我的手上給毀了。
說者可能無心﹐只是聽者卻很著意。不其然地﹐我想起了龍應臺的《誰不是天安門母親﹖》。那是一篇紀念天安門屠殺十五週年的文章。
「沒有人會尊敬市場的。這個世界再怎麼現實﹑再怎麼野蠻﹐最終贏得國際尊敬的﹐不是市場或武力﹐而仍是一個國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中國要得到泱泱大國贏得的尊敬﹐不在於市場之大﹐國土之廣﹐人口之多﹐而在於她道德擔當的有無。『六四』使中國道德破產。」
在Unicef跟北京奧運之間兩者選一﹐這個選擇太容易了罷。
上個星期三的夜晚﹐FC BARCELONA是在STAMFORD BRIDGE敗下陣來。不過﹐望著他們的球衣﹐CHELSEA竟然覺得有點不自在。他們的市場部人員還在打著自己的胸口﹐追問自己﹕「為何未有想到這一步﹖」最近﹐便有消息說,ROMAN ABRAMOVICH下令打探一下﹐能否在他們的藍色球衣上也繡上SAVE THE CHIDREN或OXFAM的字樣。
現今社會﹐企業再也不能只顧著盈利。因為不顧一切地牟取暴利﹐企業最終會受大眾捨棄。因此﹐企業形像也是他們需要顧及的地方。現在﹐很多慈善活動都得到跨國集團的贊助。一來可以賣廣告﹐也可以讓自己的招牌光亮一點。是百利而無一害。
只是﹐假如CHELSEA球員胸前也印著SAVE THE CHIDREN或OXFAM這些字樣﹐他們只會讓我想起﹐MADONNA在馬拉維收養DAVID BANDA的事情。兩者實在沒有分別。
話得說回來。如果一天﹐Unicef想找義工帶小朋友到NOU CAMP,請記起我。我是很樂意做的。況且﹐我也有幫Unicef做義工的經驗啊﹗我曾經做過校對。
假如你還抵得住你那個惡魔上司。
今年﹐他們終於放棄傳統﹐讓自己的胸口繡上了六個英文字母﹕U-N-I-C-E-F。主席說﹐一間成功的球會﹐不能只在球場上贏得錦標。他們也要為社會多做點事情。於是﹐FC BARCELONA成為了第一間給錢予別人﹐在自己球衣上面賣廣告的歐洲冠軍。
早在去年夏天﹐已經有消息傳出﹐FC BARCELONA準備開放球衣胸前的位置。那時候﹐北京奧委會是爭得這個歷史時刻的大熱門。據說﹐他們開出了一個天價﹐以求利用這間加泰隆尼亞球會的知名度﹐來宣傳北京奧運。面對著這個便是很多大球會都難以抗拒的OFFER,加泰隆尼亞人做了一個很多跨國企業也不敢做的事情。其實﹐向北京說不有幾多難度﹖莫忘記﹐他們曾經對抗過法蘭高將軍。
在展現新球衣的記者招待會裡﹐主席承認﹐我們的確要很小心﹐去選擇第一間在我們球衣上面買廣告的機構。一點隨便不得。FC BARCELONA的名聲不能在我的手上給毀了。
說者可能無心﹐只是聽者卻很著意。不其然地﹐我想起了龍應臺的《誰不是天安門母親﹖》。那是一篇紀念天安門屠殺十五週年的文章。
「沒有人會尊敬市場的。這個世界再怎麼現實﹑再怎麼野蠻﹐最終贏得國際尊敬的﹐不是市場或武力﹐而仍是一個國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中國要得到泱泱大國贏得的尊敬﹐不在於市場之大﹐國土之廣﹐人口之多﹐而在於她道德擔當的有無。『六四』使中國道德破產。」
在Unicef跟北京奧運之間兩者選一﹐這個選擇太容易了罷。
上個星期三的夜晚﹐FC BARCELONA是在STAMFORD BRIDGE敗下陣來。不過﹐望著他們的球衣﹐CHELSEA竟然覺得有點不自在。他們的市場部人員還在打著自己的胸口﹐追問自己﹕「為何未有想到這一步﹖」最近﹐便有消息說,ROMAN ABRAMOVICH下令打探一下﹐能否在他們的藍色球衣上也繡上SAVE THE CHIDREN或OXFAM的字樣。
現今社會﹐企業再也不能只顧著盈利。因為不顧一切地牟取暴利﹐企業最終會受大眾捨棄。因此﹐企業形像也是他們需要顧及的地方。現在﹐很多慈善活動都得到跨國集團的贊助。一來可以賣廣告﹐也可以讓自己的招牌光亮一點。是百利而無一害。
只是﹐假如CHELSEA球員胸前也印著SAVE THE CHIDREN或OXFAM這些字樣﹐他們只會讓我想起﹐MADONNA在馬拉維收養DAVID BANDA的事情。兩者實在沒有分別。
話得說回來。如果一天﹐Unicef想找義工帶小朋友到NOU CAMP,請記起我。我是很樂意做的。況且﹐我也有幫Unicef做義工的經驗啊﹗我曾經做過校對。
假如你還抵得住你那個惡魔上司。
Monday, October 23, 2006
上次銀行假期﹐我到了倫敦看MUSICAL。是ANDREW LLYOD WEBBER的EVITA。
我們在LEICESTER SQUARE的那些DISCOUNT COUNTER買票。
本來我是想看PHANTOM OF THE OPERA。或者THE MISÉRABLES。只是要買這兩套音樂劇即晚的門票﹐實在需要不少的金錢。況且﹐那天是星期六。便是在那些DISCOUNT COUNTERS,也要花你五十英鎊方能找到一張。最後﹐按著自己的銀包﹐我們選擇了剛剛重新上演的EVITA。六十英鎊兩張。那是最便宜的了。縱然門外的告示板上面寫著:EVITA,FROM 20。
我想﹐可能那是平時週一至週四的價錢。因為我們的座位是整個劇院最後的那一排。我們背後便是牆壁。
很不意外地﹐又是一晚FULL HOUSE。我不知道究竟這晚是EVITA這套音樂劇在WEST END的第幾次公開演出。我想﹐應該不下過百。不過﹐依然能夠吸引眾人。它吸引的不只是普通的市民﹑情侶和遊客。有人選擇了看EVITA來慶祝生日。有人甚至選擇看EVITA做她「母雞夜」的其中一個節目。在英國和愛爾蘭﹐在一些特別的晚上﹐女生跟她的朋友都很喜歡穿上特別的T恤﹑特別的衣服(我看過有人扮兔女郎)﹐告訴別人那是她的生日夜﹑是HEN'S NIGHT。
看過EVITA後﹐我再次證實音樂劇是百看不厭。這是我第二次看MUSICAL。上次也是ANDREW LLYOD WEBBER的作品。裡面有一首歌陪伴了我度過幾個無眠的夜。是CLOSE EVERY DOOR。
我們在開場前十分鐘已經找到我們的座位。是最後那排中間的位置。其實﹐在那個時候﹐差不多所有座位都已經坐了人。除了我們隔鄰的那個單獨座位。
不過﹐那位觀眾也剛好在開場前趕到。是一個身材肥胖的亞洲女人。由於整排座位都已坐了人﹐她很辛苦地才能來到她的應坐位置。途中﹐她要不斷的跟人講對不起。因為所有人都要站起來﹐讓這一隻恐龍通過。我慶幸帶位員未有指示她從我們這一邊走到她的座位。
聽到她講SORRY的聲音﹐我猜到她是香港人。至少﹐我猜到她是講廣東話。於是﹐我也不便對她諸多批評。我無謂把自己放到一個困難的境地。
在中場休息的時候﹐不幸地﹐我發覺我的估計完全正確。她講的是香港廣東話。因為她竟然轉個頭來問我們票子的價錢。她怕被人騙。她買的應該是SECOND LOWEST PRICE的門票。可是她覺得她的座位是最差的那一種。她想不到最便宜的座位在那兒。
望著這隻恐龍的尊容﹐我真的想告訴她﹐我們的票只需要二十英鎊。SHAME ON YOU.
她實在不應該探究自己是否被人騙了。除非她覺得整個演出不值三十英鎊。其實﹐便是懷疑自己被人騙了﹐也應該大方面對。無論如何也不能讓這件事RUIN了自己欣賞臺上精彩的演出。所以﹐更不應該查探那個真相。更何況﹐除了在外地﹐根本不可能有什麼人會有意思騙她。她實在也沒有什麼可以讓人騙走。要知道﹐跑去騙她﹐實在需要很大的勇氣。
希望這種恐龍都已經離開香港。因為她們實在不屬於香港。OTHERWISE,I WILL CRY FOR YOU HONG KONG.
我們在LEICESTER SQUARE的那些DISCOUNT COUNTER買票。
本來我是想看PHANTOM OF THE OPERA。或者THE MISÉRABLES。只是要買這兩套音樂劇即晚的門票﹐實在需要不少的金錢。況且﹐那天是星期六。便是在那些DISCOUNT COUNTERS,也要花你五十英鎊方能找到一張。最後﹐按著自己的銀包﹐我們選擇了剛剛重新上演的EVITA。六十英鎊兩張。那是最便宜的了。縱然門外的告示板上面寫著:EVITA,FROM 20。
我想﹐可能那是平時週一至週四的價錢。因為我們的座位是整個劇院最後的那一排。我們背後便是牆壁。
很不意外地﹐又是一晚FULL HOUSE。我不知道究竟這晚是EVITA這套音樂劇在WEST END的第幾次公開演出。我想﹐應該不下過百。不過﹐依然能夠吸引眾人。它吸引的不只是普通的市民﹑情侶和遊客。有人選擇了看EVITA來慶祝生日。有人甚至選擇看EVITA做她「母雞夜」的其中一個節目。在英國和愛爾蘭﹐在一些特別的晚上﹐女生跟她的朋友都很喜歡穿上特別的T恤﹑特別的衣服(我看過有人扮兔女郎)﹐告訴別人那是她的生日夜﹑是HEN'S NIGHT。
看過EVITA後﹐我再次證實音樂劇是百看不厭。這是我第二次看MUSICAL。上次也是ANDREW LLYOD WEBBER的作品。裡面有一首歌陪伴了我度過幾個無眠的夜。是CLOSE EVERY DOOR。
我們在開場前十分鐘已經找到我們的座位。是最後那排中間的位置。其實﹐在那個時候﹐差不多所有座位都已經坐了人。除了我們隔鄰的那個單獨座位。
不過﹐那位觀眾也剛好在開場前趕到。是一個身材肥胖的亞洲女人。由於整排座位都已坐了人﹐她很辛苦地才能來到她的應坐位置。途中﹐她要不斷的跟人講對不起。因為所有人都要站起來﹐讓這一隻恐龍通過。我慶幸帶位員未有指示她從我們這一邊走到她的座位。
聽到她講SORRY的聲音﹐我猜到她是香港人。至少﹐我猜到她是講廣東話。於是﹐我也不便對她諸多批評。我無謂把自己放到一個困難的境地。
在中場休息的時候﹐不幸地﹐我發覺我的估計完全正確。她講的是香港廣東話。因為她竟然轉個頭來問我們票子的價錢。她怕被人騙。她買的應該是SECOND LOWEST PRICE的門票。可是她覺得她的座位是最差的那一種。她想不到最便宜的座位在那兒。
望著這隻恐龍的尊容﹐我真的想告訴她﹐我們的票只需要二十英鎊。SHAME ON YOU.
她實在不應該探究自己是否被人騙了。除非她覺得整個演出不值三十英鎊。其實﹐便是懷疑自己被人騙了﹐也應該大方面對。無論如何也不能讓這件事RUIN了自己欣賞臺上精彩的演出。所以﹐更不應該查探那個真相。更何況﹐除了在外地﹐根本不可能有什麼人會有意思騙她。她實在也沒有什麼可以讓人騙走。要知道﹐跑去騙她﹐實在需要很大的勇氣。
希望這種恐龍都已經離開香港。因為她們實在不屬於香港。OTHERWISE,I WILL CRY FOR YOU HONG KONG.
Sunday, October 22, 2006
在布達佩斯﹐我終於買了一盒木製象棋。每一顆棋子都是木彫來的。棋盤則超過半米乘半米那麼大。花了我五十五塊歐羅。
其實﹐很久以前﹐已經很想買一盒這樣的象棋。去年﹐到意大利旅行﹐我已經到處找找。只是﹐看來看去﹐都找不到合心水的。在歐洲東部的大陸﹐因為近俄羅斯﹐選擇的確比意大利多。可是﹐遇上的不是太小﹐便是彫刻不夠細緻。當碰上了一盒很喜愛的﹐又發覺價錢很高﹐自己實在負擔不來。在布拉格的舊城區﹐我便找到了一盒很得我心。可是﹐他們竟然要我四百塊歐羅。縱然很喜歡﹐可是也不得不放棄。
有了棋盤後﹐我開始每天閱讀倫敦時報裡面的那個象棋專欄。因為這樣較容易理解。老實說﹐望著那些16.Qxd8+ Rxd8 17.Ba3 Rc8,的確很難在腦海裡想像得到戰場上如何激烈。或者﹐這是我未能成為一個好棋手的原因。
最近﹐讀了兩個很漂亮的棋局。都是前世界棋王詩帕斯奇(BORIS SPASSKY)的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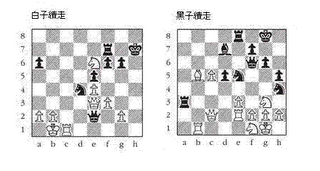
勝利的關鍵﹐都在於送皇后去死。假若白子未有把皇后走到H6,黑皇就不會給引到那個進退維谷的境地﹔假如黑子不送皇后到F3,便不能逼白皇到H1那個死角。唯有犧牲了心愛的皇后﹐方能完成開局以來的目標﹐獲得最後勝利。要知道﹐象棋裡面﹐皇后實在是一隻很厲害的棋子。因為她可以任意橫衝直撞﹐也可以隨意打斜行走。是遇佛殺佛﹐遇神殺神。
只是﹐縱然這樣厲害﹐她還不過是皇帝身邊的一隻棋子。跟前排的小卒其實沒有兩樣。要贏得一盤棋﹐倒還是要吃得掉對手的那個皇帝。只要皇帝一日未死﹐棋局還未有結束的一天。在這樣的理解下﹐皇帝身邊的其他生命﹐其實都是平等的。便是能替皇帝吃掉很多對手的棋子﹐也不表示你比其他高貴﹐可以在贏得棋局這個大前提下﹐免去一死。
誠然﹐正如許冠傑所唱﹐世事往往如棋。在一個又一個棋局裡面﹐我們竟然看到一個又一個生命的倒影。
很多時候﹐為了自己的前途和未來﹐我們不惜把心愛的皇后犧牲掉。我們更很自私地﹐把這個做法美其名為「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讓外人以為在走向勝利的路途上﹐割掉的都是我們自己的肉。我們粗暴地把別人珍貴的生命據為己有﹐然後又殘暴地按著一己的意願輕易把它結束。便是自己的最愛﹐也不能幸免。
世人都是如此。還能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人﹐都是如此。
殺戮多了﹐勝利也不斷的累積。我們開始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以為世界唯我獨大。於是﹐我們也漸漸忽略了﹐這個世界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世界。我們自己的世界﹐不過是整個世界的其中一個。它跟其他的世界互相牽連著。在眼前這個棋局裡面﹐我們可能的確是皇帝。只是﹐同一時間﹐我們也可以是另外一些棋局裡面別人的皇后。自呱呱落地一刻起﹐我們已經開始了無數﹑無數個棋局﹐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我們還能在世界生存﹐並不是自己比別人厲害﹐並不是因為自己能操控別人的生命。我們還能在世界生存﹐只因還不是時候要為別人犧牲。
世界其實祇得一個棋王。他的名字叫耶和華。
我們是人。不是神。
其實﹐很久以前﹐已經很想買一盒這樣的象棋。去年﹐到意大利旅行﹐我已經到處找找。只是﹐看來看去﹐都找不到合心水的。在歐洲東部的大陸﹐因為近俄羅斯﹐選擇的確比意大利多。可是﹐遇上的不是太小﹐便是彫刻不夠細緻。當碰上了一盒很喜愛的﹐又發覺價錢很高﹐自己實在負擔不來。在布拉格的舊城區﹐我便找到了一盒很得我心。可是﹐他們竟然要我四百塊歐羅。縱然很喜歡﹐可是也不得不放棄。
有了棋盤後﹐我開始每天閱讀倫敦時報裡面的那個象棋專欄。因為這樣較容易理解。老實說﹐望著那些16.Qxd8+ Rxd8 17.Ba3 Rc8,的確很難在腦海裡想像得到戰場上如何激烈。或者﹐這是我未能成為一個好棋手的原因。
最近﹐讀了兩個很漂亮的棋局。都是前世界棋王詩帕斯奇(BORIS SPASSKY)的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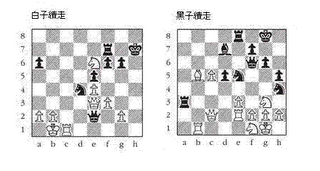
勝利的關鍵﹐都在於送皇后去死。假若白子未有把皇后走到H6,黑皇就不會給引到那個進退維谷的境地﹔假如黑子不送皇后到F3,便不能逼白皇到H1那個死角。唯有犧牲了心愛的皇后﹐方能完成開局以來的目標﹐獲得最後勝利。要知道﹐象棋裡面﹐皇后實在是一隻很厲害的棋子。因為她可以任意橫衝直撞﹐也可以隨意打斜行走。是遇佛殺佛﹐遇神殺神。
只是﹐縱然這樣厲害﹐她還不過是皇帝身邊的一隻棋子。跟前排的小卒其實沒有兩樣。要贏得一盤棋﹐倒還是要吃得掉對手的那個皇帝。只要皇帝一日未死﹐棋局還未有結束的一天。在這樣的理解下﹐皇帝身邊的其他生命﹐其實都是平等的。便是能替皇帝吃掉很多對手的棋子﹐也不表示你比其他高貴﹐可以在贏得棋局這個大前提下﹐免去一死。
誠然﹐正如許冠傑所唱﹐世事往往如棋。在一個又一個棋局裡面﹐我們竟然看到一個又一個生命的倒影。
很多時候﹐為了自己的前途和未來﹐我們不惜把心愛的皇后犧牲掉。我們更很自私地﹐把這個做法美其名為「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讓外人以為在走向勝利的路途上﹐割掉的都是我們自己的肉。我們粗暴地把別人珍貴的生命據為己有﹐然後又殘暴地按著一己的意願輕易把它結束。便是自己的最愛﹐也不能幸免。
世人都是如此。還能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人﹐都是如此。
殺戮多了﹐勝利也不斷的累積。我們開始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以為世界唯我獨大。於是﹐我們也漸漸忽略了﹐這個世界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世界。我們自己的世界﹐不過是整個世界的其中一個。它跟其他的世界互相牽連著。在眼前這個棋局裡面﹐我們可能的確是皇帝。只是﹐同一時間﹐我們也可以是另外一些棋局裡面別人的皇后。自呱呱落地一刻起﹐我們已經開始了無數﹑無數個棋局﹐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我們還能在世界生存﹐並不是自己比別人厲害﹐並不是因為自己能操控別人的生命。我們還能在世界生存﹐只因還不是時候要為別人犧牲。
世界其實祇得一個棋王。他的名字叫耶和華。
我們是人。不是神。
Saturday, October 21, 2006
在布拉格逗留了三天後﹐那個晚上﹐我們趕上了開往布達佩斯的夜車。
因為聽得太多火車上失竊的故事﹐我們決定整夜無眠﹐來守護身邊的一切。他們說﹐竊匪總是在遊客睡覺的時候﹐悄悄走入房間裡面。那個門鎖﹐完全不濟事。我想﹐有些事情﹐總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罷。只是不知道﹐到了這個年紀﹐還能否刻意地無心睡眠﹖究竟還能支持到什麼時候﹖
真的不知道。
外面下著很大的雨。因為怕弄濕房間﹐我們不得不關掉那扇唯一的窗。幸好﹐房間裡便祇得我們三個。那僅餘的空氣﹐還能讓我們吸上幾個小時罷﹖房間其實很小。只是一個四尺寬﹑六尺深的斗室。看著那些床位設計﹐我依然不能想像﹐這一間房可以同時容納六個人。
憑倚著窗﹐我看到我們的影子﹐正在全速逃離朦朧的波希米亞夜色。
我想起了十年前的那個夏天。
那年﹐才大學一年級。我們一行十多人﹐從廣州乘火車到北京旅行﹐又由北京乘夜車到呼和浩特。那時候﹐京九鐵路剛通車。因為新鮮﹐所以很受歡迎。我們買不到票子﹐可又很嚮往乘火車旅行﹐於是便決定到廣州﹐乘搭京廣鐵路。
我記得﹐車程差不多要足足一天。那是二十四個小時啊﹗我們是凌晨上車。要在車廂裡過兩個晚上。不過﹐不時在這間房間走走﹐那間房間去去﹐讀讀書﹐談談天﹐說說地﹐唱唱歌﹐時間倒也過得很快。至少﹐到了現在﹐我已記不起那些困在車廂裡面的每一分每一秒。因為那些時間﹐是幾個小時﹑幾個小時的流水般﹐跟隨外面不斷往後退的風景﹐遠離我們而去。
那是我們的青蔥歲月。沒有煩惱﹐沒有懮愁。因為世界沒有什麼事情值得我們為她煩惱。因為世界沒有什麼事情值得我們為她懮愁。世界還待我們去開發。世界還待我們去闖蕩。機會多的是。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努力﹐我們會得到應有的回報。那時候﹐香港依然是個公平的社會。你不會因為你信仰的宗教﹐使你的血汗白流。你也不會因為你的政見﹐使你的努力白費。至少﹐身邊的一切一切﹐社會上的萬事萬物﹐都讓我們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
雨終於停了。其實﹐是我們到了沒有下雨的地方。朋友說﹐那應該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邊界。我望望錶﹐才是凌晨三時。
火車稍停留了一會兒﹐便又繼續他的旅程。我不知道這兒還叫不叫做波希米亞。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前五年﹐捷克和斯洛伐克成為了兩個不同的國家。對於這些歷史﹐我是很無知。因為我的民族是一個不尊重歷史的民族。他們對於自己的歷史也不甚了了﹐遑論談什麼波希米亞。那是一個傳說中的國度罷。
是沒有雨了﹐只是我發覺﹐外面的景色卻越來越朦朧。我努力睜開眼睛﹐好讓自己認清那是晨曦的霧水。不過﹐我相信﹐那是我自己的夢境。
早上八時﹐我們抵達布達佩斯。整夜一切安全。八個小時的車程裡面﹐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也沒有人無緣無故闖了進來。
只是﹐我發覺﹐人是大了。老了。
因為聽得太多火車上失竊的故事﹐我們決定整夜無眠﹐來守護身邊的一切。他們說﹐竊匪總是在遊客睡覺的時候﹐悄悄走入房間裡面。那個門鎖﹐完全不濟事。我想﹐有些事情﹐總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罷。只是不知道﹐到了這個年紀﹐還能否刻意地無心睡眠﹖究竟還能支持到什麼時候﹖
真的不知道。
外面下著很大的雨。因為怕弄濕房間﹐我們不得不關掉那扇唯一的窗。幸好﹐房間裡便祇得我們三個。那僅餘的空氣﹐還能讓我們吸上幾個小時罷﹖房間其實很小。只是一個四尺寬﹑六尺深的斗室。看著那些床位設計﹐我依然不能想像﹐這一間房可以同時容納六個人。
憑倚著窗﹐我看到我們的影子﹐正在全速逃離朦朧的波希米亞夜色。
我想起了十年前的那個夏天。
那年﹐才大學一年級。我們一行十多人﹐從廣州乘火車到北京旅行﹐又由北京乘夜車到呼和浩特。那時候﹐京九鐵路剛通車。因為新鮮﹐所以很受歡迎。我們買不到票子﹐可又很嚮往乘火車旅行﹐於是便決定到廣州﹐乘搭京廣鐵路。
我記得﹐車程差不多要足足一天。那是二十四個小時啊﹗我們是凌晨上車。要在車廂裡過兩個晚上。不過﹐不時在這間房間走走﹐那間房間去去﹐讀讀書﹐談談天﹐說說地﹐唱唱歌﹐時間倒也過得很快。至少﹐到了現在﹐我已記不起那些困在車廂裡面的每一分每一秒。因為那些時間﹐是幾個小時﹑幾個小時的流水般﹐跟隨外面不斷往後退的風景﹐遠離我們而去。
那是我們的青蔥歲月。沒有煩惱﹐沒有懮愁。因為世界沒有什麼事情值得我們為她煩惱。因為世界沒有什麼事情值得我們為她懮愁。世界還待我們去開發。世界還待我們去闖蕩。機會多的是。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努力﹐我們會得到應有的回報。那時候﹐香港依然是個公平的社會。你不會因為你信仰的宗教﹐使你的血汗白流。你也不會因為你的政見﹐使你的努力白費。至少﹐身邊的一切一切﹐社會上的萬事萬物﹐都讓我們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
雨終於停了。其實﹐是我們到了沒有下雨的地方。朋友說﹐那應該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邊界。我望望錶﹐才是凌晨三時。
火車稍停留了一會兒﹐便又繼續他的旅程。我不知道這兒還叫不叫做波希米亞。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前五年﹐捷克和斯洛伐克成為了兩個不同的國家。對於這些歷史﹐我是很無知。因為我的民族是一個不尊重歷史的民族。他們對於自己的歷史也不甚了了﹐遑論談什麼波希米亞。那是一個傳說中的國度罷。
是沒有雨了﹐只是我發覺﹐外面的景色卻越來越朦朧。我努力睜開眼睛﹐好讓自己認清那是晨曦的霧水。不過﹐我相信﹐那是我自己的夢境。
早上八時﹐我們抵達布達佩斯。整夜一切安全。八個小時的車程裡面﹐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也沒有人無緣無故闖了進來。
只是﹐我發覺﹐人是大了。老了。
Friday, October 20, 2006
中學的時候﹐我有兩場很難忘的演講。(當然﹐只在我來說。其他人是否覺得難忘﹐我倒不知道。)
都是中文科的功課。我都是講一個我憎恨的人。
中三的時候﹐我憎恨的人叫林建岳。因為發現自己不能續任南華足球部主席後﹐他便決定帶領那些跟他自己簽了私人合約的七個球員﹐轉投另外一間球會花花。並以自己家族公司的名義贊助這間從前從不起眼的球隊﹐改名叫麗新花花。那時候﹐那七名球員都是南華陣中的正選球員。其實﹐已經事隔幾年﹐不過﹐我記得﹐那天我依然很憤怒。
到了預科﹐林建岳已經在沒有在球壇出沒。麗新花花﹐以至後來的麗新﹐都已退出香港聯賽。那時候﹐我憎恨的人已變了做梁守志。因為那段時間﹐他是東方的領隊。
老實說﹐跟林建岳不一樣﹐梁守志其實沒有做過什麼破壞南華內部的事情。不過﹐他卻帶來了林建岳不能帶來的傷害。
他帶領的東方打破了南華壟斷香港足球的局面﹐成為了一個新的王朝。因為那時候﹐徐克改編笑傲江湖的電影《東方不敗》﹐很受歡迎﹐於是他們都叫那個王朝做東方不敗。更傷擁南躉心的﹐是東方竟然憑著幾個南華的棄將﹐把南華打到落花流水。那年﹐聯賽開鑼日﹐東方便贏了南華4-0。幾個月後﹐我們再在銀牌決賽碰頭。他們更贏到5-0。更不幸地﹐竟然都給梁守志在賽前猜中戰果。猶記得﹐他在電視機裡面那副牙擦﹑不可一世的模樣。
這是我憎恨他的原因。他把南華班霸的形像徹底粉碎。
自精工以後﹐從來沒有球隊能夠這樣大比數地擊敗南華。要知道﹐精工陣中都是在78年世界杯決賽﹐替荷蘭上陣迎戰阿根庭的球員。什麼加賀夫兄弟﹑穆倫﹑尼斯堅斯和南寧加。南寧加在世界杯決賽頂入過一球。穆倫在精工退出後﹐轉投了曼聯。可是﹐東方的正選球員本來都是名不經傳的球員。李健和﹑譚兆偉﹑羅繼華﹑李偉文﹑陳志強等都是在那一年才成為香港球星。當然﹐東方的成功更有很大的程度﹐是給梁守志游說到兩個南華的棄將譚拔士和基亞回港加盟。當年﹐因為希望能給球迷一些新鮮感﹐南華毅然放棄TEMPEST和GREER兩名協助囊括所有錦標的外援。
後來﹐因為財政問題﹐東方不敗王朝也只維持了不過兩三年光景。所有球員都各散東西。梁守志更做了南華管理層。
梁守志之後﹐我憎恨的是鄭兆聰。當年﹐他為了更高的薪金﹐背叛了我對他的支持﹐轉投了南華的另一大敵快譯通。
不過﹐鄭兆聰之後﹐香港足球已再沒有人讓我憎恨。
因為我已對香港足球失去興趣。我不同意﹐南華成勣低落是一個主因。我是在香港故意輸給中國大陸0-7後﹐才放棄香港足球。或者﹐你可以說﹐RICKY CHENG之後﹐我憎恨的便是整個香港足總。
我知道﹐便是南華以後每年都囊括所有錦標﹐那感覺都不會像以前一樣。我說過﹐我再不會讓香港足總在我的口袋裡拿到一毛錢。因為我要它破產倒閉。
那天﹐他們真的傷透了我的心。
都是中文科的功課。我都是講一個我憎恨的人。
中三的時候﹐我憎恨的人叫林建岳。因為發現自己不能續任南華足球部主席後﹐他便決定帶領那些跟他自己簽了私人合約的七個球員﹐轉投另外一間球會花花。並以自己家族公司的名義贊助這間從前從不起眼的球隊﹐改名叫麗新花花。那時候﹐那七名球員都是南華陣中的正選球員。其實﹐已經事隔幾年﹐不過﹐我記得﹐那天我依然很憤怒。
到了預科﹐林建岳已經在沒有在球壇出沒。麗新花花﹐以至後來的麗新﹐都已退出香港聯賽。那時候﹐我憎恨的人已變了做梁守志。因為那段時間﹐他是東方的領隊。
老實說﹐跟林建岳不一樣﹐梁守志其實沒有做過什麼破壞南華內部的事情。不過﹐他卻帶來了林建岳不能帶來的傷害。
他帶領的東方打破了南華壟斷香港足球的局面﹐成為了一個新的王朝。因為那時候﹐徐克改編笑傲江湖的電影《東方不敗》﹐很受歡迎﹐於是他們都叫那個王朝做東方不敗。更傷擁南躉心的﹐是東方竟然憑著幾個南華的棄將﹐把南華打到落花流水。那年﹐聯賽開鑼日﹐東方便贏了南華4-0。幾個月後﹐我們再在銀牌決賽碰頭。他們更贏到5-0。更不幸地﹐竟然都給梁守志在賽前猜中戰果。猶記得﹐他在電視機裡面那副牙擦﹑不可一世的模樣。
這是我憎恨他的原因。他把南華班霸的形像徹底粉碎。
自精工以後﹐從來沒有球隊能夠這樣大比數地擊敗南華。要知道﹐精工陣中都是在78年世界杯決賽﹐替荷蘭上陣迎戰阿根庭的球員。什麼加賀夫兄弟﹑穆倫﹑尼斯堅斯和南寧加。南寧加在世界杯決賽頂入過一球。穆倫在精工退出後﹐轉投了曼聯。可是﹐東方的正選球員本來都是名不經傳的球員。李健和﹑譚兆偉﹑羅繼華﹑李偉文﹑陳志強等都是在那一年才成為香港球星。當然﹐東方的成功更有很大的程度﹐是給梁守志游說到兩個南華的棄將譚拔士和基亞回港加盟。當年﹐因為希望能給球迷一些新鮮感﹐南華毅然放棄TEMPEST和GREER兩名協助囊括所有錦標的外援。
後來﹐因為財政問題﹐東方不敗王朝也只維持了不過兩三年光景。所有球員都各散東西。梁守志更做了南華管理層。
梁守志之後﹐我憎恨的是鄭兆聰。當年﹐他為了更高的薪金﹐背叛了我對他的支持﹐轉投了南華的另一大敵快譯通。
不過﹐鄭兆聰之後﹐香港足球已再沒有人讓我憎恨。
因為我已對香港足球失去興趣。我不同意﹐南華成勣低落是一個主因。我是在香港故意輸給中國大陸0-7後﹐才放棄香港足球。或者﹐你可以說﹐RICKY CHENG之後﹐我憎恨的便是整個香港足總。
我知道﹐便是南華以後每年都囊括所有錦標﹐那感覺都不會像以前一樣。我說過﹐我再不會讓香港足總在我的口袋裡拿到一毛錢。因為我要它破產倒閉。
那天﹐他們真的傷透了我的心。
Thursday, October 19, 2006
才在都柏林住上了半年﹐我想﹐我是染上了他們的酒館文化﹕捧著酒杯﹐便跟萍水相逢的人東拉西扯﹐胡亂地談天說地。
上個月﹐有朋友歐遊﹐我便放了一個星期的假﹐跟他們一起到PRAGUE和BUDAPEST去。
在布拉格的第一個晚上﹐我們到了一間百年老店晚飯。那其實是一間釀酒廠﹐叫U FLEKU。只是﹐也經營餐廳﹐供應傳統捷克食物。他們聲稱﹐自1499年起﹐便開始釀製一種黑色的啤酒。旅遊書說﹐那是一種強烈濃味的啤酒。只是﹐我實在覺得不外如是。我還是喜歡GUINNESS。我想﹐捷克人沒有的﹐是RIVER LIFFEY的污糟水。
餐廳裡面﹐有樂手演奏手琴和喇叭。都是波希米亞的民謠。可能是酒精的興奮作用﹐客人都熱烈地高歌。氣氛很是融合。雖然我不知道他們唱的是什麼﹐不過﹐我也拍著手拍著檯﹐輕輕地哼和。在悅耳的旋律底下﹐我竟然跟鄰座很隨便地聊起天來。他們是一對在英國居住的夫婦。男的是蘇格蘭人﹐女的是香港人﹐姓何。還有一個男同伴﹐叫ALAN。都到了中年。
原來﹐他們都曾在香港住過。何小姐(﹖)說﹐他曾經在TVB上班。之後﹐過了有線電視。是CABLE TV的開荒牛。到有線搬到荃灣後﹐她覺得上班很不方便。跟吳光正反映過﹐希望留在WHARF BUILDING。不得要領下﹐便辭掉有線﹐到了星加坡工作。到現在在英國定居。
談到荃灣﹐我們便拉扯到去深井。望著那杯啤酒﹐講到深井﹐很自然地便說到生力啤。還有燒鵝。
我跟他們說﹐香港現在再沒有釀酒廠的了。便是歷史古蹟都要給拉倒﹐來興建住宅。以前﹐生力啤的那塊地﹐又怎能避免﹖聽到我的說話﹐蘇格蘭人搖搖頭﹐竟然有點感觸。
其實﹐生力啤對我也有很多﹑很多的回憶。甚至可以說﹐沒有生力啤﹐便不可能有現在的我。因為祖父便是在生力啤上班。家裡用的都是印有生力啤標誌的酒杯。讀書時候用的紙張文具﹐很多時候都是生力啤的紀念品。我沒有參觀過那個釀酒廠。我想﹐他們也沒有像GUINNESS一樣﹐開放予遊人。只是﹐猶記得﹐以前在「能記」吃燒鵝﹐總是能看到那些煙囪。
現在﹐都變了。看到的是煙囪般的高樓。一切都唯有放在記憶裡面。
祖父也離開了我們十年。
ALAN提議我們到布拉格的郊外遊覽。他說﹐那兒的景色更美。我記得﹐MyC也是如此介紹。不過﹐我們留在布拉格的時間其實很短。似乎﹐是沒有辦法到郊外去的了。(後來﹐我們是去了VYSEHRAD。不過﹐那只是布拉格的市郊。並不是他們提議的地方。)
在U FLEKU,啤酒是源源不斷供應。是根本不用自己點的。於是﹐所有人客都很興奮。大家都過了一個很開心的夜晚。音樂和酒精﹐既是食物的最佳調味料﹐也是興奮的泉源啊﹗
(U FLEKU二之二)
上個月﹐有朋友歐遊﹐我便放了一個星期的假﹐跟他們一起到PRAGUE和BUDAPEST去。
在布拉格的第一個晚上﹐我們到了一間百年老店晚飯。那其實是一間釀酒廠﹐叫U FLEKU。只是﹐也經營餐廳﹐供應傳統捷克食物。他們聲稱﹐自1499年起﹐便開始釀製一種黑色的啤酒。旅遊書說﹐那是一種強烈濃味的啤酒。只是﹐我實在覺得不外如是。我還是喜歡GUINNESS。我想﹐捷克人沒有的﹐是RIVER LIFFEY的污糟水。
餐廳裡面﹐有樂手演奏手琴和喇叭。都是波希米亞的民謠。可能是酒精的興奮作用﹐客人都熱烈地高歌。氣氛很是融合。雖然我不知道他們唱的是什麼﹐不過﹐我也拍著手拍著檯﹐輕輕地哼和。在悅耳的旋律底下﹐我竟然跟鄰座很隨便地聊起天來。他們是一對在英國居住的夫婦。男的是蘇格蘭人﹐女的是香港人﹐姓何。還有一個男同伴﹐叫ALAN。都到了中年。
原來﹐他們都曾在香港住過。何小姐(﹖)說﹐他曾經在TVB上班。之後﹐過了有線電視。是CABLE TV的開荒牛。到有線搬到荃灣後﹐她覺得上班很不方便。跟吳光正反映過﹐希望留在WHARF BUILDING。不得要領下﹐便辭掉有線﹐到了星加坡工作。到現在在英國定居。
談到荃灣﹐我們便拉扯到去深井。望著那杯啤酒﹐講到深井﹐很自然地便說到生力啤。還有燒鵝。
我跟他們說﹐香港現在再沒有釀酒廠的了。便是歷史古蹟都要給拉倒﹐來興建住宅。以前﹐生力啤的那塊地﹐又怎能避免﹖聽到我的說話﹐蘇格蘭人搖搖頭﹐竟然有點感觸。
其實﹐生力啤對我也有很多﹑很多的回憶。甚至可以說﹐沒有生力啤﹐便不可能有現在的我。因為祖父便是在生力啤上班。家裡用的都是印有生力啤標誌的酒杯。讀書時候用的紙張文具﹐很多時候都是生力啤的紀念品。我沒有參觀過那個釀酒廠。我想﹐他們也沒有像GUINNESS一樣﹐開放予遊人。只是﹐猶記得﹐以前在「能記」吃燒鵝﹐總是能看到那些煙囪。
現在﹐都變了。看到的是煙囪般的高樓。一切都唯有放在記憶裡面。
祖父也離開了我們十年。
ALAN提議我們到布拉格的郊外遊覽。他說﹐那兒的景色更美。我記得﹐MyC也是如此介紹。不過﹐我們留在布拉格的時間其實很短。似乎﹐是沒有辦法到郊外去的了。(後來﹐我們是去了VYSEHRAD。不過﹐那只是布拉格的市郊。並不是他們提議的地方。)
在U FLEKU,啤酒是源源不斷供應。是根本不用自己點的。於是﹐所有人客都很興奮。大家都過了一個很開心的夜晚。音樂和酒精﹐既是食物的最佳調味料﹐也是興奮的泉源啊﹗
(U FLEKU二之二)
Wednesday, October 18, 2006
朋友說﹐旅行的時候﹐最使人興奮的﹐莫過於找到一間很好的店子﹐滿足地吃下一頓美味的當地菜式。
對香港人來說﹐這裡面的確有很多智慧。因為對歷史和藝術都沒有太多的認識﹐到當地餐廳去﹐實在是我們認識那個地方最好也是唯一的途徑。在布達佩斯﹐我找到了ALFÖLDI ÉTTEREM。那是一間以匈牙利魚湯馳名的老店。在布拉格﹐我最喜歡的則是U FLEKU。
出發前﹐做準備工作。翻閱旅遊書﹐看到了介紹U FLEKU後﹐便打定主意,一心要去見識見識。EYEWITNESS TRAVELGUIDE是這樣說的﹕
This cavermous and often raucous brewery and restaurant with its many rooms and lounges is thought to have been founded in 1499, though nobody seems to know for sure. What certain is that there's been an onsite brewery since the early 1900s, and the food is good, reliable upmarket Czech pub fare. The present brewery makes a special strong, drak beer, sold only here.
百年老店﹐總有其過人的地方。更何況﹐他們釀的是黑色的東西。怎能不去拜訪﹖
從都柏林到布拉格﹐乘飛機要差不多三個鐘。加上時差﹐到火車站買好車票到匈牙利﹑在酒店安置妥當後﹐已經是七時多。我們已很餓。於是﹐便決定立即到U FLEKU去。因為就在酒店後邊兩個街口。都在新區。
那是一條小街。沒有太多街燈﹐所以很黑。不過﹐只要走到了KREMENCOVA街﹐便不可能找不到。因為U FLEKU是那條街上唯一一間有歌聲傳出來的地方。
裡面的確有很多間大廳。都像英國古老寄宿學校的飯堂﹐擺滿了木製的長檯和長凳。是晚飯的時候﹐所以有很多人。他們一邊飲酒用膳﹐一邊高聲唱歌。加上駐場樂手的手琴和大喇叭伴奏﹐實在讓人感覺很興奮。縱然﹐我聽不到他們唱的是什麼。都是波希米亞的民謠罷。
侍應好不容易在一張長檯﹐給我們找來了一些空檔。在我的左手邊﹐是一對日本男女﹔在我的右手邊﹐則是兩個操英語的中年漢和一個亞洲裔女人。我跟他們點了點頭﹐發覺那個女人很面善﹐好像在那兒見過。可是﹐一時間卻又想不起來。
才剛坐下﹐侍應便一聲不響地給我們遞上了三大杯啤酒。就是旅遊書說的DARK BEER,叫FLEKOVSKÉ。還未喝下第一口﹐侍應便又走過來放下餐牌﹐也同時問我們要不要嚐嚐BECHEROVKA。他們說﹐那是捷克特色的APERITIF。我望著那小杯的金黃色液體﹐心知一定是很強烈的酒精。不過﹐既然是捷克名產﹐便是肚子很餓﹐也是要試一試的。我們便從盤子裡拿走了三杯。算是飯前﹐給腸胃消毒一下。
我們按著書上介紹﹐點了一些捷克的傳統菜式。有凍肉﹑烤鴨和燴牛肉。都很可口。當然﹐我不排除那是我們太過肚餓的關係。況且﹐在這樣讓人興奮的環境底下﹐什麼食物也會變得很美味。從來﹐音樂和酒精﹐都是食物最佳的調味料。
大廳裡﹐大家都跟著樂手的演奏﹐或拍著手或拍著檯﹐大聲大聲地高歌起來。都是很悅耳的旋律。我也不其然擺動著身體﹐輕輕地哼和著。在歡樂的歌聲裡﹐我跟鄰座的那個中年漢打了個照面。我便禮貌地拿起酒杯敬了他一下。
他笑著問我﹐你們是從香港來的嗎﹖我老婆說﹐你們是從香港來的。他指了指那個亞洲裔女人。那女人便立即伸出右手﹐自我介紹道﹐我姓何﹐是香港人。不過﹐現在住在WINSOR附近。我跟她握著手﹐也用英文回答說﹐我姓N-﹐也是香港人。不過﹐現在在都柏林生活。
她的丈夫聽到後﹐便跟我講了一句愛爾蘭文。我說﹐我不懂得回答。因為我還是一個NEW DUBLINER。難道你是一個愛爾蘭人﹖
不﹗我來自蘇格蘭。他跟我說﹐SCOTTISH與IRISH是差不多的。
他指著那杯黑色的啤酒﹐問我跟GUINNESS有什麼分別。我微笑著回答﹐當然差得遠。RIVER VALTAVA的河水太乾淨了﹐根本不是做BLACK STUFF的水。他們都笑得很開心﹐包括跟他們同行的那個中年漢。他稱自己叫ALAN。
我說的倒是實話。我的確較喜歡GUINNESS。FLEKOVSKÉ太淡了,就像白開水。來到愛爾蘭後﹐GUINNESS已是我唯一飲的啤酒。
(U FLEKU二之一)
對香港人來說﹐這裡面的確有很多智慧。因為對歷史和藝術都沒有太多的認識﹐到當地餐廳去﹐實在是我們認識那個地方最好也是唯一的途徑。在布達佩斯﹐我找到了ALFÖLDI ÉTTEREM。那是一間以匈牙利魚湯馳名的老店。在布拉格﹐我最喜歡的則是U FLEKU。
出發前﹐做準備工作。翻閱旅遊書﹐看到了介紹U FLEKU後﹐便打定主意,一心要去見識見識。EYEWITNESS TRAVELGUIDE是這樣說的﹕
This cavermous and often raucous brewery and restaurant with its many rooms and lounges is thought to have been founded in 1499, though nobody seems to know for sure. What certain is that there's been an onsite brewery since the early 1900s, and the food is good, reliable upmarket Czech pub fare. The present brewery makes a special strong, drak beer, sold only here.
百年老店﹐總有其過人的地方。更何況﹐他們釀的是黑色的東西。怎能不去拜訪﹖
從都柏林到布拉格﹐乘飛機要差不多三個鐘。加上時差﹐到火車站買好車票到匈牙利﹑在酒店安置妥當後﹐已經是七時多。我們已很餓。於是﹐便決定立即到U FLEKU去。因為就在酒店後邊兩個街口。都在新區。
那是一條小街。沒有太多街燈﹐所以很黑。不過﹐只要走到了KREMENCOVA街﹐便不可能找不到。因為U FLEKU是那條街上唯一一間有歌聲傳出來的地方。
裡面的確有很多間大廳。都像英國古老寄宿學校的飯堂﹐擺滿了木製的長檯和長凳。是晚飯的時候﹐所以有很多人。他們一邊飲酒用膳﹐一邊高聲唱歌。加上駐場樂手的手琴和大喇叭伴奏﹐實在讓人感覺很興奮。縱然﹐我聽不到他們唱的是什麼。都是波希米亞的民謠罷。
侍應好不容易在一張長檯﹐給我們找來了一些空檔。在我的左手邊﹐是一對日本男女﹔在我的右手邊﹐則是兩個操英語的中年漢和一個亞洲裔女人。我跟他們點了點頭﹐發覺那個女人很面善﹐好像在那兒見過。可是﹐一時間卻又想不起來。
才剛坐下﹐侍應便一聲不響地給我們遞上了三大杯啤酒。就是旅遊書說的DARK BEER,叫FLEKOVSKÉ。還未喝下第一口﹐侍應便又走過來放下餐牌﹐也同時問我們要不要嚐嚐BECHEROVKA。他們說﹐那是捷克特色的APERITIF。我望著那小杯的金黃色液體﹐心知一定是很強烈的酒精。不過﹐既然是捷克名產﹐便是肚子很餓﹐也是要試一試的。我們便從盤子裡拿走了三杯。算是飯前﹐給腸胃消毒一下。
我們按著書上介紹﹐點了一些捷克的傳統菜式。有凍肉﹑烤鴨和燴牛肉。都很可口。當然﹐我不排除那是我們太過肚餓的關係。況且﹐在這樣讓人興奮的環境底下﹐什麼食物也會變得很美味。從來﹐音樂和酒精﹐都是食物最佳的調味料。
大廳裡﹐大家都跟著樂手的演奏﹐或拍著手或拍著檯﹐大聲大聲地高歌起來。都是很悅耳的旋律。我也不其然擺動著身體﹐輕輕地哼和著。在歡樂的歌聲裡﹐我跟鄰座的那個中年漢打了個照面。我便禮貌地拿起酒杯敬了他一下。
他笑著問我﹐你們是從香港來的嗎﹖我老婆說﹐你們是從香港來的。他指了指那個亞洲裔女人。那女人便立即伸出右手﹐自我介紹道﹐我姓何﹐是香港人。不過﹐現在住在WINSOR附近。我跟她握著手﹐也用英文回答說﹐我姓N-﹐也是香港人。不過﹐現在在都柏林生活。
她的丈夫聽到後﹐便跟我講了一句愛爾蘭文。我說﹐我不懂得回答。因為我還是一個NEW DUBLINER。難道你是一個愛爾蘭人﹖
不﹗我來自蘇格蘭。他跟我說﹐SCOTTISH與IRISH是差不多的。
他指著那杯黑色的啤酒﹐問我跟GUINNESS有什麼分別。我微笑著回答﹐當然差得遠。RIVER VALTAVA的河水太乾淨了﹐根本不是做BLACK STUFF的水。他們都笑得很開心﹐包括跟他們同行的那個中年漢。他稱自己叫ALAN。
我說的倒是實話。我的確較喜歡GUINNESS。FLEKOVSKÉ太淡了,就像白開水。來到愛爾蘭後﹐GUINNESS已是我唯一飲的啤酒。
(U FLEKU二之一)
Tuesday, October 17, 2006
最近﹐電影院都擠滿了人。因為有幾部影評人給予滿分的電影上演。THE DEPARTED是其中一部。另一部是LITTLE MISS SUNSHINE。THE DEVIL WEARS PRADA在坊間也有很高的評價。
東歐旅遊期間﹐無意中跟朋友談起無間道的荷李活版本。怎料到才回到愛爾蘭﹐便發現THE DEPARTED快要上演。我的確很期待這部電影。我很想看看經過荷李活的包裝﹐在馬田史高西斯的執導下﹐這一部香港電影會變成什麼模樣。
THE ORIGINAL OF THIS MARTIN SCORSESE PICTURE IS A HONG KONG MOVIE THAT IS MY ALL-TIME FAVOURITE.
這是我跟同事的介紹。
故事其實是三集無間道的濃縮版。當然有些角色是無可避免地刪掉了。像吳鎮宇和劉嘉玲﹐黎明和陳道仁。陳慧琳跟鄭秀文則合二為一﹐變成了週旋在MATT DAMON和DICAPRIO之間的女人。
電影很有馬田史高西斯的風格。因此﹐除了故事外﹐完全不像原裝版本。
JACK NICHOLSON實在比曾志偉更能演活黑社會頭子這個角色。奧斯卡影帝的確比香港金像獎影帝出色。不過﹐除此之外﹐香港的演員實在不比荷李活的差。至少﹐我覺得﹐劉德華就比MATT DAMON演得好。麥迪文就是缺少了那個很想做回好人的層次。當然﹐黃秋生更是無人能敵。無間道裡面的黃SIR是我最喜歡的角色。
假如未有看過無間道﹐THE DEPARTED的而且確是一部很出色的電影。便是金融時報也這樣介紹﹕SCORSESE'S BEST SINCE GOODFELLAS。
只是近來﹐我最喜歡的倒是那部英國製作﹕THE QUEEN。
故事很簡單。就是講英女皇ELIZABETH II在戴安娜車禍喪生後到舉殯這一段期間的心路歷程。便是因為故事太簡單﹐更顯得導演和編劇的功力。不肯定劇本出自英國人的手。不過﹐的確充滿了英式幽默。那些明讚暗踩﹐自我挖苦﹐實在看得人不其然發出會心微笑。原來﹐除了TONY CURTIS外﹐現今也有人能寫得出這樣好的英國劇本。影評說﹐EXCELLENT DIALOGUE。果然不虛。
一邊看電影﹐一邊想到陶傑的《泰晤士河畔》。他的確很了解英國人的心態。我記得﹐他曾經說過﹐英國人總把喜怒哀樂收藏在一己之內﹐不形於色。在他的成名作裡面﹐便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英國人的喪禮﹐寧靜而素潔。絕少有撫棺痛哭﹑呼天搶地的情景。對逝者的哀思是淡括而深遠﹐極其量只有飲泣的點綴﹐大哭的強調已是多餘。八六年尤德之逝﹐其未亡人的表現是那樣莊重而具風度﹐那是英國人喪禮的典範。一個對死亡的態度如此冷靜的民族﹐是成熟得可驚的。」
故事結尾﹐英女皇不就是跟TONY BLAIR講了這樣的對白嗎﹖
面對著現代化的大潮流﹐一個民族的性格是否也應隨著改變﹖在走向世界大同的同時﹐我們是否要放棄本身跟別人的分別﹖實在是一個很值得深究的問題。
在遠東的那個古老漁村﹐他們便向世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教訓﹕在任何一個大潮流下﹐迷失自己﹐便是迷失世界﹐後果真的可以很嚴重。唯有把握著自己跟別人的不同﹐回歸或合拼方有著其真正的意義。要不﹐那便是集體的墮落。
這是一部嚴肅但輕鬆的小品﹐讓人看得很舒服。
東歐旅遊期間﹐無意中跟朋友談起無間道的荷李活版本。怎料到才回到愛爾蘭﹐便發現THE DEPARTED快要上演。我的確很期待這部電影。我很想看看經過荷李活的包裝﹐在馬田史高西斯的執導下﹐這一部香港電影會變成什麼模樣。
THE ORIGINAL OF THIS MARTIN SCORSESE PICTURE IS A HONG KONG MOVIE THAT IS MY ALL-TIME FAVOURITE.
這是我跟同事的介紹。
故事其實是三集無間道的濃縮版。當然有些角色是無可避免地刪掉了。像吳鎮宇和劉嘉玲﹐黎明和陳道仁。陳慧琳跟鄭秀文則合二為一﹐變成了週旋在MATT DAMON和DICAPRIO之間的女人。
電影很有馬田史高西斯的風格。因此﹐除了故事外﹐完全不像原裝版本。
JACK NICHOLSON實在比曾志偉更能演活黑社會頭子這個角色。奧斯卡影帝的確比香港金像獎影帝出色。不過﹐除此之外﹐香港的演員實在不比荷李活的差。至少﹐我覺得﹐劉德華就比MATT DAMON演得好。麥迪文就是缺少了那個很想做回好人的層次。當然﹐黃秋生更是無人能敵。無間道裡面的黃SIR是我最喜歡的角色。
假如未有看過無間道﹐THE DEPARTED的而且確是一部很出色的電影。便是金融時報也這樣介紹﹕SCORSESE'S BEST SINCE GOODFELLAS。
只是近來﹐我最喜歡的倒是那部英國製作﹕THE QUEEN。
故事很簡單。就是講英女皇ELIZABETH II在戴安娜車禍喪生後到舉殯這一段期間的心路歷程。便是因為故事太簡單﹐更顯得導演和編劇的功力。不肯定劇本出自英國人的手。不過﹐的確充滿了英式幽默。那些明讚暗踩﹐自我挖苦﹐實在看得人不其然發出會心微笑。原來﹐除了TONY CURTIS外﹐現今也有人能寫得出這樣好的英國劇本。影評說﹐EXCELLENT DIALOGUE。果然不虛。
一邊看電影﹐一邊想到陶傑的《泰晤士河畔》。他的確很了解英國人的心態。我記得﹐他曾經說過﹐英國人總把喜怒哀樂收藏在一己之內﹐不形於色。在他的成名作裡面﹐便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英國人的喪禮﹐寧靜而素潔。絕少有撫棺痛哭﹑呼天搶地的情景。對逝者的哀思是淡括而深遠﹐極其量只有飲泣的點綴﹐大哭的強調已是多餘。八六年尤德之逝﹐其未亡人的表現是那樣莊重而具風度﹐那是英國人喪禮的典範。一個對死亡的態度如此冷靜的民族﹐是成熟得可驚的。」
故事結尾﹐英女皇不就是跟TONY BLAIR講了這樣的對白嗎﹖
面對著現代化的大潮流﹐一個民族的性格是否也應隨著改變﹖在走向世界大同的同時﹐我們是否要放棄本身跟別人的分別﹖實在是一個很值得深究的問題。
在遠東的那個古老漁村﹐他們便向世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教訓﹕在任何一個大潮流下﹐迷失自己﹐便是迷失世界﹐後果真的可以很嚴重。唯有把握著自己跟別人的不同﹐回歸或合拼方有著其真正的意義。要不﹐那便是集體的墮落。
這是一部嚴肅但輕鬆的小品﹐讓人看得很舒服。
Monday, October 16, 2006
中秋過了﹐冬天還會遠嗎﹖
鬧鐘還未有響﹐我便從睡夢中醒過來。摸黑找來放在床頭的手錶。原來﹐才只是四時五十五分﹗我已記不起這是連續第幾天發生的事情。也許﹐望望月曆﹐會有個大概。
自踏入十月以後﹐我似乎未有一覺睡到尾。都睡得不大好。總會在五時左右醒一醒。不過﹐輾轉一會兒﹐也可以再次入夢。可惜﹐已不是剛才的一個好夢。於是﹐到了六時許﹐我又會再睜開眼睛。看著滴答滴答的鬧鐘﹐算著算著那悄悄溜走的一分一秒。直到鬧鐘響起的一刻。我便爬起身來﹐刷牙洗臉吃早餐﹐準備上班。
今天﹐似乎是比平時更早了點醒過來。我暗罵自己。
印象中﹐在醒過來前的一秒﹐我曾經可以控制到自己多留在那個夢鄉裡面。印象中﹐在睜開眼睛前的一秒﹐我曾經可以控制到自己不那麼輕易醒過來。因為﹐我知道﹐醒過來後﹐已根本沒有可能延續到剛才那個未完的夢。那個我和她一起的夢。
我努力嘗試走回之前的那個夢裡面﹐不過都是徒勞無功。結果﹐把自己弄得很累。到鬧鐘響起來的時候﹐我實在不想起床。我很想多睡半天。
在床上多耽了幾分鐘後﹐便無奈地想起了公司檯頭的工作。
我知道﹐又要是一天的開始。
只是太陽還未出來。客廳很黑﹐只得遠處那座大廈射過來的微弱的光。我不得不開著燈來吃早餐。把所有刀叉碟子清洗完畢後﹐我才看到太陽慢慢地探出他的頭來。
我在火車上讀著報紙。偶然望出窗外﹐我看到一個藍色的天空。今天的天氣應該很好罷。難得連續四天好天氣﹗心頭有點興奮﹐今天的工作應該很順利。
我又在火車上讀著報紙。偶然望出窗外﹐我發現天空很黑暗。街燈已經亮了。原來夜幕已經低垂。我望望錶﹐才不過六時。我呆呆地想像著幾個星期後的情景。我記得﹐表弟說過﹐冬天的時候﹐下午四時多﹐都柏林的天空便會黑齊。我想﹐應該是不遠的事情了。
才只是十月。似乎﹐冬季的確可以很漫長。
吃過晚餐﹐我躺在沙發上﹐看著電影《審訊》。那是按FRANZ KFAKA的小說改編的電影。是BBC的製作。我也在微弱的燈光下﹐讀著《玫瑰的名字》。那是意大利作家UMBERTO ECO的成名作。昨天晚上﹐因為實在太累﹐還未讀畢第一章﹐便已悄然墮進夢鄉。卻竟然在夢裡面﹐跟她重遇上。竟然在這樣的一個月份﹐在這樣的一個夢境裡面。一年之後﹐我們又再夜遊普雷詩旺。
我望著那張書籤。我望著那個玫瑰般的名字。是她給我的名片。是那位藝術家。她跟她都有著相同的名字。
竟然是那麼的巧合。
十月尾那個銀行假期快來了。我不其然的想起了她。
十月﹐總是個使人難忘的月份。
中秋過了﹐冬天還會遠嗎﹖
我聽著打在玻璃窗上的雨點。原來﹐冬季的確可以很漫長。
鬧鐘還未有響﹐我便從睡夢中醒過來。摸黑找來放在床頭的手錶。原來﹐才只是四時五十五分﹗我已記不起這是連續第幾天發生的事情。也許﹐望望月曆﹐會有個大概。
自踏入十月以後﹐我似乎未有一覺睡到尾。都睡得不大好。總會在五時左右醒一醒。不過﹐輾轉一會兒﹐也可以再次入夢。可惜﹐已不是剛才的一個好夢。於是﹐到了六時許﹐我又會再睜開眼睛。看著滴答滴答的鬧鐘﹐算著算著那悄悄溜走的一分一秒。直到鬧鐘響起的一刻。我便爬起身來﹐刷牙洗臉吃早餐﹐準備上班。
今天﹐似乎是比平時更早了點醒過來。我暗罵自己。
印象中﹐在醒過來前的一秒﹐我曾經可以控制到自己多留在那個夢鄉裡面。印象中﹐在睜開眼睛前的一秒﹐我曾經可以控制到自己不那麼輕易醒過來。因為﹐我知道﹐醒過來後﹐已根本沒有可能延續到剛才那個未完的夢。那個我和她一起的夢。
我努力嘗試走回之前的那個夢裡面﹐不過都是徒勞無功。結果﹐把自己弄得很累。到鬧鐘響起來的時候﹐我實在不想起床。我很想多睡半天。
在床上多耽了幾分鐘後﹐便無奈地想起了公司檯頭的工作。
我知道﹐又要是一天的開始。
只是太陽還未出來。客廳很黑﹐只得遠處那座大廈射過來的微弱的光。我不得不開著燈來吃早餐。把所有刀叉碟子清洗完畢後﹐我才看到太陽慢慢地探出他的頭來。
我在火車上讀著報紙。偶然望出窗外﹐我看到一個藍色的天空。今天的天氣應該很好罷。難得連續四天好天氣﹗心頭有點興奮﹐今天的工作應該很順利。
我又在火車上讀著報紙。偶然望出窗外﹐我發現天空很黑暗。街燈已經亮了。原來夜幕已經低垂。我望望錶﹐才不過六時。我呆呆地想像著幾個星期後的情景。我記得﹐表弟說過﹐冬天的時候﹐下午四時多﹐都柏林的天空便會黑齊。我想﹐應該是不遠的事情了。
才只是十月。似乎﹐冬季的確可以很漫長。
吃過晚餐﹐我躺在沙發上﹐看著電影《審訊》。那是按FRANZ KFAKA的小說改編的電影。是BBC的製作。我也在微弱的燈光下﹐讀著《玫瑰的名字》。那是意大利作家UMBERTO ECO的成名作。昨天晚上﹐因為實在太累﹐還未讀畢第一章﹐便已悄然墮進夢鄉。卻竟然在夢裡面﹐跟她重遇上。竟然在這樣的一個月份﹐在這樣的一個夢境裡面。一年之後﹐我們又再夜遊普雷詩旺。
我望著那張書籤。我望著那個玫瑰般的名字。是她給我的名片。是那位藝術家。她跟她都有著相同的名字。
竟然是那麼的巧合。
十月尾那個銀行假期快來了。我不其然的想起了她。
十月﹐總是個使人難忘的月份。
中秋過了﹐冬天還會遠嗎﹖
我聽著打在玻璃窗上的雨點。原來﹐冬季的確可以很漫長。
Sunday, October 15, 2006
我們乘船遊多瑙河。經過了國會大樓﹐來到了GÉLLERT HOTEL。便在酒店的庭園餐廳來了一個HIGH TEA。
酒店在GÉLLERT HILL的山腳。建於1912-1918年﹐是一間溫泉酒店。其實﹐據文獻記載﹐早於十三世紀﹐匈牙利人已發現這兒的地下泉水有治療效用。酒店的前身便是醫院。GÉLLERT是位主教﹐在十一世紀來到布達佩斯﹐宣揚基督教﹐卻惹來一些民眾反感。有一晚﹐他們便捉了主教﹐放他在酒筒裡面﹐然後從山頂摔下至死。(說不定﹐電影《黑社會》也是在此偷橋。)後人為了紀念他﹐便把這一座山命名為GÉLLERT HILL。山上也為他豎立了一個銅像。手持十字架﹐眼望多瑙河。匈牙利人以為﹐他會永遠祝福布達佩斯。
我們坐在庭園餐廳裡﹐要了一些蛋糕和三明治。我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欣賞SZABADSÁG HID鐵橋和在她下面流過的藍色河水。
餐廳外面有一張海報。上面寫道﹕鋼琴師JÓZSEF K-會在此演奏。似乎﹐K-應該有點名氣。至少﹐餐廳會以他招徠顧客。海報說﹐K-只會在晚上彈奏鋼琴。豈料﹐卻給我們在太陽西沉的時候遇上了。聽見琴聲﹐有些客人立即拿起自己的杯﹐走到鋼琴附近坐下。
K-彈了一些李斯特的作品。也有一些我不認識的鋼琴曲。每當K-奏畢一曲﹐客人都很熱烈地鼓掌。
我知道﹐這個城市也是一個音樂之都﹐孕育了不少美妙樂章。我最喜歡的﹐始終是電影《布達佩斯之戀》的主題曲。出發前﹐我便想過要在布達佩斯聽一聽GLOOMY SUNDAY。我想﹐唯有在怡人景色下﹐我們方能真正感受到那首樂曲的那個淒怨層次。因為曲子美麗動人的地方﹐會給週邊的風景壓制著﹐好讓那哀怨的感覺突顯起來。
環望四週﹐在樹蔭下﹐在藍色多瑙河旁﹐遠眺著CHAIN BRIDGE,這也實在是一個寫意的地方。於是﹐便跟侍應說要點歌。才還未完成一句完整句子﹐耳邊便傳來了一陣淒美的樂聲。
迎著河風﹐我想起了電影裡面的女主角。這是一首寫給她的鋼琴曲。也想起了她和他和他的故事。當然﹐還有他。傳說﹐有很多人聽了這首歌後﹐都憂鬱得跑去自殺。
吃過下午茶後﹐我們便到酒店附近的洞窟教堂參觀。那兒位置更高﹐整條SZABADSÁG HID鐵橋都盡入眼帘。
顧名思義﹐教堂建在GÉLLERT HILL的一個洞窟裡面。它在十三世紀落成。1934年開始﹐是一些從波蘭逃亡的憎侶的避難所。到1959年﹐共產黨禁止了這間教堂的一切活動。他們說﹐這兒的憎侶都犯了叛國罪。於是﹐把整座教堂封了。至1989年8月27日重開。教堂裡面有ST KOLBE的畫像。二次大戰期間﹐他犧牲了自己來保護AUSCHWITZ集中營的人。也有一個石刻﹐寫滿給抓了去AUSCHWITZ士兵的名字。
在這一個神聖莊嚴的地方﹐我竟然開始哼起了GLOOMY SUNDAY的曲子。
在SZABADSÁG HID鐵橋襯托下﹐遙望著對岸的國會大樓﹐我看到一個又一個匈牙利人憂鬱地走向自由。
酒店在GÉLLERT HILL的山腳。建於1912-1918年﹐是一間溫泉酒店。其實﹐據文獻記載﹐早於十三世紀﹐匈牙利人已發現這兒的地下泉水有治療效用。酒店的前身便是醫院。GÉLLERT是位主教﹐在十一世紀來到布達佩斯﹐宣揚基督教﹐卻惹來一些民眾反感。有一晚﹐他們便捉了主教﹐放他在酒筒裡面﹐然後從山頂摔下至死。(說不定﹐電影《黑社會》也是在此偷橋。)後人為了紀念他﹐便把這一座山命名為GÉLLERT HILL。山上也為他豎立了一個銅像。手持十字架﹐眼望多瑙河。匈牙利人以為﹐他會永遠祝福布達佩斯。
我們坐在庭園餐廳裡﹐要了一些蛋糕和三明治。我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欣賞SZABADSÁG HID鐵橋和在她下面流過的藍色河水。
餐廳外面有一張海報。上面寫道﹕鋼琴師JÓZSEF K-會在此演奏。似乎﹐K-應該有點名氣。至少﹐餐廳會以他招徠顧客。海報說﹐K-只會在晚上彈奏鋼琴。豈料﹐卻給我們在太陽西沉的時候遇上了。聽見琴聲﹐有些客人立即拿起自己的杯﹐走到鋼琴附近坐下。
K-彈了一些李斯特的作品。也有一些我不認識的鋼琴曲。每當K-奏畢一曲﹐客人都很熱烈地鼓掌。
我知道﹐這個城市也是一個音樂之都﹐孕育了不少美妙樂章。我最喜歡的﹐始終是電影《布達佩斯之戀》的主題曲。出發前﹐我便想過要在布達佩斯聽一聽GLOOMY SUNDAY。我想﹐唯有在怡人景色下﹐我們方能真正感受到那首樂曲的那個淒怨層次。因為曲子美麗動人的地方﹐會給週邊的風景壓制著﹐好讓那哀怨的感覺突顯起來。
環望四週﹐在樹蔭下﹐在藍色多瑙河旁﹐遠眺著CHAIN BRIDGE,這也實在是一個寫意的地方。於是﹐便跟侍應說要點歌。才還未完成一句完整句子﹐耳邊便傳來了一陣淒美的樂聲。
迎著河風﹐我想起了電影裡面的女主角。這是一首寫給她的鋼琴曲。也想起了她和他和他的故事。當然﹐還有他。傳說﹐有很多人聽了這首歌後﹐都憂鬱得跑去自殺。
吃過下午茶後﹐我們便到酒店附近的洞窟教堂參觀。那兒位置更高﹐整條SZABADSÁG HID鐵橋都盡入眼帘。
顧名思義﹐教堂建在GÉLLERT HILL的一個洞窟裡面。它在十三世紀落成。1934年開始﹐是一些從波蘭逃亡的憎侶的避難所。到1959年﹐共產黨禁止了這間教堂的一切活動。他們說﹐這兒的憎侶都犯了叛國罪。於是﹐把整座教堂封了。至1989年8月27日重開。教堂裡面有ST KOLBE的畫像。二次大戰期間﹐他犧牲了自己來保護AUSCHWITZ集中營的人。也有一個石刻﹐寫滿給抓了去AUSCHWITZ士兵的名字。
在這一個神聖莊嚴的地方﹐我竟然開始哼起了GLOOMY SUNDAY的曲子。
在SZABADSÁG HID鐵橋襯托下﹐遙望著對岸的國會大樓﹐我看到一個又一個匈牙利人憂鬱地走向自由。
Saturday, October 14, 2006
望著綠色軍團在塞浦路斯給主隊蹂躪﹐整個愛爾蘭都變得死寂一片。那是他們在歐洲國家杯外圍賽的第二場比賽。
歐洲足球的平均水準當然高。不過﹐也像中國大陸的貧富懸殊一樣﹐最好的一些跟最差的一些﹐有著九千七百萬丈遠。便是中游位置的國家﹐他們跟像SAN MARINO、ANDORRA、MALTA、LUXEMBOURG和LIECHTENSTEIN這些國家隊﹐也有一段很大的差距。因此﹐有人提出﹐先要那些「十年才贏得一場國際賽的國家」﹐先來一個外圍賽的外圍賽﹐以免經常出現像上個月德國對聖馬力諾的比賽。那場比賽﹐德國作客贏13-0。
CYPRUS其實也是歐洲裡面的一隊魚腩。很多時候﹐他們都會以全敗的成勣完成外圍賽。故此﹐輸給他們﹐實在是歐洲國家的一大恥辱。如果還要輸到5-2,那將是國家的黑暗時候。
於是﹐上星期六後﹐這個島嶼都給一片黑沉沉的死氣包圍著。全個愛爾蘭都在討論領隊史當頓的失職。他上任後﹐愛爾蘭踢了五場比賽﹐輸了四場﹐失了十一球。很多很大的聲音﹐要他立即請辭。他們以為﹐這位前利物浦的球員實在沒有管理球隊的能力。他不能把十一個球員融成一隊球隊。從電視所見﹐面對著塞浦路斯﹐愛爾蘭的球員便如同一盤散沙。任由對方推進﹐任由對方盤扭。中場沒有人攔截﹐後防沒有人解圍﹐前面兩個前鋒如同做了無名氏。沒有士氣﹐沒有靈魂。失球後沒有懊惱﹐輸掉比賽後也沒有失望。假如不是看過香港慘敗0-7的比賽﹐我一定以為那一隊愛爾蘭國家隊是世界史上最差的球隊。
星期一﹐公司TEA TIME的時候﹐跟AIDAN講開足球。我笑著跟他說﹐面對著塞浦路斯﹐也要失五球。星期三﹐在LANSDOWNE ROAD面對著捷克﹐實在不敢想像。要知道﹐捷克在FIFA排第七。
AIDAN搖搖頭苦笑道﹐你永遠不會清楚愛爾蘭足球隊。因為他們很痴線。面對強隊﹐他們向來都很有辦法應付。
我望著他的臉﹐也不知道說些什麼好了。也許﹐AIDAN是對的。史當頓帶隊的首場比賽﹐他們贏瑞典3-0。不過﹐也不好忘記﹐接著下來﹐他們先敗給智利0-1,然後慘吞荷蘭四隻光蛋。作客德國﹐亦敗走0-1。沒有打進入球。
其實﹐我很明白愛爾蘭人的感受。
從小﹐代表我到國際比賽的那隊球隊﹐都是輸多贏少。印象中﹐甚至沒有帶給過我什麼驚喜。他們未曾出線過世界杯。便是亞洲杯﹐他們也是那些在外圍賽止步的球隊。也許﹐他們曾經是亞洲的冰島﹑芬蘭。不過﹐近來﹐他們越來越像馬爾他或盧森堡。
望著代表自己到國際比賽的球隊﹐給人蹂躪﹐的確是一件很難受的事情。因為那是切膚之痛。不過﹐當看到他們毫無鬥心﹐夢遊球場﹐任憑對手擺布﹐那更是千支針刺在心的感覺。假如對手是一隊不X知所謂的球隊﹐那傷口可就永不會痊癒。每年總有些時候﹐會有些血絲滲出來。量不多﹐但依然隱隱作痛。唯有來些發泄﹐才能勉強暫時忘記那永不結焦的傷口。
在愛爾蘭﹐大家都爭相表達對球隊的不滿。所有報紙的頭版都是慘敗給塞浦路斯的消息。電視都是要求史當頓下臺的聲音。在直播對捷克的比賽前﹐評述員說﹐今天的陣容﹐有六個變動啊﹗你怎樣看﹖另一個則回答道﹐便是如何派什麼人打正選﹐都一定比上場的陣容強。
的確比上場強。強多了。因為球員都知道羞恥。都知道他們實在傷透了人民的心。
雖然他們沒有如AIDAN所講﹐擊敗了捷克。不過﹐他們的表現的確有很大很大的進步。至少﹐讓人看得到他們的鬥心。他們被捷克逼和1-1。
我記得﹐上次﹐香港輸掉給中國0-7後﹐大家都沒有當它是一回事。報紙沒有大幅批評。市民也沒有表達不滿。電視臺的評述員甚至暗罵香港為何不多輸一球﹐好讓中國出線世界杯。之後﹐香港隊在國際賽的表現依然乏善足陳。
我不知道﹐在失掉十三球給德國後﹐聖馬力諾的市面是否跟香港一樣。
歐洲足球的平均水準當然高。不過﹐也像中國大陸的貧富懸殊一樣﹐最好的一些跟最差的一些﹐有著九千七百萬丈遠。便是中游位置的國家﹐他們跟像SAN MARINO、ANDORRA、MALTA、LUXEMBOURG和LIECHTENSTEIN這些國家隊﹐也有一段很大的差距。因此﹐有人提出﹐先要那些「十年才贏得一場國際賽的國家」﹐先來一個外圍賽的外圍賽﹐以免經常出現像上個月德國對聖馬力諾的比賽。那場比賽﹐德國作客贏13-0。
CYPRUS其實也是歐洲裡面的一隊魚腩。很多時候﹐他們都會以全敗的成勣完成外圍賽。故此﹐輸給他們﹐實在是歐洲國家的一大恥辱。如果還要輸到5-2,那將是國家的黑暗時候。
於是﹐上星期六後﹐這個島嶼都給一片黑沉沉的死氣包圍著。全個愛爾蘭都在討論領隊史當頓的失職。他上任後﹐愛爾蘭踢了五場比賽﹐輸了四場﹐失了十一球。很多很大的聲音﹐要他立即請辭。他們以為﹐這位前利物浦的球員實在沒有管理球隊的能力。他不能把十一個球員融成一隊球隊。從電視所見﹐面對著塞浦路斯﹐愛爾蘭的球員便如同一盤散沙。任由對方推進﹐任由對方盤扭。中場沒有人攔截﹐後防沒有人解圍﹐前面兩個前鋒如同做了無名氏。沒有士氣﹐沒有靈魂。失球後沒有懊惱﹐輸掉比賽後也沒有失望。假如不是看過香港慘敗0-7的比賽﹐我一定以為那一隊愛爾蘭國家隊是世界史上最差的球隊。
星期一﹐公司TEA TIME的時候﹐跟AIDAN講開足球。我笑著跟他說﹐面對著塞浦路斯﹐也要失五球。星期三﹐在LANSDOWNE ROAD面對著捷克﹐實在不敢想像。要知道﹐捷克在FIFA排第七。
AIDAN搖搖頭苦笑道﹐你永遠不會清楚愛爾蘭足球隊。因為他們很痴線。面對強隊﹐他們向來都很有辦法應付。
我望著他的臉﹐也不知道說些什麼好了。也許﹐AIDAN是對的。史當頓帶隊的首場比賽﹐他們贏瑞典3-0。不過﹐也不好忘記﹐接著下來﹐他們先敗給智利0-1,然後慘吞荷蘭四隻光蛋。作客德國﹐亦敗走0-1。沒有打進入球。
其實﹐我很明白愛爾蘭人的感受。
從小﹐代表我到國際比賽的那隊球隊﹐都是輸多贏少。印象中﹐甚至沒有帶給過我什麼驚喜。他們未曾出線過世界杯。便是亞洲杯﹐他們也是那些在外圍賽止步的球隊。也許﹐他們曾經是亞洲的冰島﹑芬蘭。不過﹐近來﹐他們越來越像馬爾他或盧森堡。
望著代表自己到國際比賽的球隊﹐給人蹂躪﹐的確是一件很難受的事情。因為那是切膚之痛。不過﹐當看到他們毫無鬥心﹐夢遊球場﹐任憑對手擺布﹐那更是千支針刺在心的感覺。假如對手是一隊不X知所謂的球隊﹐那傷口可就永不會痊癒。每年總有些時候﹐會有些血絲滲出來。量不多﹐但依然隱隱作痛。唯有來些發泄﹐才能勉強暫時忘記那永不結焦的傷口。
在愛爾蘭﹐大家都爭相表達對球隊的不滿。所有報紙的頭版都是慘敗給塞浦路斯的消息。電視都是要求史當頓下臺的聲音。在直播對捷克的比賽前﹐評述員說﹐今天的陣容﹐有六個變動啊﹗你怎樣看﹖另一個則回答道﹐便是如何派什麼人打正選﹐都一定比上場的陣容強。
的確比上場強。強多了。因為球員都知道羞恥。都知道他們實在傷透了人民的心。
雖然他們沒有如AIDAN所講﹐擊敗了捷克。不過﹐他們的表現的確有很大很大的進步。至少﹐讓人看得到他們的鬥心。他們被捷克逼和1-1。
我記得﹐上次﹐香港輸掉給中國0-7後﹐大家都沒有當它是一回事。報紙沒有大幅批評。市民也沒有表達不滿。電視臺的評述員甚至暗罵香港為何不多輸一球﹐好讓中國出線世界杯。之後﹐香港隊在國際賽的表現依然乏善足陳。
我不知道﹐在失掉十三球給德國後﹐聖馬力諾的市面是否跟香港一樣。
Friday, October 13, 2006
突然收到ROGER的電郵。他是我以前的一個上司﹐現在到了巴林工作。看到SUBJECT是MUNSTER,感覺有點意外。有點興奮﹐也有點感觸。
剛來到都柏林的時候﹐因為家裡還未接駁到互聯網﹐所以未能每天都在這個專欄寫一篇文章。可是﹐我又想我的朋友知道我的近況﹐於是每個星期﹐我都會到INTERNET CAFE,寫一個長長的電郵﹐跟他們報告一下。有天﹐碰巧愛爾蘭欖球隊MUNSTER贏得了歐洲冠軍(欖球的CHAMPIONS LEAGUE)﹐我便用了他們的名字來做電郵的SUBJECT。我說﹐我們終於成為了歐洲冠軍。猶記得﹐幾天後﹐ROGER是這樣回覆﹕請不好輕易放棄你的足球。
不經不覺﹐原來﹐已經是五個月前的事情。那些日子﹐真的很難忘。
我想﹐是因為愛華頓的表現太好﹐使他發了這一個EMAIL。他問我﹐有否打算過海看球賽﹖
其實﹐幾個星期前﹐我想過給他寫些東西。那天﹐倫敦時報有一個沉船意外的跟進報導。
意外發生在今年三月三十號晚上。一隻遊船在巴林海面沉沒﹐五十八人死亡。事發時﹐遊船正給一間建築公司租用﹐用來慶祝巴林世界貿易中心首期落成。ROGER便是在那間建築公司上班。因為他回來香港看七人欖球賽﹐所以未有出席那個派對。也就避過了一劫。本來﹐我們是約好在香港見面。因為發生了這件慘劇﹐他當然要立即返回BAHRAIN,打點一切。
THE TIMES說﹐船主正要控告建築公司經理SIMON HILL,因為他硬要船長開船﹐縱然船長是十萬個不願意。
不過﹐倫敦時報發現意外調查報告裡面說﹐意外主因是船主未能好好維修遊船﹐讓她適合載人。報告又說﹐負責安全檢查的公司﹐在出發前﹐又沒有把遊船檢查妥當﹐以至弄出悲劇。
只是﹐很奇怪地﹐報告竟然以為建築公司也要負責。因為他們疏忽。報告說﹐在租用遊船前﹐建築公司應該要確保遊船的安全檢查經已徹底完成﹐有證書證明。
天啊﹗難道我們上巴士前﹐也要查問一下﹐究竟這架巴士的安全檢查是否合格﹖登上地鐵時﹐我們乘客也要確保該輛地鐵性能良好﹐車長安全記錄優良﹖否則﹐便是發生了意外﹐都是活該﹖
中東國家真的無奇不有。
註﹕MUNSTER是愛爾蘭西部的一個省。
剛來到都柏林的時候﹐因為家裡還未接駁到互聯網﹐所以未能每天都在這個專欄寫一篇文章。可是﹐我又想我的朋友知道我的近況﹐於是每個星期﹐我都會到INTERNET CAFE,寫一個長長的電郵﹐跟他們報告一下。有天﹐碰巧愛爾蘭欖球隊MUNSTER贏得了歐洲冠軍(欖球的CHAMPIONS LEAGUE)﹐我便用了他們的名字來做電郵的SUBJECT。我說﹐我們終於成為了歐洲冠軍。猶記得﹐幾天後﹐ROGER是這樣回覆﹕請不好輕易放棄你的足球。
不經不覺﹐原來﹐已經是五個月前的事情。那些日子﹐真的很難忘。
我想﹐是因為愛華頓的表現太好﹐使他發了這一個EMAIL。他問我﹐有否打算過海看球賽﹖
其實﹐幾個星期前﹐我想過給他寫些東西。那天﹐倫敦時報有一個沉船意外的跟進報導。
意外發生在今年三月三十號晚上。一隻遊船在巴林海面沉沒﹐五十八人死亡。事發時﹐遊船正給一間建築公司租用﹐用來慶祝巴林世界貿易中心首期落成。ROGER便是在那間建築公司上班。因為他回來香港看七人欖球賽﹐所以未有出席那個派對。也就避過了一劫。本來﹐我們是約好在香港見面。因為發生了這件慘劇﹐他當然要立即返回BAHRAIN,打點一切。
THE TIMES說﹐船主正要控告建築公司經理SIMON HILL,因為他硬要船長開船﹐縱然船長是十萬個不願意。
不過﹐倫敦時報發現意外調查報告裡面說﹐意外主因是船主未能好好維修遊船﹐讓她適合載人。報告又說﹐負責安全檢查的公司﹐在出發前﹐又沒有把遊船檢查妥當﹐以至弄出悲劇。
只是﹐很奇怪地﹐報告竟然以為建築公司也要負責。因為他們疏忽。報告說﹐在租用遊船前﹐建築公司應該要確保遊船的安全檢查經已徹底完成﹐有證書證明。
天啊﹗難道我們上巴士前﹐也要查問一下﹐究竟這架巴士的安全檢查是否合格﹖登上地鐵時﹐我們乘客也要確保該輛地鐵性能良好﹐車長安全記錄優良﹖否則﹐便是發生了意外﹐都是活該﹖
中東國家真的無奇不有。
註﹕MUNSTER是愛爾蘭西部的一個省。
Thursday, October 12, 2006
最新一期經濟學人﹐裡面有一個調查報告﹐實在是每一個打工仔的必讀。於是﹐編緝便把它做了封面故事。其標題為THE SEARCH FOR TALENT︰WHY IT'S GETTING HARDER TO FIND。
THE ECONOMIST發現﹐近來老闆懮心的不再是盈利﹐也不再是成本。因為最近的確是所有企業的黃金時期。工會勢力越來越弱。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既給西方工業國提供大量廉價勞工﹐同時也開放了市場好讓各國企業賺取一桶又一桶的黃金。從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屢創新高﹐可見一斑。
他們懮心的﹐是找不到合適的人替自己辦事。
調查顯示﹐這情況經已不單發生在高科技行業。因為各行各業的企業都要花很長時間﹐方能找到填補空缺的人選。有時候﹐他們甚至要用一些SUB-STANDARD的人來頂上。畢竟﹐人才難求。去年﹐花在聘請人手方面的金錢﹐已是歷史新高。人力資源部門越來越重要。高盛便設有自己的「大學」﹐MCKINSEY亦有一個「人力委員會」﹐星加坡也成立了一個「國際人才部門」。都是為了方便招攬合適人手。
調查更顯示﹐到了2025年﹐人才短缺問題會更嚴重。因為工業大國的勞動人口都有大幅度的減少。德國便會少7%,意大利少9%。日本更會少14%。都是近年出生率偏低所導致。
在GLOBALIZATION的大風吹之下﹐香港已不再是我們唯一的MARKET。近年﹐隨著內地經濟起飛﹐越來越多香港人北上工作。不過﹐朋友﹐實在不好給政府及一眾華文報章蒙蔽了眼睛﹐只以為中國大陸才是我們未來要走的路。求才若渴的地方﹐實在不只中國一個。因為人才短缺已是全世界都要面對的問題。除了香港現在的宗主國﹐我們其實還有很多選擇。
當然﹐對於很多人來說﹐在中國大陸工作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始終是中國人的地方。文化差異不是沒有﹐不過不會很大。況且﹐在香港變得越來越像中國的一個城市的時候﹐文化差異也只會越來越小。只是﹐當你以為中國大陸工作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時﹐你又是否留意過外面的世界呢﹖只了解市場的某部份﹐而忽略了市場的大部份﹐便匆匆投入那個某部份﹐是否有點冒失﹖是否有點不智﹖
我們打工﹐務求得人賞識。你又可知道美國企業正面臨一個嚴重人才流失的問題﹖據估計﹐未來五年內﹐在美國頭500間企業裡面﹐至少有一半高層將會退休。他們都是戰後新生代。這表示﹐將有很多高級職位待人填補。你又可知道近來西方國家不斷希望年青一代棄文從理﹖因為他們發覺﹐他們培養得太少科學家和工程師﹐根本不夠人手去維持他們的優勢。
朋友﹐你看到了你的機會沒有﹖
的確﹐中國和印度也有很多理科人才到了美國讀書工作。只是﹐THE ECONOMIST對此有這樣的一個REMARK︰There are also cultural legacies to deal with. India's Licence Raj destroyed management skills, while China's Confucian tradition still emphasises "face" over innovation.
香港人﹐你看到了你的機會沒有﹖
這便是我們要不斷強調自己是香港人的原因。因為那才是我們的NICHE。為了生存﹐我們更不能跑去當中國人民一份子﹐放棄自己本身國際公民的身份。
奈何﹐香港政府卻不是這樣看事情。他們竟然以自己是中國的一個沿海城市為傲。
為了下一代﹐我們還是在香港淹沒在紅色中國大海之前﹐跑去開始我們的國際夢罷。國際的天空﹐很大﹑很廣。
THE ECONOMIST發現﹐近來老闆懮心的不再是盈利﹐也不再是成本。因為最近的確是所有企業的黃金時期。工會勢力越來越弱。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既給西方工業國提供大量廉價勞工﹐同時也開放了市場好讓各國企業賺取一桶又一桶的黃金。從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屢創新高﹐可見一斑。
他們懮心的﹐是找不到合適的人替自己辦事。
調查顯示﹐這情況經已不單發生在高科技行業。因為各行各業的企業都要花很長時間﹐方能找到填補空缺的人選。有時候﹐他們甚至要用一些SUB-STANDARD的人來頂上。畢竟﹐人才難求。去年﹐花在聘請人手方面的金錢﹐已是歷史新高。人力資源部門越來越重要。高盛便設有自己的「大學」﹐MCKINSEY亦有一個「人力委員會」﹐星加坡也成立了一個「國際人才部門」。都是為了方便招攬合適人手。
調查更顯示﹐到了2025年﹐人才短缺問題會更嚴重。因為工業大國的勞動人口都有大幅度的減少。德國便會少7%,意大利少9%。日本更會少14%。都是近年出生率偏低所導致。
在GLOBALIZATION的大風吹之下﹐香港已不再是我們唯一的MARKET。近年﹐隨著內地經濟起飛﹐越來越多香港人北上工作。不過﹐朋友﹐實在不好給政府及一眾華文報章蒙蔽了眼睛﹐只以為中國大陸才是我們未來要走的路。求才若渴的地方﹐實在不只中國一個。因為人才短缺已是全世界都要面對的問題。除了香港現在的宗主國﹐我們其實還有很多選擇。
當然﹐對於很多人來說﹐在中國大陸工作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始終是中國人的地方。文化差異不是沒有﹐不過不會很大。況且﹐在香港變得越來越像中國的一個城市的時候﹐文化差異也只會越來越小。只是﹐當你以為中國大陸工作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時﹐你又是否留意過外面的世界呢﹖只了解市場的某部份﹐而忽略了市場的大部份﹐便匆匆投入那個某部份﹐是否有點冒失﹖是否有點不智﹖
我們打工﹐務求得人賞識。你又可知道美國企業正面臨一個嚴重人才流失的問題﹖據估計﹐未來五年內﹐在美國頭500間企業裡面﹐至少有一半高層將會退休。他們都是戰後新生代。這表示﹐將有很多高級職位待人填補。你又可知道近來西方國家不斷希望年青一代棄文從理﹖因為他們發覺﹐他們培養得太少科學家和工程師﹐根本不夠人手去維持他們的優勢。
朋友﹐你看到了你的機會沒有﹖
的確﹐中國和印度也有很多理科人才到了美國讀書工作。只是﹐THE ECONOMIST對此有這樣的一個REMARK︰There are also cultural legacies to deal with. India's Licence Raj destroyed management skills, while China's Confucian tradition still emphasises "face" over innovation.
香港人﹐你看到了你的機會沒有﹖
這便是我們要不斷強調自己是香港人的原因。因為那才是我們的NICHE。為了生存﹐我們更不能跑去當中國人民一份子﹐放棄自己本身國際公民的身份。
奈何﹐香港政府卻不是這樣看事情。他們竟然以自己是中國的一個沿海城市為傲。
為了下一代﹐我們還是在香港淹沒在紅色中國大海之前﹐跑去開始我們的國際夢罷。國際的天空﹐很大﹑很廣。
Wednesday, October 11, 2006
自小知道自己不是領袖的材料﹐所以﹐從來沒有想過做一國之首﹑一黨之頭頭。讀三國﹐我愛的是諸葛亮﹔讀水滸﹐我喜歡的是吳用。
早陣子﹐保守黨舉行年度大會。DAVID CAMERON當然是大家的焦點。在他的領導下﹐TORIES已經在民意調查超越了工黨﹐大有機會贏得下屆大選﹐再次執政。影子財相GEORGE OSBORNE也是報紙雜誌爭相採訪的對象。他跟金馬倫成為了英國政壇最年輕耀眼的光芒。他們的年齡相加也不過七十五﹐比起遠東那個古國那些眷戀權力的老人家還要少。由他們入主唐寧街九號和十號﹐英國無異是一個OLD COUNTRY WITH A PROUD PAST AND A BRIGHT FUTURE。
不過﹐一手把垂死的保守黨鑄入新生命的﹐其實是STEVEN HILTON。另一個OXFORD畢業生。他比CAMERON少三年。有人說﹐希爾頓實在是PETER MANDELSON和ALASTAIR CAMPELL的混合體。文度森與甘寶便是新工黨的幕後策劃。
希爾頓祖籍匈牙利。1956年﹐因為蘇聯入侵﹐他的父母便以難民身份定居英國。
HILTON為人低調﹐並不喜歡出風頭。DAVID CAMERON演講的時候﹐他只會站在會場最後排的位置。當有鏡頭對准他的時候﹐他會立即迴避。他不跟記者交談。他沒有JOB TITLE,TORY的網頁裡面也找不到他的名字。年度大會舉行期間﹐他也甚少出席公開場合﹐只留在酒店裡面。不過﹐大家都知道﹐他跟DAVID CAMERON住在同一間套房。他也是金馬倫大兒的GODFATHER。
讀著報紙裡面介紹HILTON的文章﹐我想起了一個人。
他是一個香港富豪的左右手。他曾經跟我說過﹐「風頭﹐永遠由老闆來領。」我知道﹐那是他的成功秘訣。看著他爬到這個位置﹐我更相信﹐這不是騙人的話。有時候﹐他甚至要製造風頭讓老闆來領。有一次﹐他邀請了法國酒廠東來﹐為他自己的藏酒換水松蓋。不知怎樣收來的風﹐南華早報竟然得知﹐希望來採訪。因為那是歷史上第一次在非法國境內﹐給近百年的紅酒換水松蓋﹐對酒有認識的人都想開一開眼界。他不希望上鏡。於是﹐便把那些酒說成是老闆的珍藏﹐用老闆的名義邀請中外記者來報導。第二天讀報紙﹐我完全找不到他的名字。
多年前﹐壹周刊介紹香港富豪的頭馬。他便是唯一一個沒有給登上照片的人。我想﹐因為香港記者根本拍不到他的照片。每次給拍到上電視﹐他總是站在人群裡面﹐跟老闆保持了一段應有的公開距離。要不是認識他﹐實在分辨不出來。雜誌裡面的那篇介紹也很短。局外人便只知道他跟他的老闆都是在同一間大學畢業。NOT A PENNY MORE,NOT A PENNY LESS。
我相信﹐在這方面﹐STEVEN HILTON還要跟他多多學習。倫敦時報是刊登了希爾頓的照片﹐也用了一版來介紹。
很多時候﹐我都會以他為做人目標。每次跟他吃晚飯﹐我都覺得獲益良多。至少﹐去了一些甚少機會去的餐廳﹐喝了一些不大可能開的酒。
我不知道﹐我能否有這樣的能力﹐去攀到那個位置。不過﹐似乎我便走著他走過的路﹕看了CLASSIFIED POST的廣告後﹐便接受了OFFER,毅然漂洋過海去。只是﹐我去的是一個外國人的世界。不知這樣是否會多加一點難度﹖
早陣子﹐保守黨舉行年度大會。DAVID CAMERON當然是大家的焦點。在他的領導下﹐TORIES已經在民意調查超越了工黨﹐大有機會贏得下屆大選﹐再次執政。影子財相GEORGE OSBORNE也是報紙雜誌爭相採訪的對象。他跟金馬倫成為了英國政壇最年輕耀眼的光芒。他們的年齡相加也不過七十五﹐比起遠東那個古國那些眷戀權力的老人家還要少。由他們入主唐寧街九號和十號﹐英國無異是一個OLD COUNTRY WITH A PROUD PAST AND A BRIGHT FUTURE。
不過﹐一手把垂死的保守黨鑄入新生命的﹐其實是STEVEN HILTON。另一個OXFORD畢業生。他比CAMERON少三年。有人說﹐希爾頓實在是PETER MANDELSON和ALASTAIR CAMPELL的混合體。文度森與甘寶便是新工黨的幕後策劃。
希爾頓祖籍匈牙利。1956年﹐因為蘇聯入侵﹐他的父母便以難民身份定居英國。
HILTON為人低調﹐並不喜歡出風頭。DAVID CAMERON演講的時候﹐他只會站在會場最後排的位置。當有鏡頭對准他的時候﹐他會立即迴避。他不跟記者交談。他沒有JOB TITLE,TORY的網頁裡面也找不到他的名字。年度大會舉行期間﹐他也甚少出席公開場合﹐只留在酒店裡面。不過﹐大家都知道﹐他跟DAVID CAMERON住在同一間套房。他也是金馬倫大兒的GODFATHER。
讀著報紙裡面介紹HILTON的文章﹐我想起了一個人。
他是一個香港富豪的左右手。他曾經跟我說過﹐「風頭﹐永遠由老闆來領。」我知道﹐那是他的成功秘訣。看著他爬到這個位置﹐我更相信﹐這不是騙人的話。有時候﹐他甚至要製造風頭讓老闆來領。有一次﹐他邀請了法國酒廠東來﹐為他自己的藏酒換水松蓋。不知怎樣收來的風﹐南華早報竟然得知﹐希望來採訪。因為那是歷史上第一次在非法國境內﹐給近百年的紅酒換水松蓋﹐對酒有認識的人都想開一開眼界。他不希望上鏡。於是﹐便把那些酒說成是老闆的珍藏﹐用老闆的名義邀請中外記者來報導。第二天讀報紙﹐我完全找不到他的名字。
多年前﹐壹周刊介紹香港富豪的頭馬。他便是唯一一個沒有給登上照片的人。我想﹐因為香港記者根本拍不到他的照片。每次給拍到上電視﹐他總是站在人群裡面﹐跟老闆保持了一段應有的公開距離。要不是認識他﹐實在分辨不出來。雜誌裡面的那篇介紹也很短。局外人便只知道他跟他的老闆都是在同一間大學畢業。NOT A PENNY MORE,NOT A PENNY LESS。
我相信﹐在這方面﹐STEVEN HILTON還要跟他多多學習。倫敦時報是刊登了希爾頓的照片﹐也用了一版來介紹。
很多時候﹐我都會以他為做人目標。每次跟他吃晚飯﹐我都覺得獲益良多。至少﹐去了一些甚少機會去的餐廳﹐喝了一些不大可能開的酒。
我不知道﹐我能否有這樣的能力﹐去攀到那個位置。不過﹐似乎我便走著他走過的路﹕看了CLASSIFIED POST的廣告後﹐便接受了OFFER,毅然漂洋過海去。只是﹐我去的是一個外國人的世界。不知這樣是否會多加一點難度﹖
Subscribe to:
Posts (Atom)

